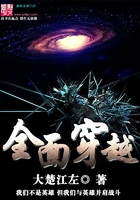在中国绘画中,形式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笔法,二是绘画的结构。在唐代甚至以前的人物画中,形式大多仅局限笔法。南齐谢赫在评陆探微的绘画时说:
“一点一拂,动笔皆奇……”
已从单纯独立的点划之闻,看出了画家的风格倾向。
又说:
“……出人穷奇,纵横逸笔,力道韵雅,超迈绝伦……”
在他看来,“出人穷奇”、“力道韵雅”的绘画效果均是在“纵横逸笔”的笔法形式下产生的。可以看出当时带有书法意义的笔法已在人物画中出现并开始具独立意义。这从顾恺之的传世作品中可以略见一斑,其“春蚕吐丝”的用笔,精致而细密,具有连绵延续的形式感,与实际衣纹的结构已相去甚远。笔法在山水画中的出现稍晚于人物画,其发展有一个过程。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山水画虽然已具有“以形媚道”、“卧以游之”的认识契机,但笔法形式尚未成熟。中国现存最早的山水画,是隋代展子虔的《游春图》,它在对具体形象的描绘上,雕琢和模拟的痕迹是相当明显的,如对自然的描绘仅用单线平涂,以及桃红柳绿的色彩应用等。
在唐代的山水画中,一些画家和理论家在实践中开始注意笔法形式和书法的结合,并在理论上加以总结,初步指出它的独立效果。《历代名画记》的作者张彦远指出:
“唯王子敬明其深旨,故行首之字,往往继其前行,世上谓之一笔书,其后陆探微亦作一笔画,连绵不断,故知书画用笔同矣。”
“书画用笔通同矣”这个结论,恰恰指出了中国绘画形式美的重要特点之一。
中国画表现形式与书法的关系是带有血缘性的,它的渊源见乎绘画的早期发展上。例如,图案上的单纯用线,可在原始的彩陶中见出毛笔的痕迹。又如,中国的早期文字主要是用毛笔作为传达的物质工具。考古学表明,几千年前的甲骨文未完成刻契的部分中,残见着书写痕迹。西方绘画虽也有用线的,但作为再现的物质媒介,线条主要起结构形体的作用,不像中国画那样具有明显的独立的美感的意义。
然而中国绘画在具体的形体表现中笔法形式又体现着一定的。如描绘一块顽石,也要遵循圆中寓方,方中见圆的精神,这关系着笔法的单纯形式的美。因为简单的圆或方都易失之于流滑和刻板。明末清初的画家八大山人所画的一条长线就充分体现出平直圆滑的统一。其荷茎转折侧带,方圆扁浑合宜,显示出更深刻的富有体味性的形式涵义。五代画家荆浩曾说:
“凡笔有四势,谓筋、肉、骨、气是也,笔绝而不断谓之筋,起伏成实谓之肉,生死刚正谓之骨,迹画不败者谓之气。”
骨与肉是对立(性能上:软与硬)的。要把二者统一在同一形式内,使其相互依存,这是表现精神上的立体,即从各个方面赋予笔法形式以丰富的涵义,包括思想上的主动意识的渗化。这个“立体”使形式至多层次,多意象。在形式中表达儒家温良敦厚的精神性格美,则形成带有倾向性的美感。因而,在对这种本领的锻炼中,许多因用笔不当或心滞意庸而产生的失败笔法,宋代郭思就曾指出过:
“一曰板,二曰刻,三曰结。”
近代画家黄宾虹在多年的形式探索中,曾深有体会地扩充笔意内义,使其包含有人的个性美:
“作画最忌者:死、板、刻、浊、薄、小、流、轻、浮、甜、滑、飘、柔,艳;应做到:重、大、高、厚、实、浑、润、老、拙、活、清、秀、和、雄。”
这就已经不是单纯的笔法了,而是笔法形式中显示的画家的风格,毫无疑问是人意附会的。讲大气、正气、浩然之气,都带有性格倾向、人品倾向和思想伦理的变通,正如苏轼对文与可评价那样:
“与可之文,其德之糟粕;与可之诗,其文之毫末。诗不能尽,溢而为书,变而为画,皆诗之余。其诗与文,好者差寡、有好其德,如好其画者乎?”
这里苏氏全面权衡的是文与可绘画的整体构成因素,也包含笔法形式在内。这个“德”,实际上是文与儒、道思想修养的反映。
笔法形式的独立性美感,不单与书法有渊源关系,而且也是一幅画高下的重要因素。点之延长为线,点之扩充为面,虽是造诣精湛的书家可能不通于画,但作为一个有成就的画家来讲,书法的修养深度则可以关系到他绘画艺术的高下。中国绘画在严格笔法即直接书法意义的同时,并由此派生出许多衣纹描法和山水皴法,(间接书法意义的)线的还原和点的扩充都是这些技法的具体来源。中国人物画后来总结出来的所谓十八种描法,有一个部分便是对书法笔法的正面承继和应用,另一部分则对书法笔法加以变革、改造和发展,以表现人物丰富复杂的动态和内心世界。所谓“钉头鼠尾描”等即是如此。在山水画中这类利用尤为明显,无论是形势峭立,使人“观而壮之”的名山大川,还是娱于胸襟的野浦远汀,仅仅要求线本身的变化是不够的,因此需要出现演化。被后人总结到三十余种的皴法,便是这种要求下派生的,如斧劈皴、披麻皴等,就是为表现特定的山川而出现的。
书法在绘画中的主动意识性明确应用见于元代之始,如“写竹干用篆法,枝用草书法,写叶用八分法,或用鲁公撇笔法,木石用折钗股屋漏痕遗意”。这种为使书画结合而不惜局隘的做法,作为一种意识上的应用程式难免有其死板的一面。事实上,后世绘画并没有因此而停止发展,李晴江的竹叶法,金冬心的梅花法,八大山人的山水画法等,都是根据各自的审美和表现特定意象而做出的形态各异的笔法变化。
中国绘画自元代始,跋文款识直接题在画面上。这种“始侵画位”的做法实际上在宋代就开始有了,如宋徽宗赵佶,其清劲的瘦金体同富丽高雅的画面奏出美妙的和弦,书法做为融合因素开始与表现的景物平分秋色了。在元代几个有代表性的画家的山水画中,书法味的形式更为突出。如黄公望的山水画所用的方法主要是长披麻皴,它有一个显明之处就是在萧散清逸的画面上,笔痕加强了,笔与笔之间的独立性显得格外清楚,重叠性用法明显地减少了。这不能说不是在书法融汇画法的风气中一种自觉的形式美探索。同时代的倪云林、吴镇诸家也非常鲜明地具有以上特色。王蒙虽然笔法繁复,但形如蚯蚓的用笔亦特具意味。这种现象在赵孟頫的画中早有预见性的端倪,其《鹊华秋色图》可见佐证。笔迹是画家为表现客观物象的美进行各种渲染、皴擦的结果。相对讲,在笔法的相互重叠中,独立的笔法形式要少得多。而上溯唐代,见诸遗迹中,孙位的《高逸图》是一个很好的说明,画中之石酷似自然之石,笔迹在渲染、皴擦中混淹了,这里,形式附庸形体的做法是显而易见的。曾自负有笔有墨的荆浩对吴道子与项容的评点,实际上说明了当时对此类倾向已萌发意识。
另一方面,中国绘画中还有艺术家充满正气的人品性格的流露,荆浩在《笔法记》中说:
“起伏成实谓之肉,生死刚正谓之骨……”
这里与其说是单纯探讨笔法形式,毋宁说是在****的五代,艺术家正统的儒德和正直诚实的品性修养的表现。不过在荆洁的笔法形式中,书法意义还不见鲜明(传作《匡庐图》亦可说明)。
元代绘画的新倾向,说明了书法形式之于绘画不甘于徒具表现因素,而逐渐走向独立。款识在元代虽已盛起,但主要还是一种说明的因素,即对境界的加深和技法独立的显示。明清两代,书法形式美的地位在绘画中得到了彻底的加强,真正成为绘画不可分割的构成因素。这种现象由于清代摹拟前人山水画传统之风昌盛而呈“凝化”状态。但在花鸟画中却得到了更广泛的自由渗透。无论是徐渭草书飞舞的枝藤,还是朱耷出神入化的枯荷,以至用笔如金刚铁杵的吴昌硕的写意花卉,无不说明书法形式美已成为绘画中不可缺少的组成因素。另一方面,有时款书占据了画面的大部分空间,在比例上远远超过了画中所表现的物象,例如八大山人朱耷的绘画有的甚至只画一朵小花,旁边却题上大之数倍的草书:落花题字与植物本来无从联系;但盘虬屈曲的书法结构和绞动的形式感,亦给人以带有生命力的长生着的老藤的感觉,直与画面形成大小、疏密、老嫩的对比。即使是不能产生如此局滞的视觉联想,亦能给观者类似的形式美感受。这样,书法有时在画面上与所描绘的自然物相映成趣,而成为构成韵律交响不可缺少的音符。从朱耷的这幅画中即可以看出,如把款书抽出,此画便难以成立。(当然这种尝试未必一定就是绘画的方向,但书法在中国绘画中的重要地位可见一斑。)又如扬州画派,各家皆以各自的书法之长,创就了各具风格的具有强烈形式美感的作品,如郑板桥的奇诡洒落,金冬心的凝重古拙,李晴江的潇洒飘逸,黄瘿瓢的连绵跌宕等等。由此可以看出,书法之于中国绘画的影响因素是多方面的,逐渐形成的。在中国绘画形式美感的生成和显现上书法有其积极的意义和重要的地位。因此,若没有书法意义的形式,则中国绘画形式美的意义便不复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