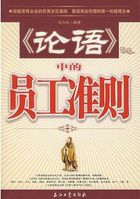另一位是裴君,名庆昌,宁世五,长我两岁。我们关系更近,因为一,不只同乡,而且邻村;二,同时上小学,在同一个课桌上念共和国教科书;三,由启蒙老师主盟,结为金兰兄弟;四,由30年代起,又相聚于北京,连续50多年,住在一城之内,常常见面,直到送他到八宝山,几乎没有分离过。以下专说这第四的长相聚。他来北京比我早,是上中学。只念了两年,因为家境突降,必须自己谋生,改为在街头卖早点。在外城菜市口一带,与两位表兄住在一起,共吃而分别卖自己的豆浆、杏仁茶之类。他忙,下午备货,早晨挑担出去,所以聚会总是在他的住处,对着灯火共酒饭。酒总是白干,饭常是小米面窝头,家常菜一两品。可是觉得好吃。更有意思的是裴君记性好,健谈,两三杯酒下咽,面红耳热,追述当年旧事,能使我暂时忘掉生活的坎坷,感到世间还有温暖。就像这样,连续几十年,一年聚会几十次,就使我们的友情不同于一般。怎么不同?难于说清楚。我认识人不算很少,自然也就间或有交往,交往中会感到善意,甚至亲切,可是与裴君相比,就像是远远不够。一般的友谊,比喻是花,与裴君的是家常饭,花可以没有,家常饭就不能离开。可是他终于先我而去,一年四季,晚上还是至时必来,我常常想到昔日的聚会,也就禁不住背诵《庄子·徐无鬼》篇的话:“自夫子之死也,吾无以为质矣,吾无与言之矣!”话归本题,“老者安之”,安,也靠友谊,可是这个处方不难,买到高效药却大不易。
7.我的两个朋友
从维熙
从维熙,1933年生,河北玉田人。当代作家。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北国草》、《裸雪》,中篇小说集《遗落在海滩的脚印》、《远去的白帆》,短篇小说集《从维熙小说选》、《洁白的睡莲花》等,另外还有文艺论集《文学的梦》。《大墙下的红玉兰》、《远去的白帆》获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
儿时,在村口大庙改建的学堂,就摇头晃脑地背诵过这样的警世诗句:“光阴好比河中水,只能流去不流回”,“一寸光阴一寸金,寸金难买寸光阴”。当时我刚刚告别襁褓的孩提时光,虽然背诵这些诗行时有滋有味,但并不理解诗句中的深奥意义。我究竟是从哪个年头才开始认识时间的价值的,已经无从回忆;朦朦胧胧地记得开始发表习作时,我才开始勒紧了时间——这匹飞快奔驰着的野马的缰绳。
后来到了劳改队,就更知道时间的贵重了。那时一天到晚干着笨重的体力劳动,只有借晚上的空当,不十分合法地看点想看的书。在山两某地的一个劳改单位,因为我读果戈理的《米尔格来德》,睡得太晚了,第二天早晨耽误了出工,读了自我批判的语录还不行,还受到了站在主席像前请罪的惩罚。
为了充分地占有时间,又不再受到“请罪”的惩处,我决心买一块闹钟(原来一块半钢的英纳格手表,在穷途潦倒时变卖了)。每次从劳改队回来,我都要抽出点时间去逛信托商店,察看古旧钟表的行情。当时手表还不像今天这么普及,即使是旧货,至少也要三五十元,多则一二百元;苦于囊中没有那么多“铜板”,我每次都是喜兴而去,扫兴而归。
我心不死。在七一年我从山西回北京探亲时,再次去地处东单附近的“三洋信托商店”,寻找买古旧的钟表契机。这次出行真是吉星高照,我看见一位神色惆怅的少妇,手里捧着一个北京牌的淡乳色的小闹钟,在信托商店的收购部门前徘徊,看那神韵仿佛是个被斗户的家属,家中似有难言之隐痛,出于无奈才来变卖这个小闹钟,因而步履迟疑,不好意思走进收购部的两扇玻璃门。说实在的,我真想上去询问她一声,这个闹钟她要卖多少钱,但是劳改多年也没改造掉的那股子清高气,黏着了我的两片嘴唇,使我几次欲言又止。还是她看出我的心思(因为我两只眼不断地打量那个小闹钟的新旧程度),主动询问我一句:“要买这个小闹钟吗?”“是的,你想要多少钱?”她看看我似乎不像个倒买倒卖的“倒爷”,又不像专门抓店外交易、化了装的便衣侦缉,便诚恳地说:“看着给吧!这是抄家给我剩下的,已然是身外之物了!”她这么一说,我倒不好意思开口了:价钱高了吧,我买不起;价钱低了吧,说不定这位大嫂要靠这钱给孩子订牛奶呢!
她看我面有窘色,悄声说:
“新闹钟才十二块钱,你就给我一半吧!”
“六块?”
“嗯!”
我几袋里只装有8块钱,冲动之下都递给了她。我想:“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这位少妇可能是怕人发觉我们的店外交易,也没有点一下一共几张一元的钞票,就匆匆地从东单二条拐出去,消失在大街的人流之中。
从此,这个有八成新的小闹钟,丁零丁零的成为我的亲密伙伴,它限制我夜读的时间,又用铃声催我起床出工。劳改队的小木匠盖孝贤,得知这个小闹钟的来历后,特意给我做了个四四方方像儿童积木一样的玻璃钟罩,以防从空隙间飞进尘埃,影响这座小闹钟为我服务的时间。
1971~1985年,时间流水般地流过去14个年头。这5000多个日日夜夜,这座小闹钟如同我最忠实的朋友,为我赢得时间而鞠躬尽瘁。特别使我珍视的是,14年中它没进过表店修理,连一次油泥也没擦洗过,真可谓生命力极为顽强。我重返文坛之后,虔诚地把它摆在写字台的正前方,我把它当做一面镜子,自省,自励,自强,自进。
1985年春,我随中国作家代表团访日,在即将返回中同的头一天,一位日本文化界朋友,赶到东京新大谷饭店为我送行。其实,我和他并非熟知,只因前几年过春节时,一位中国记者带他到我家家访,正逢燕祥、绍棠、友梅、叶楠、浩成、厚明等好友围着餐桌为辞岁迎春而碰杯。可能是日本人极重礼仪之故,这位朋友为答谢我昔日款待他之情,执意要送我一块日本精工牌电子旅行表,推谢再三终未能拒,只好将它装进行囊,带回北京。启盒之后,发现这旅行表十分美观:古铜色的外壳,金黄色的夜明表盘;机心内配有鸣笛喇叭,报起时辰来颇为悦耳。
我把这个旅行表放在小闹钟身旁,写作疲惫之际,常抬头看那两个表盘上的时针、分针、秒针,沿着360度的圆周奔跑。不知是我的那位“老朋友”,忌妒我这位“新朋友”之故,还是因为它生命力逐渐衰老之因,我突然发现它的时差和北京标准时间越拉越大。我不愿使这位“老朋友”伤感,误解我有喜新厌旧之嫌,便将这位“新朋友”装进表盒里,让这位“老朋友”独占案头,嘀嗒嘀嗒地和我说话。哪知它并不因此峰回路转,而且继续对我怠工示警。我倒为此而感伤起来,因为这座小闹钟不仅来历不凡,而且它的表盘上的每个刻度里,都记忆着我在漫漫长途跋涉中的痛苦和欢乐;它对我来说,既是历史经卷,又是有功之臣,因而我仍然把它摆在我的面前,不断地用眼睛和它对话。即使这样,它仍然对我不加宽恕,有时竟然不再转圈了。我把它送进修理钟表的店铺,老师傅告诉我:“同志,换个新的吧!它已经完成它的使命了!”我执意叫他修理,并愿付出几倍的修理价格。老师傅含蓄地甩了我几句:“同志,我曾是个技艺高明的钟表匠,可是现在老了呀!眼神不济,手脚哆嗦,我这个月就要把这把椅子让给我的徒弟了。你这小闹钟也像我一样,就是给你修理了,它还是要和你经常发脾气闹罢工的!你还是买个新闹钟吧!”我明知老师傅这一席话,扼要地阐明了一条自然规律,但我还是坚持要他精心地把闹钟修理一下。他摇摇头感慨地说:“瞧你这位同志,倒是挺恋旧的,我丑话可说在头里,我们修表店对它能否继续走动,概不负责。”
半月之后,我把这座小闹钟取了回来。为了怕它重犯狭窄的“忌妒狂”,我把它进修表店期间放置案头前的那块精工旅行表,再次收拾起来入库;可是使我遗憾的是,我的这位“老朋友”不仅仅是对我怠工了,而且常常躺倒不干。最近,国际青年征文授奖大会在中央戏剧学院礼堂举行;事先参与这次授奖大会的组委,曾反复叮咛我下午两点必须赶到现场。因为我没有察觉我那位“老朋友”又犯了休克症,误把它指示给我的时间,当成了北京标准时间,结果,延误了工作,使我为此而感到深深的内疚。
内疚之后,我似乎真正发现了一点什么新的意念。
我怀着十分复杂的心情,把我那位“老朋友”从桌子上请了下来,拂去钟罩上的灰尘,用一块新毛巾把它包好,收藏进书橱里。我很矛盾,曾经几次把它重新放在写字台上,想让它重新成为我的生活罗盘,但是我的这位“老朋友”的转动速度,如同步履蹒跚的老人,时喘时停,我不得不下定决心把它请下书桌。
我把那块80年代精工新产品,摆在写字台前。它不用我每天上弦,走得和北京标准时间吻合无误,我的那位“老朋友”曾使我赢得时间,我将永远怀念它;我的“新朋友”使我赢得了新的时间概念,它不仅是我生活中严厉的法官,而且启示我认识了严酷的自然法则……
8.我的朋友爱琴海
高建群
高建群,1953年生,陕西临潼人。当代作家。现任陕西省文联副主席、陕西省作家协会副主席。代表作有《最后一个匈奴》、《六六镇》、《古道天机》、《愁容骑士》、《大顺店》、《胡马北风大漠传》等。2004年被《中国作家》评为当代最具有影响力的中国作家。
爱琴海画了一幅油画给我。油画叫《奥德塞史诗里的野天鹅》。苍茫的雪原上,一群野天鹅在挣扎,在歌唱,在气绝而亡。油画的调子是蓝色的,有点像鬼蜮,又有点像天堂,油画传达不出声音,但我凝神谛听,分明能听到天鹅们弥漫在整个空间的大美之音。
两人认为,天鹅一生只吟唱·次,那是在它行将辞世的时候。那时,它毕·生之力,将最美好的祝福留给人间。借于此,拜伦在他的《唐璜》中,曾经犀利地唱道:“让我像白天鹅歌尽而亡。”
歌尽而亡的天鹅,最后蜷缩起来,在雪原上形成一个个小丘。那些美丽的遗骸莽莽苍苍,从我们的脚下直铺天际。我刚刚从宁夏归来,这样充满凄凉感的小丘我见过;不过那是沙丘。宁陕道上戈壁滩上会突兀地出现这么一片景致:烟雾腾腾,飞沙走石,小丘连连,气象森森,仿佛前人在这里布下的一个八卦阵。而银川左近的那个影视城,一片历史的废墟,横亘荒原,更有不尽的沧桑会向你袭来。张贤亮老师说,他是在出卖荒凉!
爱琴海的油画现在就悬挂在我的客厅里,占了半面墙壁。每口相对,佐我晨昏。
我没有上过大学,《奥德塞》者,《伊利亚特》者,我知之甚少。不过我喜欢希腊悲剧的那种崇高感和古典美。我在自己的作品中,总是竭尽所能,向历史上的那个高峰靠近。大约正是知道我这种一厢情愿的艺术追求,并且知道我对那个挥舞着拐杖的大诗人拜伦充满敬意吧,爱琴海先生专门画了这幅油画赠我。
去年的这个时候,我从陕北回到了西安。前辈作家、我的好朋友张敏先生说,住在北郊吧,这里的房便宜。我说“好”。后来又有朋友说,北郊不好,北郊是下等人居住的地方,文化人应当居住在南郊。我听后置之一笑说,我本来就是个下等人,不修边幅,不拘小节,衣衫不整,邋里邋遢,混迹于这些引车卖浆者之中,正是我的心愿啊!
前不久,爱琴海先生从陕南下来。这时我劝他也居住在这里,爱一拍大腿说:“好,三人成虎。咱们住在一块,闹一番世事。”我的楼前面,有一溜平板房,爱琴海在二楼上,租了两间,月租150元,一张大白木桌子,房中一摆,一手挥动画笔,一手挥动钢笔,进入状态。
爱琴海除画画之外,还是一位作家。1988年,他写道一部有影响的中篇《沉默的玄武岩》。而今,他手头又有两部长篇,一部已竣工,一部已接近完成。他说,一个交出版社,闯点名;一个交书商,挣点儿钱。
我和张敏、石岗几位,都是爱热闹的人,三天一小聚,五天一大聚。有个郑定于老师,中国电影界的大权威,也时常放下架子作老顽童状,与我们一起厮混。每次冶游归来,见爱琴海的房间里,还有灯光,便上去敲门。爱琴海穿一条短裤,大汗淋漓,正在写作,房间热得像间土耳其浴室。“今天完成了8000字!”他说。只这一句话,令我们几个面生愧色。
爱琴海当然主要还是一个画家。他有一个堂吉诃德式的梦想,想在西安的北院门,开一个画店,经营他的画。他目前已凑够了20多幅,店址也已确定,可望不久即开张吧。他的画,大约会找到买主的,以他给我画的这幅《奥德塞史诗里的野天鹅》而论,据说,有人曾出到1万元要买,他说这是给朋友画的,不卖。
爱琴海身材矮小,大约一米六吧。夫人却长得雍容华贵,身材高大,一米七还要多些吧!那次在我客厅哩,挂这幅画,爱琴海站在一个小凳子上,半天挂不上二去。夫人见了,一把推开他,又一脚踢走小凳,然后站在地板上,伸长玉臂,轻轻松松地将画挂好。“高女人与矮丈夫,这是冯骥才小说中的—个题目!”我打趣道。爱琴海听了,使劲地伸长脖子,作小伟人状,婆姨横他一眼说:“现在要长,恐怕迟了!”
爱琴海已经调来,婆姨还没有调来,我盼望这一对伉俪能早日团聚,亦盼望他的那两个长篇,会给新时期文学增添斑斓之色,并给他带来收益。画店什么时候开张,我也等待着,到时候,为他凑个热闹吧,如果那时手头宽裕,不妨率先买他一·张画,给市民们做个榜样!
9.深夜怀友
叶公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