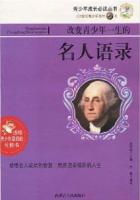之后,我在这种心情下过了将近一年。这段时间里,我不再想袭击这些野人,我再也没有到那个小山丘上去看是否有他们的踪影,去了解他们是否已经上岸。因为我怕自己受不住诱惑而对他们重新实行我的计划,怕自己看到有机可趁而袭击他们。我只做了一件事情,就是把我放在岛那边的小船移到了岛的东部来,并把它开到一个我在高岩下发现的一条小溪里。我知道,由于激流,那些野人,无论什么原因也不敢或不愿乘着他们的小船到这里。
我把留在小船上的一切东西都搬了下来。这些东西是短期航行不需要的,包括我为小船制作的一套桅杆和帆,一个似锚的东西,但实际上既不似移动锚又不是搭钩,但我尽其所能,也只能做成那个样子了。我把这些东西全搬了下来,免得被人发现,被看出有船只和住人的迹象。
此外,我比以往更加深居简出了,除了日常工作,如挤牛奶、照料树林中的羊群,很少走出住宅。那些羊群在岛的另一边,因此没有什么危险。因为那些常到这个岛上的野人,从来不曾设想能在这里找到什么东西,所以他们也就从不曾离开海岸向岛里走。我怀疑自从我对野人忧虑重重而十分小心后,他们来这岛上已有好几次了。实际上,我一回想起过去就非常害怕。因为我以前只带一支枪,枪里只有些很小的子弹,而且经常手无寸铁地在岛上东张西望,以期有所发现。如果这时恰巧碰到他们或是被他们发现,我的处境又该是怎样呢?或者,假如当时我看到不是一个人的脚印,而看到了十几个、二十个野人,他们拼命追赶我,而且跑得那样快,我从他们手中根本无法逃出,那我又该何等的惊慌失措啊!
有时想到这里,我就吓得灵魂出窍,心里异常难过,好半天都回不过神来。想不出我那时该怎么办,不知道该去怎样抵抗他们,不但会由于惊慌失措,考虑不出应付的办法,甚至会把经过深思熟虑和充分准备的办法也都忘掉了。真的,每每认真琢磨一下这些事情,就感到郁郁不乐,半天都不能消除。最后,我把这一切都归结到对上天的感激之中,是他把我从那么多看不到的危险中解救出来,叫我远离了那些灾祸,而这些灾祸是我无法逃脱的,因为我完全不可能考虑或预测到会发生这些灾难。
这使我心头重新想起了我以前就有的设想,当我们在生活中遇到危险时,上帝总是慈悲为怀,使我们脱离危险。当我们还不知道怎么回事时,便已从中解脱出来,这是怎样的神奇啊!当我们犹豫不决,不知道该走这条路还是那条路,一种神奇的暗示就会引导我们走这条路,而我们当时本打算走另外那条路。而且,有时我们的感觉、意念或是我们的任务叫我们走另一条路时,我们心中却忽然有一股也说不出从哪儿冒出的灵感,也不知道是什么力量,硬逼着我们走这条路。而事实证明,如果我们走了我们要走的那条路,或是走了我们认为应该走的路,我们早被葬送了。
在此基础上,经过反复考虑,我找出了一条规律:不管什么时候,当心中有股神秘的暗示或力量,叫我去做什么而不去做什么,走这条路而不走那条路时,我必须服从这种神秘的指示。虽然我不知道心中这种暗示或力量是什么,但在我的一生中,特别是来到这个倒霉的岛上以后,我可以找出许多这样成功的例子。
此外,还有许多事情,如果我当时也用现在的眼光看问题,一定可以注意到,但只要自己能够意识到,从来都不会为时太晚。我想奉劝那些有头脑的人们,如果他们的生活,也同我一样,充满了种种不寻常的变故,或者即使没有什么不寻常的变故,都千万不可轻视这种神秘的上天启示。不管这种暗示是从什么看不见的神明意愿出发的,但这种启示至少可以证明精神与精神之间是可以交流的,有形的事物和无形的事物之间有着神秘的沟通。这种证明是永远不可推翻的。这一点我不准备在这里论讨,也不想加以说明。但关于这些,我将在我后半生的孤寂生活中举出一些很重要的例子来。
这些焦虑,这些长期包围着我的危险,以及需要我操心的事情,已经中断了我为生活安适和便利而构思的种种发明计划。如果我坦白承认这些,我相信,读者一定不会感到奇怪。我目前急需解决的是我的安全,而不是食物问题。我现在不敢钉一颗钉子,不敢劈一根木柴,生怕发出声音让别人听到。由于同样的理由,更不敢开枪了。尤其让我无法忍受的是不能生火这件事,惟恐白天老远就可以看见烟冒,坏了我的大事。
于是,我把手头上需要生火的事,比如烧制陶罐烟斗等,都移到森林中的新房去做。那个地方,我去了一段时间后,在土窝里发现了一个天然地洞,令我感到说不出的欣慰。这个地方伸进去很深,我敢说,即使是野人走到了洞口,也不敢冒险进去,除非是像我这样,一心想找个安全藏身之处的人。
这个洞的洞口位于一块巨岩下面,由于一次偶然(如果我没有充分的理由把这些事情归于天意的话,我只好这样说了),我在那里砍伐粗树枝,准备烧炭。在我讲我的发现之前,我必须先谈谈我制炭的理由:前面我已说过,我怕在我的住所弄出烟来,但是,不能烤面包、烤肉,我又无法住在那里。于是,我计划按照我在英国看到的办法,先在草皮泥底下烧些木头,烧成木炭,然后熄了火,把木炭带回家。每当家中需要用火时,可以烧炭,就没有冒烟的危险了。
暂且不提这些。当时我在这里砍柴,忽然发现在一片浓密的小树丛后,有个类似洞口的地方。我不免好奇,想进去看看,费了很大劲才走进洞口,发现里面居然很大,站直身子还绰绰有余,甚至还能再盛下一个人。但坦白地说,我一进去就赶快逃出来,因为当我进一步向里看的时候,在那漆黑的洞里,我看到了两只明亮的眼睛,不知道是人的眼睛还是魔鬼的,在洞口射进的微弱光线映射下,像两颗星星,闪闪发光。
过了一会儿,我才镇定下来,开始暗咒自己是个十足的笨蛋,告诫自己,如果一个人害怕魔鬼,他就不会孤独地在这个岛上生活20年了。我敢相信,在这个洞中,没有什么东西比我更可怕了。想到这里,我就鼓起勇气,拿起一根燃烧着的火把,又重新进入洞里。还没走上三步,我又像先前那样吓了一大跳,因为我听到了一声很响的叹息,就像是一个痛苦中的人发出的,继之而来的又是一阵不连贯的声音,像是只言片语,然后又是一声沉重的叹息。我大为吃惊,身上冒出冷汗,连连后退。如果当时我头上戴着一顶帽子,我不敢保证头发不会把它顶下来。但我还是尽量提起精神,想想上帝的力量和精神是无处不在的,能够时时保护我。想到这我又鼓起勇气,向前走去。我举着火把,把它举过头顶,借着火光一看,我看到地上正躺着一只硕大无比,老得可怕的山羊,无奈地喘着气,显然已快要死了,这个山洞大概是它选择的等待死亡的地方。
我推了它一下,想看看能不能把它赶出去。它也打算站起来,但却起不来了。我想了想,觉得还是由它躺在那里吧。因为它既然能把我吓了一跳,也会把那些胆敢在它活着时进来的野人吓一跳。
现在,我已从惊慌失措中回过神来。看了看四周,我发现地洞其实很小,周遭也就12英尺,既不圆又不方,没什么形状,显然不是人工制成的,而纯粹是天然形成。同时我又注意到在洞那头还有个更深的地方,但很低,我只能匍匐向前爬去,通到哪里我也不知道。前进了一会儿,因为没有蜡烛,我只好停下来,决定第二天带上几只蜡烛和火绒盒来(我用短枪上的枪机做出的),再带上一盘火种。
第二天,我带上六只自己制作的大蜡烛来到这里。我现在已能用山羊脂做出很好的蜡烛了。进入这个地洞后,正像我说过的,我被迫爬着向前,走了约有10码。顺便说一句,我认为这是件极为冒险的事情,因为我既不知道要走多远,又不知道它里面是什么。通过这段甬道后,洞顶忽然高了起来,足有20英尺。我敢说,我在岛上从未见过这样的地方,它的四壁和洞顶金光耀眼,蜡烛光在洞壁上反射着万道光芒。洞里到底是有钻石、宝石,还是金子,我说不上来。
这个地方,看起来可真是一个美妙的洞穴,而且正是我想要的,尽管里边很黑暗,地面上面铺着一层细沙,却干燥平坦。所以,这里没有讨人厌的毒蛇爬出,四壁和洞顶也不潮湿,仅有的一点缺点,就是入口处太狭窄,不过这正是我所希望的通路,对我很有利。我简直陶醉了,毫不迟疑地将我最担心的那些东西搬进洞中,特别是火药、多余的枪支,包括两支鸟枪、三支滑膛枪。因为我一共有三支鸟枪和八支短枪,所以在城堡里,依然有五支短枪。它们像炮似的架在我的外墙上,需要时可以随时取下来使用。
当转移火药时,我乘机拿出了从海里捞出的受湿的那桶火药,发现边上已有三四寸的火药浸湿了,变成了硬块,就像一个果核,使得里面的部分保存地很好,这样在小桶的中央我就有了差不多60磅的尚好的火药。对于当时的我来说,这确实是个令人欣喜的发现。于是,我把火药全都搬了过去,惟恐发生什么意外,城堡里只留下不到三磅的火药。同时,我又把做子弹的铅也全都搬了过去。
我把自己幻想成为一个古代的巨人,生活在岩石中的地洞里,据说任何人都无法接近他们。当我在地洞里时,我努力劝说自己,即使有500个野人追踪我,他们也别想找到我。即使他们能找到我,也不愿到此冒险来袭击我。
那个老山羊在我发现这个地洞的第二天就断了气,死在洞口边。我发现与其把它拖出去扔掉,倒不如在就地刨个大一点的坑,把它用土埋掉更容易些。我把它埋葬了,省得气味难闻。
我已在这个岛上生活了23年,对这个地方以及这种生活方式习以为常了。如果没有野人来打扰,我已经接受这种生活事实了,很愿意在这里度过我的余生,像那只老山羊,直到最后一刻,倒在洞里死去。我还找出了几件消遣和娱乐的事情,使我的生活比过去要愉快许多。
首先,我已提过,就是教我的波儿说话。它已经说得非常熟练,说得也很清楚了,这令我很高兴。它跟我生活了不下26年。至于它后来活了多久,我也说不清了。我知道在巴西有种说法,说它们能活一百年。也许可怜的波儿仍活在那里,一直到现在都在叫着可怜的鲁滨逊。我希望不要有任何英国人,那么倒霉,跑到那里,听到它的声音。而如果真有人到那里,他一定会认为那是魔鬼的声音。我的狗儿也是个令我十分开心的伙伴,它跟了我至少16年,后来老死了。至于我的猫,我已说过,它们繁殖得很快,我在开始就不得不开枪打死了几只,以免吃完我的一切东西。到最后,我带来的两只老猫死掉后,我又不断驱逐它们,不给它们东西吃,使它们都跑到树林里变成野猫了。只有两三只我喜欢的,我把它们驯养起来,而每当它们生出小猫时,我都把小猫溺死。这就是我家庭中一部分成员。
除了这些,我还养了两三只小山羊,我教它们在我手里吃东西。另外还有两只鹦鹉,也都会很好地说话,并且都会喊“鲁滨逊”,但没有一只比得上第一只。而实际上,我花费在它们身上的工夫远不及第一只。我还驯养了几只不知道名字的海鸟,是在海边捉到的,我把它们的翅膀剪掉养起来。我在城堡前所栽的树桩现在已长成了浓密的小树林,那些海鸟就生活在这些小矮树中,并在那里繁殖,真是有趣极了。所以我敢说,如果不畏惧野人,让我安全地生活在这里,这种生活已经让我心满意足了。
但事实却与我的愿望正相反,读到我故事的人们从中不难观察到这点。在生活中,我们越是想极力躲避的坏事,越是极为害怕的坏事,却往往是我们获得解救,摆脱烦恼的途径。在我离奇古怪的一生中,我可以举出许多这样的例子。我在这个岛上最后几年的可悲生活中,这种情况表现得极为明显。
我说过,这是我在这里的第23个年头的12月份了,正是太阳在最南端的冬至。这里的十二月,根本不能算是冬天,是我收获的季节,需要我经常外出呆在田里。一天大早,天刚微微亮,忽然我很吃惊地看见在离我很远的岛的尽头,大约有两英里海岸边亮着火光。那里正是我以前看见野人的地方,但恼人的是那地方不在岛的那边,却在我这边。
看到这些后,我确实惊惧至极,呆在小树林里再也不敢出来,惟恐受到突然袭击。并且心中再也无法平静,想到这些野人在小岛上走动,可能会发现我那些还在长着的庄稼和收割下来的庄稼,以及我的那些工事和设施,他们便会立刻觉得这地方有人,那时他们不把我找出是不会罢休的。在这危急关头,我径直跑回城堡中,收起了我的梯子,并把一切收拾得看上去尽可能荒芜而自然。
然后我在城堡里面做了准备,使自己处于临战状态。我支好所有的大炮,我自己这样称呼,其实是我的步枪。我把它们放在新防御工事上,并装好所有的手枪,准备抵抗到最后一口气。同时我并没有忘记祈求神的保护,我挚诚祈祷上帝让我从这些野人手中解脱出来。我在这种临阵状态中呆了有两个小时,便急不可待地想去外边看看,因为我没有探子可以替自己出去看看。
我坐了一会儿,考虑着怎样对付他们,但不久便忍受不了在这里呆坐了。于是我把梯子搭在小山的一边,登上了我提过的那块平地上,把梯子拉上来,又搭起来,登上了山顶,拿出我特意带上的望远镜,平卧在山地上,开始向那个地方望起来。很快就看见约有九个裸体的野人围坐在一小堆火旁边,显然不是为了取暖。据我推测,他们是在煮他们带来的残忍的人肉,只是我不知道他们带来的野人是活的还是死的。
他们共有二只独木船,都已被拖到岸上。这时正是退潮的时候,依我看,他们要等到潮水再来的时候才走。当我看到这些时,内心的慌乱简直无法想像,尤其是我看到他们就在岛的这边,离我又这样近。但我又想到,他们一定是借助潮水的涨潮来到这里时,心里变得安稳了,因为只要他们不在岸上时,我就可以在潮水涨起时安全地出门了。观察到这一点,我以后就可以从容地去收割庄稼了。
果然如我预料的那样,当潮水向西流去时,他们就全部上了船,摇着桨离去了。我可以观察到,在他们离去前一个小时,还跳了一阵舞。通过望远镜,我还可以很容易地辨出他们的舞姿,再仔细观察,可以看到他们全都赤裸全身一丝不挂。但至于是男是女,我就分辨不出了。
我一看到他们上船离去,便拿了两支枪扛在肩上,把两支手枪挂在腰上,又拿了一把不带鞘的长剑挂在腰边,往那座小山跑去——那里是我最初发现这些迹象的地方。差不多用了两个小时的时间,我才到了那里(因为我身上背那么多武器,走不快)。我爬上山,只见海上还有三只独木舟,再往远处望去,看见他们在海上会合后,向陆地驶去。
真是一个可怕的景象。对我来说,更可怕的是我走下海滩以后,所看到的那些遗迹。那是他们所干的罪恶勾当留下来的,全是那帮野蛮人以娱乐方式吃剩的鲜血、人骨和块块人肉。看到这些我义愤填膺,下定决心,下次再让我看到这些,我一定把他们全干掉,不管他们是谁,也不管他们有多少人。
很明显,他们并不是经常光顾这个小岛,因为他们过了足有15个月之久才再次登岸,也就是说,在这段时间里,我从没有见过他们,也没有看到他们的任何脚印,任何痕迹。因此看起来他们在雨季里是绝不会出门的,至少不会来这么远的地方。但这段时间里,我还是过得极不舒服,因为时时担心他们会来突然袭击我。从那以后,我总是担心坏事的发生,这种痛苦比遭遇到坏事还要厉害,尤其是当我无法摆脱掉这种担忧和这些想法时。
在这段时间里,我一直有一种要杀人的冲动。我把能够利用的大部分时间都用来计划在下次看到他们时,怎样以计取胜,怎样袭击他们,尤其是提防他们分开前来,就像上次那样分两部分前来。我根本没有考虑,如果我把他们其中一部分杀光了,比方杀死十几个,但到了第二天,第二个星期,或是第二个月,我还要杀死其中另一部分。这样下去,到最后我将变成一个不亚于这些食人者的凶手,甚至比他们还要凶残。
我现在是在极为忧虑和焦虑中度日,料想着总有一天我会落入这帮凶残不仁的野蛮人手中。如果偶尔冒险外出,总是小心翼翼地东张西望。不管怎样,现在我有一群驯化的山羊,这是令人十分快慰的事,因为我在任何情形下都不敢再开枪。
我尤其不敢在他们经常来的岛这边开枪,惟恐惊动这些野人。我料定,即使我能把他们吓跑,不出几日,他们又会卷土重来,而且可能带来两三百只独木船,其后果就可想而知了。
然而,我又消磨了一年零三个月的时光,也没有再见到一个野人。后来,我才又发现了他们,这些我将在后边讲到。事实上,这期间他们也许来过一两次,或许他们没有停留太久,所以我没有听到他们的任何动静。但是,大约是我来这个岛上第24年的5月,我又很奇怪地同他们相遇了。我将在下面讲到这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