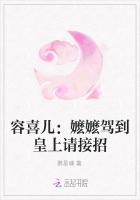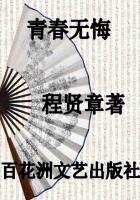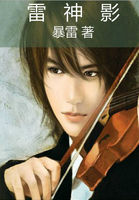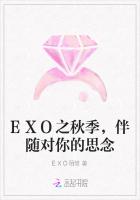——司马光评唐朝节度使由军士废立(臣光曰100)
唐肃宗乾元元年(758),上距唐朝开国140年,下距唐朝灭亡149年,差不多介于整个唐朝289年历史的中间点。而这个中间点,对于有唐一朝,意义十分重大。因为过了这一年,先前说话算数的皇帝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说话不算数的皇帝。坐大的强藩悍镇,不再拿圣旨当一回事。于是全国一盘棋,变成全国一盘沙散,山头林立,各自为镇。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会有如此严重的挫裂力呢?且看历史的说法。
是年十二月,平卢节度使王玄志死了。唐肃宗派中使(太监)前去抚慰将士,并负责调查摸底。看看将士们是否有中意的节度使人选,如有,就依他们的意思,“授以旌节”。裨将、高丽人李怀玉乘机杀死王玄志的儿子,推立姑丈侯希逸为平卢军使。唐肃宗竟然默认了,因以侯希逸为节度副使。《通鉴》说:“节度使由军士废立自此始。”
这件事情初初看来似乎极平常,但其后坐影响力却是无穷大。节度使由军士擅自废立,无疑宣告了朝廷对藩镇的全面失控。此一点与大将的玩寇之志(《玩寇的起因》),及后来的宦官之祸,实际上构成了唐室乱政的三大主因。
司马光“臣光曰”第100篇评论了此事,文章很长,归纳起来主要有如下几层意思:
一,尊卑有分,是为了免生觊觎之心。因为人之性情,皆有锦衣玉食的欲望。因此,需要有礼,让世人明了各自的定位,免生非份之想,这样现世才有秩序。而皇帝行使“爵、禄、予、置、生、夺、废、诛”这八大权力以御下,便是要确保这个秩序的有条不紊。如果人君做事失了这个权柄,那如何有效地领导手下人呢?
唐肃宗时遭中衰,幸而复国,理应借此时机,大力阔斧,整顿朝纲,“正上下之礼以纲纪四方”。可是唐肃宗却苟且一时之安,不思永久之患。“偏裨士卒,杀逐主帅”,朝廷不以为罪,反顺水推舟授以职任。这就是典型的姑息了。如此一来,大家也跟风,手握重兵的将帅之任免,不由中央,全凭将士之喜好,乱局哪会有终了的时候?
二,清明之世,必是赏善而诛恶。奖赏善举就是为了劝人为善,惩罚恶行就是为了戒人作恶。而唐肃宗放过杀人的李怀玉,又依从他的意思任委侯希逸为节度使,无疑是肯定、奖赏、鼓励这种恶行。
于是乎,作为部下,一门心思要取代上级,一有机会,便毫不犹豫地动手。作为上级,丝毫没有安全感,老得提防着部下,一有风吹草动,也要乘其不备而杀之。彼此都想着先发制人,岂是长治久安之计?
胡三省说,此“二言曲尽唐末藩镇、将卒之情状”。我以为,唐代后期的藩镇割据,跑不出这二个路数。其结果是士卒可以欺陵副将,副将可以欺陵将帅,那么将帅欺陵天子,也就势所必然的了。
事实亦是如此,目不识丁的朱温最后凭着精兵强将,篡了唐朝去。之后的五代,军人乘权,祸乱继起,兵革不息,民坠涂炭。藩镇与五代,前后大乱几二百年。
追原藩镇之乱的根源,唐肃宗实难辞其责。唐肃宗就如西汉的元帝,实为有唐国势之分水岭。唐肃宗是自废“武功”,礼由天子自坏,并非臣下坏之。周易说:“臣弑其君,子弑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来者渐矣。”其渐始自唐肃宗,最后上下习以为常,尾大不掉。朝廷再无有足够强大的势力,将兵权收归中央,只好眼睁睁地看着武人蛮横。继起的宋太祖,有鉴于此,易以文臣出将,藩镇横逆之局面才得以终结。
关于司马光追责唐肃宗的观点中,清初王夫之提出异议。他认为,察将士之意愿而立帅,并不是什么不好的事。这样不但可以避免军士因不服主帅而产生内讧,而且会促成“军效于将,将效于国”,上下一条心。
王夫之有点现代民主的意思。但问题是,这样选出来的将帅,只看部下的脸色,不看朝廷的脸色怎么办?一国三公,政出多门,这样的国势也就可想而知了,更谈何效力于国家呢。
附:臣光曰100:夫民生有欲,无主则乱。是故圣人制礼以治之。自天子、诸侯至于卿、大夫、士、庶人,尊卑有分,大小有伦,若纲条之相维,臂指之相使,是以民服事其上,而下无觊觎。其在周易,“上天、下泽,履”。象曰:“君子以辨上下,定民志。”此之谓也。凡人君所以能有其臣民者,以八柄存乎己也。苟或舍之,则彼此之势均,何以使其下哉。
肃宗遭唐中衰,幸而复国,是宜正上下之礼以纲纪四方,而偷取一时之安,不思永久之患。彼命将帅,统藩维,国之大事也,乃委一介之使,徇行伍之情,无问贤不肖,惟其所欲与者则授之。自是之后,积习为常,君臣循守,以为得策,谓之姑息。乃至偏裨士卒,杀逐主帅,亦不治其罪,因以其位任拔之。然则爵禄、废置、杀生、予夺,皆不出于上而出于下,乱之生也,庸有极乎。
且夫有国家者,赏善而诛恶,故为善者劝,为恶者惩。彼为人下而杀逐其上,恶孰大焉。乃使之拥旄秉钺,师长一方,是赏之也。赏以劝恶,恶其何所不至乎。书云:“远乃猷”。诗云:“猷之未远,是用大谏”。孔子曰:“人无远虑,必有近忧”。为天下之政而专事姑息,其忧患可胜校乎。由是为下者常眄眄焉伺其上,苟得间则攻而族之;为上者常惴惴焉畏其下,苟得间则掩而屠之。争务先发以逞其志,非有相保养为俱利久存之计也。如是而求天下之安,其可得乎。迹其厉阶,肇于此矣。
盖古者治军必本于礼,故晋文公城濮之战,见其师少长有礼,知其可用。今唐治军而不顾礼,使士卒得以陵偏裨,偏裨得以陵将帅,则将帅之陵天子,自然之势也。由是祸乱继起,兵革不息,民坠涂炭,无所控诉,凡二百余年,然后大宋受命。太祖始制军法,使以阶级相承,小有违犯,咸伏斧质。是以上下有叙,令行禁止,四征大庭,无思不服,宇内乂安,兆民允殖,以迄于今,皆由治军以礼故也。岂非诒谋之远哉。(《通鉴》卷2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