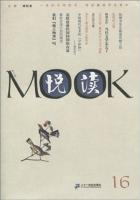北方人最爱盘炕。那炕好大,好暖啊!说那样睡着舒坦、平整、腰板直。
故乡的土炕,我对它寄予着无限深情。
盘炕其实就是砌炕。砌炕的学问也挺大的哩!盘炕技术若好,烧火做饭时火旺,不倒烟,省柴禾,满炕热。盘不好,火不旺,倒烟不说,极费柴禾还烧不热炕。尤苏夫大爹可是咱村上颇有名气的炕把式。经他盘的炕,几乎没有不热的,关键在炕洞门上那四块双层面子支的直不直,烟囱嘴子上的两块斜着的三棱子坷垃别摆“歪”了。村人争先效仿尤苏夫大爹的盘炕方法,其效果依然不及他老人家那一手。
细算起来,我睡热炕的年月并不短,打从出生那阵子,一直到进城两三年后,才基本与土炕脱离了关系。好说歹说也有近20年的历史。土炕伴随着我度过了人生中最欢乐、最有情趣的童年时光。城里人一提及土炕,脏乎乎,土叽叽,满屋子尽是土星子,那股子讨厌劲无从说起。其实,炕盘好后,将炕面上用精泥抹平整、光滑,再用一块较好的粗木板做一个比炕面高出近十厘米的木炕沿。讲究的人家用木推子将木炕沿推刮得光溜溜,再用砂布打几遍,淋上香油,反复搓擦,使木炕沿更加光亮照人。年代越久,炕沿磨得越亮晶,色儿越深。平实而论,有高炕沿挡着,土炕上的土星子是飞不过来的。老家那一带的土炕都是靠着窗户盘的,两间大的屋子一盘炕就占去一半的空间,却也显得宽敞、亮堂。
进城10多年了,母亲还是舍不得在仅有40平方米的两间屋子里盘一土炕。前些日子,弟兄几个为了让两个老人安度晚年,在正街区买了一套三居室的楼房,母亲仍然坚持一定要给她盘一土炕。否则,她就不住。人老了,睡个土炕,觉得心里踏实些,有滋味,遇个头痛脑热的,烧热炕,盖个厚被子,发身汗,浑身的关节痒酥酥、怪舒服的,胜似温泉浴,别提有多实惠。的确,像母亲这样朴实、厚道的农家妇女,苦日子过惯了,对新时代的“洋床”并不适应,最好不过还是睡她的土炕。这也许就是北方人刚毅、耿直的缘故吧!
土炕大,睡满了能躺十几口人。有的人家因条件所致房子窄小,一家几代人就挤在一条土炕上。那些年不搞计划生育,说是一只手能提篮,两只手能端盘,千万只手能移山,哪家不是大花、二林、三丫、四尕、五宝、六小的,丫头尕子一大群。一般家庭养个五六口还算正常,多的还有养十三四口依然不负众望。如果是睡城里人的木床,就是两人一张,光床板也得好几方木料。且不说争铺夺盖,就是夜里乱蹬乱踹也够老娘受的。尤其是冬天。土炕的优点更加发扬光大,一天三顿火,烧得热呼呼、暖烘烘的,尕子丫头们的小脑袋依次排下去,好似一窝肉乎乎的小雏燕,叽叽喳喳,吃着炒熟的玉米、黄豆,嚼着胡萝卜,其乐无穷。老人看在眼里,暖在心里。很多的时候,再听些“故事篓子”爷爷讲的许多美丽动人的回族民间故事,诸如《抢枕头》、《要口还》、《弯弯棍》、《玉石桌》等进入梦乡,似乎连做梦都是香甜有味的。
童年的土炕给我们的生活注入了无限情趣。很小的时候,母亲为了养家钥口,多挣工分,生下我们五六个月就在土炕边上插一木棍,用宽布条将我们揽腰拴好,系在大棍上,卷去炕单、铺盖、被褥,只留一张竹席子,上面铺上厚厚一层干绵沙,就匆匆出门做活去了。偷闲的工夫,母亲急猴猴地回来喂几口奶继续上工。尿了屙了全渗进沙子里。加上土炕老娘临走时烧了又烧,尿湿的沙子也会很快被烘干的。绝对不会因为长时间湿沙而腐蚀我们幼小嫩软的皮肤,也不会给卫生院送那苦涩的医疗费。
长大一点后,土炕依然是我们快乐的舞台。我和哥哥、弟弟、小妹4个人,曾经在头上缠上一根带色的细布条,身上被裹着被单、炕单,手持木棍、笤帚、灰刷,扮演孙悟空、猪八戒、沙僧护送师傅西天取经。在脖颈上插上两根嫩绿的柳条或公鸡毛当穆桂英。碗、筷伴奏,举行演唱会。
冬天,庄户人的生活没啥新花样,想吃个新鲜菜还得到四五十里开外的县城里买。可那阵根本没那个条件。母亲为了调节我们的生活,在炕头上放一口大盆,放上捡好的黄豆、黑豆和蚕豆,添上水,捂好盖,生豆芽菜。过不上三天那豆子就张开了黄白黄白的小嘴嘴,露出一根短短的小尾巴,怪诱人的,母亲从这时开始天天用它给我们熬米粥、做米饭、煮面条,一直吃完为止。母亲经常是这盆快完,那盆连忙又捂到了炕头一边。有好几年,母亲还将抱窝的老母鸡“请”上炕头孵蛋,20多天后,那些圆圆的生鸡蛋里就会爬出一群活泼可爱的小鸡……
入冬的时候,土炕就必须换一次,换下来的炕面子和坷垃支子,被柴烟熏得黑油油的。是农家上好的肥料,最宜小麦田施肥。上过土炕肥的小麦长得又黑又绿又厚实,穗头大,产量高。困难时期,穷人家牲121少,积不出什么好肥,就半年换一次炕。记得70年代初期,俺村正好处在“三边一梢”地区,紧靠黄河边,人多地少,人穷马瘦。尤苏夫大爹因家庭拖累大,生活非常困难,又没有到外头去卖苦力的能耐,好在自己有一手盘炕的本事,专门给庄户人盘炕挣口粮。有的家户一年换三次炕,他都一样尽心尽责,不怕脏、不嫌累给人家往好里盘。后来有人告他专门干制造假肥料上地,破坏农业学大寨,挨批受斗五六年,他从没有弯下腰,叫出个声来。
前年早春,我因尤苏夫大爹的邀请,前去参加他孙子的婚礼。发现他几个儿媳妇的屋里全都拆了土炕换上席梦思床,我的心里一阵酸楚,真想不到拆炕那阵尤苏夫大爹的心情是怎样的翻腾。二媳妇插话道:“现在俺爹那套子早已过时了,谁还睡那个土炕,真不嫌麻烦,盘了拆,拆了盘,土都没处搁。再说谁还上那土炕肥,国家造的优质化肥都用不过来,你说盘个炕不是自找苦吃吗?”三媳妇连忙插话:“现在只准生一个孩子,土炕没啥用处,还占地方的很呢。铁炉子、电褥子都眼看快过时了。俺还想今年秋天收完庄稼,装几片子土暖气呢!”我无言可答,心里像失落了许多难以把握的东西,极为伤感。尤苏夫大爹似乎看透了我的心思,说:“尔里,人家爱咋折腾折腾好了,走,到大爹的寒窑里坐坐。”
要是与那三个小子四面红的红砖房相比,尤苏夫大爹住的房子大概要倒退二三十年,依然还是那间被柴烟熏透了的土坷垃房子,又黑又暗,墙上掉土的地方,他已经用旧报纸都糊上了。让别人看,这老头肯定是五保户,谁还相信他有三个儿子两个丫头呢。尤苏夫大爹把我让到了他的土炕头上,颤抖着双手给我沏了一盅子香喷喷的盖碗茶。那土炕坐着暖乎乎、痒酥酥的,怪舒坦的。坐着坐着还有些不想起来的意思。三小子开玩笑说:“尔里哥,等俺爹多盘几个土炕,让那些洋人来睡睡咱中国人的土炕,兴许还能赚几个外汇呢!”我忍不住笑了。尤苏夫大爹直骂儿子不如他的土炕亲。
的确,故乡的土炕已经被现代文明所代替,但土炕留给我的回忆却永远是温馨的。
故乡的土炕,好大,好暖的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