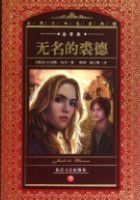做梦也没料到李安森会出事。上回他送的烟我还没抽完。我们还说好了,过些天我约几个朋友,带上老婆孩子上他们今年开张的岚湖渡假村乐几天。这才几天哪?怎么说倒霉就倒霉了?
所以肖玉打我手机时我根本没反应过来。她说是李安森老婆和弟媳妇来了,这会儿正在家里等我,要我赶紧回去招呼。
我只当又是李安森让她们带什么东西来了,随口就叫肖玉把她们领到我这儿来。刚好我跟几个电台的哥们吃烧烤,这会儿刚入席。我说这儿都不是外人,其中两个还跟我去过东泰镇,吃住就在李安森弟弟开的酒店里。那酒店的生意可真叫红火,镇上的应酬招待基本都归他承包了。所以我啥时候去那儿,楼下大堂里都是扑鼻而来的酒气。但李安森弟弟和他完全不是一个脾味,虽说他是老板,却不善应酬,见人总是目光闪烁,从来不敢与人对视,也很少上席喝酒。他那媳妇可了不得,长得白里窜红怪撩人,开席前也静静的,手脚麻利地端茶递烟,见谁跟谁笑,那两个小酒窝现在又在我眼前闪。可是一旦她撸起袖子劝开酒来,天天在酒山肉海穿行的李安森都不是她的对手,谁不喝就捏鼻子灌。她还是个黄段子高手,手机上有的、酒桌上流行的,没有她不熟悉的。今天有了她,这酒就更有味了。不过我这席上可有高手,她还敢像乡下那么猖狂的话,怕也够她喝一壶的。
不过我也多少有那么点儿预感,李安森弟媳和老婆跟我从没有直接交往,怎么突然就摸到我家来了,不会有什么要紧的事吧?
正想再问问,手机又响了。肖玉压低声音说她们不肯来,嘴上说也没什么事,神色上看肯定有要紧事。反正她们一定要和我见上一面。我有点犯难,但也没太往心里去,叫肖玉给她们弄点吃的,我招呼完客人尽快回来。可一杯酒刚下肚,肖玉的电话又来了,说是李安森老婆想跟我说句话。我来到包间外,话筒里传来的却是他媳妇的声音。怯怯的,全没了酒席上那份嚣张。我刚跟她开了句玩笑,那边就哭开了:我大哥他……进去啦!
你是说李镇长……我的背上嗖地窜过一阵凉风:进去了是什么意思?
手机里又换成了李安森老婆的声音:大哥你别听她乱说,是……双规。县里纪委抓的……大哥你帮帮他吧,我都两天没睡觉了……麻烦你千万帮我找个什么关系说说话。受啥处分都可以,千万不能往检察院送了。
有这么严重吗?我还是难以相信:李镇长多好的一个人,他们凭啥抓他?
这个……要不您先吃饭,一会我再跟您详细汇报?
这种事的确不是电话里方便说的。于是我答应马上赶回去。可总觉得这事来得太蹊跷,实在难以置信。于是下意识地拨通了李安森的手机。果然,手机提示已关机。
我没了喝酒的心思,编了个借口就急急地下了楼。
其实我跟李安森也非亲非故的,甚至未必算得上过从密切的挚友。毕竟我在省城,他在乡下,一年里除了我会去他那儿玩几回,平时也就是偶尔通个把电话。有时他会让人带点东西给我,春节上省里来进贡,他也会顺便捎上我一份礼品,却也从来没工夫和我坐下来喝上回酒。
算起来,我结识他也快三年了。省电视台专题部要给东泰镇搞个十分钟的宣传片,让我给他们写本子。那回镇上书记到香港去了,接待我们的就是李安森。也不知是不是有缘分,我跟李安森一见如故,几乎毫无障碍地就热乎了。李安森个子不高,岁数和我差不多大,四十刚出头;说话洪亮而自信,为人颇有亲和力。加上那黑苍苍的圆脸盘和虽已开始发福却仍很壮实的身躯,一看就是个典型的颇富进取心的乡镇干部。
我们的迅速热乎,起先多半还是酒的缘故。我们都属于那种爽快型的,热爱喝酒却没多大的量,三杯下肚就没了彼此。我没把他当镇长,他也没把我作主任,拍肩膀掐脖子碰得杯子叮■响,浑身热血沸腾。酒席散了,我们还都没够的意思。李安森让镇办主任把其他人都打发去休息,却搂着我不让回房。俩人在热哄哄的镇街上轻飘飘地乱窜。李安森一脸豪气地要我实地体验一下东泰的夜景,一路上则还不断地和一个又一个堆满谄笑的“子民”们打哈哈。
和一般地方干部一样,李安森也惯于用“我”来指代自己麾下的这方水土。张口我的GDP多少多少,我的招商引资怎么怎么了。总之我这么,我那么,指的就是东泰镇怎么了。俩人大摇大摆在街上晃悠时,他一会指指这座楼说这是我搞的,一会又指指那个工厂说那是我引的资,不无自得。一路上不断有认得他的“子民”满脸谄笑地和他打招呼。他有时哼哈两声,有时则手拉手地打一阵哈哈,还把那什么主任什么总的热烈地介绍给我。别说,那一路我也大有几分荣耀的感觉。这东泰镇之所以愿意花上8万来做这个资料片,固然有宣传引资的目的在,首先也确实有做的资本。镇面扩张得很厉害,新老两区风格迥异。老街上还见得到千百年前传下来的老虎灶,新区则煊煊赫赫一派灯火,俨然一座欣欣向荣的新城。快十点了,街上还人头攒动,商店里挤满外地口音的打工者,饭馆里处处哄响着划拳的声音。那市面,那规模,比起一般地区的县城来也毫不逊色。
李安森说得兴起,抄起手机哇哇一顿吼,不一会他的司机就把车开了来。李安森挥挥手打发走司机,自己开上车,不一会就把我拉到镇外的东泰开发区,四面八方转了一大圈。清泠泠的月色下,规模相当可观的开发区被银亮的路灯勾勒出网状交叉的英姿。一排排颇现代的厂房里灯火交辉,空气里都涌动着热火朝天的气势。李安森跳下车,热得发烫的手掌一把捏紧我的手,怕我跑了似地拽着我这里看看,那里望望。他大敞着怀,嘴里滔滔不绝,说到激动处还啪啪地拍打他那浑硕的肚皮,细微的唾沫星子频频溅在我脸上。我只好不断调整位置往上风去,但不是左手便是右手则始终被他捏在汗叽叽的手心里。说起来,我并不是个懦弱的人,虽是客人,但身份地位都不在他之下;但在他面前就总有种身不由己的臣服感。应该说这也是他的一种魅力,或者也可说是某种习惯性的霸气吧,让人不由自主地会给他牵着鼻子走。不过我对这种人倒并不讨厌。
我们重新上车后,李安森却不急于发动车子,双拳支在肚腩上,歪着头盯着窗外那一派光晕出神。那神情恋恋的,又分明有几分陶醉。突然,他长嘘一声:两年呵!整整两年我彻头彻尾地卖给了这片鬼地方!刚开工那阵子,连绵阴雨,工地都泡成了糖稀糊,一脚下去泥浆滋满长筒靴,只好甩掉靴子打赤足巴子。我那指挥部的床上,被褥都是泥迹巴拉的——哪天夜里不让人喊起来好几回!黑灯瞎火地摸回来,两条腿全靠用手搬上床,哪还有心思洗什么脚呵,倒头就着。刚才喝酒时,你们那编导唱什么?“想亲亲想得我胳膊弯弯软,提起个筷子来端不起个碗”,我的泪一下子滚进了酒杯里。可是那时候鬼才有心思想什么亲亲哪,成天累得你两条胳膊端茶杯喝水都直哆嗦……
我不禁偏头想看看他是不是眼里有泪,但轰地一声,车子抖擞着吼起来。他急打方向盘,小车猛地拐上大路,箭一般射了开去——
天地良心,我连一个铜板也没多得!
回到宾馆,编导拉我们打牌。令我意外的是,李安森说他不会打牌,也不会玩麻将。农家出身的他,上大学前为跳出农门拼命读书。工作后为出成果则拼命工作。他也坦承,尽管大学时他曾是文学爱好者,但现在已好几年没看过一篇小说。主要就是一个字,忙、忙、忙。招商、引资、GDP,指标一年比一年高。农田、水利、城镇建设;萨斯、禽流感、抗旱防汛,没一样事情松得下来。天天鸡叫忙到鬼叫,年年没有双休日的概念。春节也顶多在家呆上一两天,甚至记不清自己是哪一年在家吃的年夜饭……
那回我写完东泰的解说词后,顺手给李安森写了个报道,在我们省报上发了半个版。李安森也很上路子,特地让他司机送来一箱“东泰优特”,一大篓螃蟹。
扑面清风一吹,我的头脑清静了许多。右脚随即压到了刹车板上。急着回家干什么呢?他老婆似乎把希望都寄托在我身上了。我该如何去面对她?
跟李安森好上后,我沾过他不少光,他倒是从没有求过我什么事。这回虽说不是他找我,却无异于他求我了。而这种事情我能帮上什么忙,又能帮到什么份上呢?不能说我完全没有办法,但却未必是管用的办法。许多亲朋的音容和电话在我脑海里飞速旋转,却一个也立不起来。“人”到用时方恨少呀。
脑海中再度浮起一个人来:何定一。其实我最先想到的也是他。我和他虽不能算是哥们,过从倒也不薄。我写过他两篇报道,对他去年的立功应该是不无助益的。他刚好是李安森那个市的纪委四处主任,虽说这案子不一定是他抓的,县纪委是他们下级,他要肯斡旋,但有几分可能,下面不会不给他面子吧?找他无疑是最对路的。可是拨通他电话后,我才意识到,我处理这类事太没有经验也操之过急了。何定一问我具体情况,我却是一问三不知。只好反复求他帮忙做做工作,不管什么事,能大化小小化了最好,不能,起码也别往检察院送了。
老兄哎,这可不是由谁说了算的事呀。何定一似乎没为我的焦灼所动,也不知是说话不方便还是怎么,他的声音里完全没了以往的热情,听起来始终像哽口痰似的,遥远而压抑:你想想,他犯的是什么事,证据如何,我现在情况不明,怎么能承诺你什么呢?不过凭我的经验,他的麻烦恐怕小不了。如果不是有什么大把握,县里轻易不会办镇一级干部的双规。而一旦到了这一步,不移送的可能也不大呵。
所以要劳你的驾嘛!
问题是……这人到底是你什么人?如果是亲戚的话,你对我不妨明说。
这倒不是。
那你何必掺和这种事嘛。
话不能这么说,根据我对他的了解,李安森绝对是个好人。起码,他对东泰的贡献是远大于过失的……
我想起来了,我好像是看过你写他的文章,对不对?何定一忽然发出一声怪笑:但是老兄呵,我也看过你写的那些反腐文章呢!
何主任你不是在骂我吧?我突然有一种被何定一抡了一警棍的感觉:李安森在我心目中和什么腐败分子是挂不上钩的。
我相信你这种感觉。不过凭你我的了解,我还是想请你原谅我说句实话:根据我的经验看,凡我们办过的人,没有一个不是被一些人看作该打该杀的贪官污吏,而又被另一些人看作至爱亲朋的。这也正常,人总是有感情的嘛,包括我,也不可能不为你的感情所动。所以嘛……这样好不好,我明天给他们打个电话,先摸摸底再说,如果没有太实质性的证据的话……
拜托你了!
我机械地发动引擎重新向家里开去。心里却突然感到异常沮丧。按说我已经尽力了。李安森也的确算不上我的至爱亲朋,何定一毕竟还没有把门关死,那么我不应该有什么负疚了。但我总有点悻悻然,却又一时想不清是什么原因,但肯定和何定一刚才的话有关。这家伙!看来这号人不管你和他交情如何,恐怕也永远成不了交心朋友的。
李安森却属于那种很快就能跟你钻一个被窝睡觉、掏心窝子说话的朋友。
我后来有空了或者心烦意乱想散散心的时候,最爱去的就是他那儿。有时下班开车回家的路上,突然心血来潮,给报社打个电话说要下去采访,掉头就往东泰窜。有回还拉上帮铁哥们,呼啦啦三四个车一长溜冲过去。李安森顿时兴起,咋乎着叫弟媳搬一箱“东泰特优”来,谁也不许用小盅,一溜玻璃杯排开,他亲自倒水样哗哗往里灌……
不管去多少人,李安森总让我们住他新搬进的别墅里。他的房子在镇西口小山坡上。一片蜂飞蝶舞的梅花林中,掩映着8幢三楼三底的欧式别墅,黑漆铁栅和似乎家家都是同一个种的德国黑背,卫护着绿肥红瘦的庭园。车库、地下室应有尽有,一条条花木掩映的水泥路,把这8座令我唏嘘不已的别墅彼此并与外界沟通起来。
李安森喝多了喜欢和我睡一个房间,没完没了地海阔天空。
说实在的,这时的李安森比起刚相识的他来,我的感觉是和我更贴心了,他也明显更有成就感了。也不知几时开始,他脸上架了副金丝边眼镜。天再热,胸前也总是飘飘地垂着条质地上乘的领带。这使他在不喝酒的时候显得斯文多了。却也隐约让我觉着几分陌生。偶尔还会生出点让我暗中犯点嘀咕的东西。是什么东西,我一时辨不清,也不愿意去深究。比如他这座即使在下面,估计也起码值个百把万的别墅吧,李安森说是镇里统一征地、施工和装修,然后卖给镇上四套班子主要领导的。他们出了多少钱?我没好意思问。谁知李安森夜里自个告诉我,说是出的也是统一的8万块!我暗中咋舌没说什么,李安森却看透了我的心思,自己打着哈哈说,有的老百姓背后叫这是贪官楼——管他娘的呢,书记的主意,我不住白不住。再说了,我开发区里好些董事长、总经理的,哪个年薪少于这一栋楼的?我们这房子不过是沾点地价和造价的便宜,帐面上干干净净的,住里面的,起码我是算不上贪官的!
我觉得李安森的说法也不无道理。但也觉得这时的他自我感觉似乎有点太强悍,或者说不定是太脆弱了。和他打乒乓球时,我这种感觉就更强。他家的地下室就是稍矮点,面积也很宽敞。李安森在里面放了跑步机和乒乓球桌。每次去他都缠住我杀几盘。但与其说他球瘾大,不如说他好胜心太强,似乎球的输赢关乎他什么似的。5局3胜、7局4胜、9局5胜,反正只要他输,就必定要变换规则继续打下去,直到他胜出。其实他的球技决不在我之上,一看就是从小没机会养成正确的姿势,扣球时尤其好玩,整个身子是僵着的,胳膊又屈得过深,活像从腋下掏什么宝贝,怎么看怎么别扭。只是他打起来极认真,也凶悍,对付起来也有不小的麻烦。我先还和他较真,之后就放起水来,但还不能明显,否则他觉察到了反而不高兴。非要我“拿出看家本领来”和他重来不可,但结局又非得他胜才停得住。
还有一个让我有点吃不准是他本性如此,还是因为对我彻底没了戒心的事情是,这家伙对我毫不掩饰他的某种邪性,而且行为方式还颇另类,有时简直就是肆无忌惮。见多识广的我也不免暗自为他抽几口冷气。我指的并不是他领我到“外省考察”的事。这种事在时下的某些官员那儿并不是个值得大书特书的异象。
所谓到外省考察,实际上也就是到和东泰紧挨的午阴乡去找小姐“敲背”。午阴乡是两省三市的交接地,是个似乎谁都可以管,实际上谁都管不好的飞地。
那晚我们在按摩室美美地敲了把背,又回到包间呼呼地睡到天快亮。使我惊异的是李安森做这种事时居然也毫无顾忌得可说是猖狂。这时电影“手机”正热播。我怕老婆来查岗就关了机,结果李安森指着我鼻子大笑我“太没用场”,居然当着我面给家里打手机,啪啪拍着小姐屁股对老婆喊:我在外省陪客人敲背。这小姐肉嘟嘟的,比你性感多啦……
我正怀疑她是不是真打给了老婆,这家伙却把手机贴我耳根上了。正听到他老婆乡音十足的嗔骂:稀罕她你就跟她过去,再也别给我死回来……
他还得意地翻出手机上储存的信息吱吱地揿给我看:什么破“手机”,说什么老婆到电信局打通话清单,这种事也值得拍电影来骗钱,冯小刚也太无聊了。
如果不是亲耳听李安森给他老婆打电话那口气,我完全不可能相信李安森的话是真的。可他显然真是无所顾忌。他手机上储存的那些信息,哪一条要让我老婆看了都会跟我拼命:“亲亲,你又在泡小姐吧?老让我独守空房,你太狠心啦。”“我的脑海里涨满了你,我的身子在蠕动,我在呻吟,哦,你好狠心呵……”
这时的李安森就完全不像平时的李安森了。我惊诧他老婆怎么能容忍这些。也怪他这么刺激老婆太残忍。他却依然振振有词,熏人的酒气喷得给他做面摩的小姐脸扭得老远:我可是样样都满足她了!无论是虚荣心还是最实惠的钱,一个女人想要的她都得到了,还有什么好说三道四的?再说她对我也没什么不放心的。她太清楚现在的世道啦,知道我也不容易。只要我不碍她根本,吃点、喝点,玩点,她也只好睁眼闭眼算了。再说了,难道你真当我是喜欢这种颓废生活的人吗?狗屁!半夜里酒醒过来我不知抽过自己多少回耳光。可他妈的身不由己啊!听起来倒是堂堂一个富得流油的大镇之长,实际上前些年还有那么点成就感;现在倒好,一年三百六十五天里,起码两百天是泡在酒精和会议里,成天还忙着虚应故事、应付四面八方横里竖里的各色人等;你也知道,现在的人吃什么山珍海味都嫌淡,钓鱼什么的也早就腻了……不过我也不是贱胚,除非要紧人物,一般的我都让下面陪了。在这种地方陪人,感觉他妈的就是三陪男啊……
我不禁有点脸红。李安森一眼看出我的不自然,哈哈一笑猛敲脑袋:喝多了喝多了,你老兄应该是相信我的。像你我这样没有功利色彩,能让我一吐郁闷的哥们,我可是求之不得呀……
我连说是是,却见他已大仰八叉地闭上了眼睛。不一会却又似睡非睡地嘟哝了一句:说句良心话,老婆倒是我前世修来的福。只不过……现在的男人,没几个对得起老婆喽……
他这话我信,尤其对于他而言。他老婆对他也真是没话说了——问题是,她显然过于高估我的能量了。这叫我如何是好?
停好车,我迟迟不敢上楼去,拖着两条软塌塌的腿在楼下打了好几个转转。
我抱着试试看的心态,又给几个估计能有点办法的朋友打了电话,得到的都是爱莫能助的答复。有两个还郑重其事地劝我别多事,你们再好也终究不是亲兄弟,有个意思就行了。这种事不比别的,弄不好自己沾一身腥。我不爱听这种话,却也大大泄了气。再想想自己也真算是尽了力,许多事人算不如天算,李安森命当此厄,我又奈之何?
不出所料,李安森老婆一脸的憔悴与焦灼,嘴角还蝇屎般簇着堆水泡,说话怕疼,总拿手护着。向来印象中静弱少语的她,如见救星般一步冲到我跟前,刚招呼过我,就泣不成声了。那红肿如桃的双眼更让我不忍正视。我和肖玉还有李安森弟媳妇一起,好说歹说安抚了好一阵,她才坐下来,慢慢恢复了平静。我这才注意到门边乱七八糟堆着的礼品袋,身上不由得一阵燥热。待听完事情原委,却又恍若看到眼前洞开了一条无底的黑隙,李安森正在飞速坠向深处。
按照李安森老婆的说法,李安森是遭了镇上书记的暗算。说是镇上新开发的岚湖渡假村项目,书记拍板收了开发商一笔钱。正副书记加李安森三个,一人揣了8万“辛苦费”。不料后来书记竟又暗地里把自己那份“主动”上交到县纪委,却不跟李安森他们打招呼。这一来他成了有觉悟的好干部,李安森和副书记直到县纪委立案谈话才认了帐,明显涉嫌受贿,当即被宣布双规接受进一步审查。如果没有强有力的关系,被移送检察院的话,没个十年八年是出不来了……
我对李安森老婆这种说法表示怀疑:书记这么做,好像也太玄了点吧?会不会是有人举报了这事,他上头有背景先得了消息,所以就把钱交了……
那他为什么不给李镇长他们通个气?李安森弟媳也一口咬定就是这么回事:镇上人都知道,他跟李镇长脾味不对头,一向嫉恨李镇长比他名气响,功劳大。多少次想把他挤走都没成功,这回他是赌命下死套啦。
我仍然有点怀疑,但又觉得这事究竟如何已不重要,要命的是李安森这回恐怕是难逃劫运了。但我没把这意思说出来,只是安慰李安森老婆,叫她先别着急,我已经给他们市纪委四处的主任打了电话,他答应帮忙云云。
李安森老婆顿时两眼放光:这可太好啦!市纪委下来的人,就是四处的!
我傻了眼。感觉活像又挨了何定一一顿嘴巴——既然四处都派了人下来,何定一作为主任,分明早已对案情了如指掌。可他却对我说什么了解了解再说……
当然,我明白何定一这么做没有错。但我或者说李安森还能指望他什么呢?
李安森哪,我可是黔驴技穷了!你的命运如何,只能听从上帝安排了……
可是,好不容易把李安森老婆和弟媳妇送下楼,刚回到家里,肖玉神情怪异地塞过来一个鼓胀胀的大信封,说是她刚从李安森老婆带来的礼品袋中发现的。
我的天,里面竟是封得好好的一万块现金!
我扑到窗前想叫住她们,刚好看见她们的小车拐出小区大门。
我这才意识到,天已经黑透了。
原载《长江文艺》2005年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