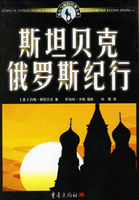如果说漆著的影响研究带有某种全面总结性的话,那么以某一具体问题为依托来阐述道家思想对古代文学理论的渗透或浸渍,则是有关道家思想对古代文学理论的影响的探讨活动中最为常见的一种话语方式。如:吕艺考察了《庄子》中对“情”字的使用和对“情”的特别关注,认为古代文论的“缘情说”,其发展轨迹并非只是循着儒家思想所作的单线运动,其初始源头可追溯到先秦道家中的庄子。吕艺:《庄子“缘情”思想发微》,《北京大学学报》,1987(5)。漆绪邦就道家思维对中国古代艺术思维论的影响作了深入的探讨,他认为,在文论史上第一个明确而充分地研究艺术思维问题的是陆机,其艺术思维论的思想根基正是道家的“玄览”“游心”之说,而刘勰的“神思”论亦远承老庄之学,近取陆机、宗炳之论,才发展成为完整的艺术思维理论。漆绪邦:《从“玄览”“游心”到“神思”——道家思想与中国古代文学理论探讨之二》,《北京师范学院学报》,1985(3)。徐应佩分析了老庄哲学对古代文学鉴赏论的影响,认为这种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由言探意调动文学鉴赏的能动作用;在文学鉴赏的心理要求方面,提出了“虚静”“坐忘”的看法;将自然天籁看做是文学鉴赏的审美崇尚;有无相生的思想形成了文学鉴赏的辩证法。徐应佩:《道家哲学对文学鉴赏论的沾溉与浸润》,《名作欣赏》,1997(3)。杨铸认为道家贵自然的倾向促进了诗歌创作对自然素朴的艺术追求,道家贵“无”轻“有”的思想、“言不尽意”的思想、重神轻形的思想对古代诗歌理论中的“虚实”论、“言外之意”论、“神似”论等都有重要的影响。杨铸:《道家思想与中国古代诗歌理论》,《北京师院学报》,1990(4)。叶维廉在《中国诗学》中以“言无言:道家知识论”为题,就道家的语言观对中国古典“空白美学”的影响作了精辟的论述。他认为道家的知识论在语言的破解中建立一种“离合引生”的活动,“不但开向异乎寻常的朴实而诡奥的遮诠行为”,引至“显现即无,无即显现”的美学,而且还对“名”与“体制”之间的辩证关系作了深刻的反省,道家“言无言,未尝不言”的语言观对中国古典“空白的美学”的形成有着深刻的影响。叶维廉:《中国诗学》,57—60页,北京:三联书店,1992。董国尧认为庄子的自然美思想对古代诗歌艺术创作中冲淡自然的“出水芙蓉”的审美情趣的形成,对于反对雕琢、造作的风气都产生了相当的影响,谢灵运、陶渊明、王维、李白的诗,曹雪芹的小说等都受了庄子自然美思想的陶冶。董国尧:《庄子论自然美》,《学习与探索》,1981(4)。李壮鹰剖析了道家的艺术本体论,认为儒家注重艺术与社会的联系和社会功用,注重艺术的外部规律,而道家多注重艺术自身的特性和内部思维规律。道家对后世文艺理论影响最为深远的就是“艺术本体论”,从其中引出的鉴赏论在理论上有相当的价值,诸如“象外”说、“滋味”说、“兴趣”说、“意境”说、“神韵”说均受其溉泽。李壮鹰:《道家的艺术本体论剖析》,《学术月刊》,1984(2)。类似的专文还有刘则鸣的《试论老子的“大音希声”及其对中国文艺思想的影响》、王乙的《老子“言”“辩”之美及其对后世文论的影响》等。刘文载《内蒙古大学学报》,1989(2);王文载《四川师范大学学报》,1986(4)。
三、玄学与古代文学理论
魏晋南北朝是中国文学的自觉时期,也是中国古代文学理论空前大发展的时期。这一时期产生了《文赋》《文心雕龙》《诗品》等重要的文学理论著作或专文,这其中,玄学极盛于魏晋,扬波于南朝,是整个魏晋南北朝的统治思想,对文学创作与文学理论总结产生了十分深远的影响。玄学的“才性之辩”“善意之辩”“有无之辩”“形神之辩”等思辨活动为魏晋南北朝文学理论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哲学基础,提供了方法论武器,也帮助文学理论家增强了理论思维的能力。可惜在20世纪上半叶,有关玄学与文学理论之间的关系的专论甚少,陈钟凡、郭绍虞、罗根泽等人的批评史著作也多是语焉不详。新时期以前的近二十篇研究魏晋南北朝文学理论的概述性专文也多是将其作为一种时代背景一笔带过。这一研究状况直到新时期开始才得到改观。如:敏泽的《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在讨论魏晋南北朝文学理论中所产生的新概念如风韵、形神、言意等时,就将玄学作为一种背景理论来加以分析。成复旺等人的《中国文学理论史》在讨论魏晋南北朝文学理论时,单列“玄学的盛行和理论思维的发展”一节来分析玄学对当时文学理论思维的影响。张少康《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发展史》第六章和第七章则分别以“魏晋玄学与文学理论批评的新发展”和“玄佛合流与南朝文学理论批评的繁荣”为题,分析玄学兴起与文学观念变迁之间的内在关系,对玄学对文论的影响给予了极大的重视。与此同时,一些有关玄学与古代文论之间关系的专论的出现也显示了学者们对此一领域的重视,这其中,讨论较多的三个问题是:
(一)关于玄学本体论(或宇宙论)同古代文论之间的关系
如:陈顺智认为《文心雕龙》的内在理论构架与玄学本体论之间有着内在的关系,表现在:1.刘勰论道,先从宇宙之道论及人道,再论及文道,实是由本及末、由无及有、由远及近、由里及表的逻辑推演;2.由道而圣人而五经的文章模式,进一步推演,便有刘勰各种文体论均源于经典的文体论思想;3.玄学本体论思想还一以贯之地表现在《文心雕龙》的创作论中;4.圣人体道立意、立象尽意、立言尽象的逻辑序列乃是就圣人阐释精微深奥的神道而言,作者表现情志也同此逻辑序列。陈顺智:《玄学本体论与〈文心雕龙〉》,《武汉大学学报》,1990(5)。张连第等人认为玄学对魏晋南北朝文学理论的影响主要体现在本末有无之辩、才性之辩以及善意之辩对文学的本源、本质论、作家论和创作论的影响,其中最为根本的是本末有无之辩对文学本源、本质论的影响,它有力地促进了当时文学观念的转化。张连第、吴相道:《玄学本末、有无之辩对文学本源、本质论的影响》,《社会科学战线》,1995(2)。张海明分析了玄学本体论的重要意义及其对文学理论的影响,认为它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对事物之本体与现象的区分,促使了理论研究去追问事物存在的最终依据,而不止于现象层面的探讨;二是玄学本体论的真正着眼点在于人格本体论,而对于人格本体论的关注则不可避免地导向人性自然说,个体之情感、个性由此得到突出。张海明:《玄学本体论与魏晋六朝诗学》,《文学评论》,1997(2)。孔繁则认为玄学宇宙论中的“以无为本”“知本”“自然为正”“独化”“崇本息末”等思想对中国古代文学理论具有深远的影响,这些思想促使魏晋以后的文论特别注意探讨文学的本质,揭示文和道的关系,把握文学发展的规律等。孔繁:《魏晋玄学和文学理论》,《晋阳学刊》,1987(1)。
(二)关于“言意之辩”的讨论
汤用彤早年曾作《善意之辩》一文对玄学的理论基础作了哲学分析,认为“善意之辩”是玄学体系的基础,其源实起于汉魏间评论人物的名理之学,汤用彤:《魏晋玄学论稿》,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后又在《魏晋玄学和文学理论》一文中将其哲学分析引入文学理论研究中,强调“魏晋南北朝文学理论之重要问题以‘得意忘言’为基础”。汤用彤:《汤用彤全集》(第四卷),393页,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0。新时期以来,从哲学上的“善意之辩”入手来探索文学理论中的语言与思想之间的关系问题的文章不在少数,如袁行霈和刘文英都探讨了“善意之辩”对古代文艺理论的影响,前者考察了“善意之辩”对中国古代诗歌、绘画、戏曲、音乐等创作理论的影响;后者则探讨了魏晋玄学中“言不尽意”论对古代文论中“余意不尽”说的影响。袁行霈:《魏晋玄学中的的善意之辩与中国古代文艺理论》,《古代文学理论研究》第1辑;刘文英:《关于魏晋的“善意之辩”和文学理论》,《学术月刊》,1982(8)。邓乔彬探讨了庄、玄、禅对古代诗歌创作及理论的影响,清理了老庄、《易经》、玄学在“言意之辩”思想形成与发展过程中的作用,特别就从陆机到刘勰的理论嬗变中“象”论的展开作了分析,同时还对白皎然、刘禹锡、司空图到宋代严羽一脉相承的诗歌“境界”理论所受的禅宗影响作了梳理。邓乔彬:《从言意之辩到境生象外》,《华东师范大学学报》,1989(1)。王钟陵认为,“言意之辩”不仅仅是一种语言上的论争,应当将之放在哲学高度、民族思想发展历程和民族思维能力的提升过程中来加以认识,刘勰的“隐秀”论是哲学理论与文学理论的一种合璧,是“言不尽意”论、“得意忘言”论、“言尽意”论的深刻的合题。王钟陵:《哲学上的“言意之辩”与文学上的“隐秀”论》,《古代文学理论研究丛刊》第14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又如,刘琦等人对善意之辩与魏晋南北朝文学思维理论的发展之间的关系作了细致的阐发,认为“善意之辩”作为一种哲学论题对文学创作思维特征的研究产生了至关重要的影响,它不仅是理论储备,更重要的是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如果说陆机只是提出了文学创作思维过程中的言意矛盾,那么刘勰则已从文学创作的思维方式和特征,从理论的不同层次上给予了有力的解答。而到了钟嵘,哲学言意论的痕迹已经消失,它已作为纯审美观念融汇在整个理论探讨中,在创作、鉴赏甚至整个审美过程中都体现出其影响。载《文艺研究》,1992(4)。
(三)玄学与《文心雕龙》的关系
学者们大多认为玄学对《文心雕龙》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但探讨的出发点或立论的角度则各有不同。如:吴观澜从“善意之辩”入手加以考察,认为刘勰基本完成了“善意之辩”从玄学向美学的转化,吸取了玄学“言不尽意”论和“得意忘言”论的概念和精神,探讨了艺术中言意之间的矛盾,这在文学批评史和美学史上都有巨大的意义。吴观澜:《一个从玄学向美学转化的论题——论“善意之辩”对〈文心雕龙〉的影响》,《学术研究》,1987(1)。陈书良从玄学的“清谈”入手,认为《文心》的主要形成基础就是清谈,《文心》中无论是资料的掌握、理论的阐发、作品的分析、作家的评价都从清谈中吸取了极为丰富的养分。陈书良:《清谈与〈文心雕龙〉》,《求索》,1986(3)。金大章则从王弼玄学本体论中的有生于无、文原于道的观点入手进行考察,认为刘勰是借助玄学理论将作为本体的“道”与儒家经典巧妙地结合起来,使《文心》成为以道家为体、以儒家为用的理论体系的,而且,刘勰用玄学本体论中的“执一御也”的思想,有条不紊地安排了《文心》的内容,组织了《文心》的结构。金大章:《王弼玄学本体论对〈文心雕龙〉的影响》,《学术月刊》,1988(6)。这类文章还有严寿徵的《道家、玄学与〈文心雕龙〉》、蔡仲翔等的《〈文心雕龙〉与魏晋玄学》、姚汉荣的《〈文心雕龙〉与魏晋玄学》等。严文载《重庆师范学院学报》,1983(3);蔡文载《文心雕龙学刊》第3辑,姚文载《中州学刊》,1986(2)。
此外,也有一些其他角度的研究。如:张少康剖析了“声无哀乐论”与玄学的密切联系,认为嵇康的“声无哀乐论”在对声、心关系的认识上,和玄学家对言与象、象与意关系的认识是一致的,而且嵇康论述声音与哀乐的关系,实际上也体现了玄学本体论视道与物、无与有为体用关系的观念。张少康:《玄学文艺思想与嵇康的〈声无哀乐论〉》,载《文艺学的民族传统》,张少康著,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张海明对魏晋玄学价值论同古代诗学之间的内在关系作了分析,认为魏晋玄学对这一时期的诗学产生了多方面的影响,价值论的影响即为其中之一。由玄学“以无为本”的价值取向所决定,魏晋六朝诗学在审美取向上相应的表现为:重神贵虚、自然清丽和以怨为美。张海明:《玄学价值论与诗学》,《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97(2)。黄应全剖析了“清谈”在玄学与文论之间的重要中介作用,认为从汉末“清议”发展而来的魏晋南北朝“清谈”作为士族名士们的主要社交方式,促使了“言”与“笔”的分化,促使了文学批评之风的盛行和批评标准中玄学色彩的加深,也促使了《老》《庄》及玄学成为文论家的基本修养,从而成为玄学影响文论的媒介。黄应全:《玄学影响文论的桥梁——清谈》,《文艺研究》,1997(4)。杨乃乔则借鉴现代阐释学对汉魏之际儒家诗学之整体意义让位及其从文化中心全面退却的困境作了全面的分析。他认为玄学大师从道德观、圣人观、本体观三个方面对儒家经典文本进行了破坏性误读,其实质就是儒家经典文本的原初视阈与玄学大师启动阐释的当下视阈——道家语境的融合,并逼使儒家诗学让位于道家诗学,而这实质彰显了汉魏转型时期文化景观上的文学批评权力话语的争夺现象。杨乃乔:《批评的中心指涉结构与阐释的破坏性误读——论经学的玄学化与中国古典诗学走向自觉的阐释学景观》,《天津社会科学》,1997(2)。
值得一提的还有孔繁的《魏晋玄学和文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该著重在剖析与明辨玄学与文学的关系,诸如:玄学重视精神、天才、个性、情性,及其对文学创作和文学风格的影响;玄学对个性的尊重,及其对繁荣文学创作的意义;玄学宇宙观和方法观对文学创作、文学理论以及音乐美术思想的影响;玄学对于诗歌创作的影响;玄学如何通过艺术境界使人领悟言外之意、象外之旨;等等,该著都作了较为全面的清理,对认识魏晋玄学和文学理论之间的关系也很有帮助。此外,罗宗强的《玄学与魏晋士人心态》、陈顺智的《魏晋玄学与六朝文学》、卢盛江的《魏晋玄学与文学思想》等著,从不同的角度论述了魏晋玄学同当时的文学思想之间的关系及其对后世文学思想的影响,也值得研究者注意。
毫无疑问,20世纪古代文学理论研究中的这种文化本源上的探究是十分有益于古代文学理论研究的深化与拓展的。这主要表现在:这些探究活动把文学理论文本(或表意实践)看成是一个开放性的文本,一种包含着复杂的社会文化、历史象征系统的符号体系,把文学批评从纯文学的解读与阐释中解放出来,打破了过去封闭的学科界限。相对于以往的文学批评研究,这种文化本源上的探讨使古代文论研究的视界出现了一些显而易见的转移。较之以往的文论研究时常围绕着文学理论史上的经典作反复的文本细读甚至文本考辨,它不仅仅扩大了研究者关注的范围,或放大了研究者理论考察的半径,更重要的是它提示古代文论研究者要注意去重建文学—文化的公共场域并使之进入合理的对话交往语境,学会关注和寻找文学与文化之间的“间”性,因此,它的意义更在于方法论的启示和研究视阈的展拓上,而这正是古代文学理论研究最为需要的。在笔者看来,20世纪道家文艺思想研究中这种文化探源方面的努力,也是最值得学者注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