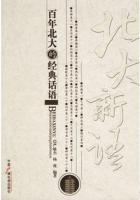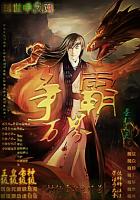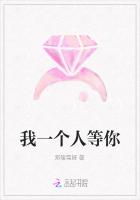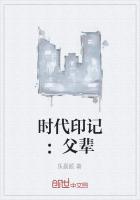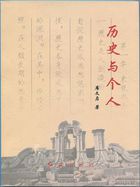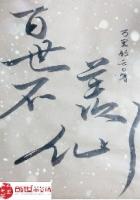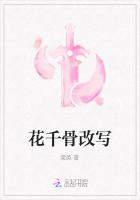中国古典美学史研究在20世纪经过几代学人的辛勤耕耘和劳作,通过研究论域的不断拓展,研究视野的不断开阔,以及方法和学术理念的不断变革、调整,逐渐走向成熟和完善,为后学者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但研究中也呈现出一些理论困境,本文拟就内在于中国美学史研究之历史与现实的真问题做一些初步的探讨,并就其解决方式提出初步的设想。
这些内在于中国美学史研究之历史与现实的真问题大多是以理论困惑的形式表现出来的,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研究对象的困惑
研究对象的确立是一门学科形成的重要基础,对象的游移不定最易造成学科体系严密性的缺失或各种论争的出现。就目前中国美学史研究的现状看,引起各种论争、美学史研究方法各异以及美学史书写风貌迥然有别的主要原因,正在于学界对中国美学史研究对象的困惑上。国内目前关于美学史研究对象问题的看法主要有以下几种:
(一)中国美学史即中国审美意识史
这种看法认为,美学史的研究对象是审美意识史,而不应该仅仅是美学思想史、美学理论史。审美意识有感性形态和理性形态两种表现形态。前者是指体现于人类创造的一切感性产品中的审美意识,包括物质产品和艺术产品,其中又以文艺作品最为集中、最为典型。在后者中,人类的审美意识则是直接以概念、范畴及范畴体系的理论形态出现的,它是感性形态审美意识的总结、概括和理论升华。这两种形态相互关联,相互补充,却不能相互代替。完整的美学史,应是以理性思想与感性的创造相互对照,相互补充,才能完整地反映审美意识发生、发展的历史运动。持这种看法的学者认识到,以往的中国美学史著作的写作大多局限于美学思想史、美学理论史的范围或者审美意识的理性形态方面,对于丰富多彩的美学感性形态不太注意,因而还不是完整的美学史,并由此提出了重写中国美学史的设想。这种看法就其学理而言,可能在相当程度上参照或借鉴了鲍桑葵的《美学史》。鲍桑葵的《美学史》旨在着重叙述各个时期的审美意识的特征以及这些审美特征赖以形成的历史基础和条件。他认为,用思辨理论的方法研究美学史是不恰当的,要研究美学史必须了解这种植根于各时代生活的审美意识的发展。鲍桑葵在《美学史》中说:“我的任务是写作一部美学的历史,而不是一部美学家的历史。”他想“尽可能写出一部审美意识的历史来”,并明确地指出:“美的艺术史是作为具体现象的实际的审美意识的历史。美学理论是对这一意识(指审美意识)的哲学分析,而要对这一意识做哲学分析,一个重要条件就是要了解这一意识的历史。美学理论的历史,则要探讨审美意识在学术上的表现——美学理论——的历史,但是它从来也没有忘记,需要阐述的中心问题乃是美对于人类生活的价值。”[英]鲍桑葵:《美学史》,张今译,6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从学理上看,国内持鲍桑葵这种主张的学者的理论基点主要体现在对审美意识表现形态的多样性的坚持上,用以证明其理论主张正确性的例证则是温克尔曼的《古代艺术史》、黑格尔的《美学》以及李泽厚的《美的历程》等从审美意识入手,并兼顾感性和理性两种表现形态,以此来探讨美学的历史发展的较为著名或成功的美学史著作。
(二)中国美学史即中国审美理论史
如有学者认为:“中国美学史,指的是从远古到清代的审美理论史。”张法:《中国美学史五题》,《东方丛刊》,2001(1)。实际上持这种看法的人明显表现出以美的形而上学的理论为美学史研究核心的倾向,其西学渊源也表现得极为明显。例如,美国的吉尔伯特、德国的库恩在其合著的《美学史》开端就曾说:“美学与其说产生于任何纯粹的悟性活动中,不如说产生于争辩的过程中。”[美]凯·埃·吉尔伯特、[德]赫·库恩:《美学史》(上卷),夏乾丰译,9页,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鲍桑葵的《美学史》和意大利的克罗齐的《作为表现的科学和一般语言学的美学的历史》也都是以西方美学中的论辩性言论作为美学史研究的重点,把美学思想史理解为哲学思想诞生时起渗透于其中的关于艺术和美的性质的考察,以及后来发展成为美的形而上学的理论的历史。这些论著之前的一些西方美学史也大多表现出这样的特点。例如,科莱尔在其《美学史草稿》(雷根斯堡,1799)前言中就说他的《草稿》只涉及一般理论,目的是给在德国大学里学习鉴赏力批判的美的艺术的理论的青年人提出“美学的产生与发展的一份明晰的纲要”。齐默尔曼的《作为哲学科学的美学史》(维也纳,1858)第一卷叙述的是“从希腊人到通过鲍姆嘉通的著作而形成的哲学美学”,第二卷叙述的是“从鲍姆嘉通到美学的变革——康德的《判断力批判》”,第三卷论述“从康德到唯心主义的美学”,第四卷论述“从唯心主义的美学到1798—1858年的美学”,总的来看,也是以形而上学的美学理论为主要研究对象。在卡斯莱尔的《美学批判史》(柏林,1872)中,作者称其历史只是理论的准备,是“为构成一个新体系的最高原理”。梅嫩德斯-佩拉约的《西班牙美学思想史》(马德里,1890—1891)主要论述的则是美的形而上学、关于上帝和爱的神秘主义的思辨、散见于哲学家关于艺术的理论和所有有关美学的理论(如诗学、修辞学、绘画、建筑)等。[意]克罗齐:《作为表现的科学和一般语言学的美学的历史》,“附编”中的“一般参看书目”,王天清译,袁华清校,309—313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苏联美学家B.П.金斯塔科夫在其《美学史纲》序言中更说:“美学学说史是美学极为重要的篇章。”他引述苏联哲学家阿斯穆斯的话说:“美学史的研究只有在这样的条件下才富有成效:以往历史上所产生的和出现的理论能够成为讨论当代美学问题和当代各种美学思想斗争的催化剂。”[苏]B.П.金斯塔科夫:《美学史纲》,“序言”,樊莘森等译,1页,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6。这种研究理念甚至还出现在国人所写的西方美学史著作中,如朱光潜在《西方美学史》一书中就说:“严格地讲,本编只是一部略见美学思想发展的论文集或读书笔记,不配叫做《西方美学史》。任何一部比较完备的思想史都只有在一些分期专题论文的基础上才写得出来……编者只能介绍一些主要流派中主要代表的主要论点。”朱光潜:《西方美学史》上卷,“序论”,2—3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
(三)中国美学史即中国美学范畴史
例如,国内学界就有人认为:“从根本上讲,中国美学和文学理论史研究,应该而且必须抓住范畴的发展、演进这个核心环节。”潘知常:《关于中国美学史的研究方法问题》,《学术月刊》,1984(7)。实际上,这种看法也有其西学渊源。波兰美学家W.塔达基维奇在其《西方美学概念史》中就认为,美学史的研究不能局限于一些孤立的美学原则的推演,也不能局限在个别的、有突出成就的美学理论的逻辑模式中。历史学家不仅要考察那些涉及或谈论到美与艺术的历史文献,而且还要注意人类审美活动的具体实践以及以这一实践为背景的特殊的审美观念,也就是要把美学史放在一个更广泛的文化背景下来研究。因此,他选择了一种特殊的研究方法,以概念或范畴为线索来进行美学史研究。国内以这种学术理念进行美学史书写比较成功的是叶朗先生的《中国美学史大纲》,《大纲》试图创立一种既能展示中国美学发展线索和规律,又能全面体现中国美学特点,把握住每个时代的主要美学范畴和美学命题的体例,因而并不拘泥于面面俱到地介绍每一位美学家的全部美学观点,而是抓住他在中国美学史上有贡献、有创新的美学命题以及每个时代提出的新的美学概念、美学范畴加以分析,以期有助于在总体上把握住中国美学的特点。还有学者从审美意识史书写中理论形态和感性形态走向结合显然过于理想化这一隐忧出发,提出在目前的状况下,首先应该抓住中国美学的基本方面、主导方面,即抓住它的主潮,搞清其基本性质、特点和发展的主要线索,是较为切实可行的办法,而这一主潮则主要体现在各时代美学的总范畴和审美理想上,即体现在关于美和艺术(广义的艺术美)的理想上,因此应该抓住各时代美学的总范畴和主导理想。周来祥:《〈中国美学主潮〉序》,《博览群书》,1989(8,9)。
(四)中国美学史即中国的感性经验史
持这种看法的学者显然依据的是鲍姆嘉通最初对美学这一学科的基本界定,即美学是“研究感性认识的科学”,美学等于“感性学”。鲍姆嘉通的这种研究主张在西方的美学史书写中也有直接的承接者,李斯托威尔的《近代美学史评述》正是这样一部美学史。作者将这段时间的美学流派分成主观的和客观的两大部分,共介绍了十四个流派。在他看来,美学“是关于人类各个方面,各种以及各个领域中的美感经验的科学和哲学”。[英]李斯托威尔:《近代美学史评述》,朱光潜译,235页,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0。在国内学者看来,如果把中国美学史的任务规定为研究中国人的感性经验,而事实上中国哲学史家们对此领域又尚未给予更多的关注,那么它将向当代美学研究者展示一个相当开阔的学术前景。
(五)中国美学史就是中国审美活动史
例如洪毅然认为,美学史应该是美学这门“科学”的历史,即人类对于客观事物的美和主观审美活动诸规律不断深化其认识之整个进程的历史。其中自然包括作为审美主体的人之审美意识的发展史在内。因此,美学史的对象和范围是十分广泛的:1.人和物的审美关系的发展演变进程;2.人对物的美及丑的认识的深化、广化的进程;3.在此基础上逐步形成起来的各历史时期人的审美意识的发展演变的客观历史规律。其中包括自然美、社会生活美和艺术美三方面。马鸿增:《中国美学史学术讨论会纪要》,《美学》,1984(8)。细究之下,亦可发现,这种研究理念的基础来自于马克思主义实践论,即依据人类实践领域的不同来划分美所存在的领域并以此展开美学史研究。
(六)中国美学史就是中国艺术本质的思想史
例如,易中天在《中国美学史的内在逻辑与历史环节》一文中就认为,“在严格的意义上,美学史只能是人类对自己的艺术和审美活动进行理性规范,即不断探索、研究和界定美和艺术本质的思想史。”易中天:《中国美学史的内在逻辑与历史环节》,《武汉大学学报》,1990(1)。他将中国美学史分为三个时期:1.封建前期艺术社会学;2.封建中期艺术哲学;3.封建后期艺术心理学。这种研究理念很显然来自于黑格尔的《美学》,在《美学》中黑格尔曾明确地将美学定义为“艺术哲学”或“美的艺术的哲学”。
研究对象的游移不定直接导致了研究方法的各异。林同华先生曾将目前研究中国美学史的方法归纳为四种:文艺思想与哲学思想渗透法;审美范畴、审美命题系列法;审美文化起源法与文艺思潮衔接法;审美文化与审美思想印证法。林同华:《关于中国美学史研究的对象与方法问题》,《学术月刊》,1995(2)。这在一定程度上也说明研究方法的花样翻新很大程度上就是由于研究对象的不确定。我以为在这一困惑上,不妨尝试一种现象即本体的思考向度(即不妨将各种美学形态视为“现象”,将各种美学思想视为一种对现象的“本体”性思考),这种思考向度其实十分适合中国古典美学的本有特征,现象即本体这种不离不弃的关系可以使研究者更妥帖地处理美学思想与美学形态之间的辩证关系,从而释放出更大的解释学空间(吴功正先生通过对中国美学史研究状况的分析和把握,以及自身几部断代美学史著研究撰写的经验概括,特别指出当前最需要克服的是把中国美学史写成美学理论史即美学理论的历史的偏向,应当将美学思想和审美形态的结合作为中国美学史研究的基点,这种看法实际上已经极其敏锐地察觉到了中国美学史研究中现象与本体相脱离的痼疾。吴功正:《建构中国美学史的学科体系》,《南通师范学院学报》,2004(3)。
二、主体视界的内在困境
从上述有关中国美学史研究对象的论争来看,中国美学史学科的建立在相当程度上都是以西方学术为最高标准的,由此又引发了以西方学术为标尺的中国美学史研究理念和书写方式在主体视界方面的内在困境。它主要表现在中国美学史书写主体始终处于“历史的眼光”与“现在的眼光”的相互纠结中。“历史的眼光”作为美学史研究的学术本位,是显在的一种学术姿态,它是对传统美学历史的清理与爬梳,主要是借“辨章学术、考镜源流”来获得美学史的学术方向感,而“现在的眼光”则是通过一种新的整理意识和新的知识背景(主要是西学)来重写或重认“过去”,进行“价值重估”,它主要在于通过放眼于现代世界和西方美学资源,或者通过某种“现代”的接轨,来实现民族美学的某种复活(或激活)。这种纠结导致了以下三种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