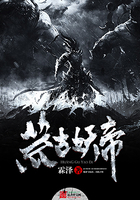有一个来自天国的人,因为吃了地上的谷物而丧失了飞行能力,最后,又因为这种能力的丧失而失掉了他的天国。这是个在我的家乡流传很广的故事,几乎到了妇孺皆知的地步,我很小的时候就听我母亲讲起过。需要说明的是,这个故事在我家乡流传时已经有两种不同的版本,因为——我这么一说你就明白了,我们这儿有许多的佛教徒和基督教徒,具体有多少或者各占多少比例无法弄清楚。那是个信仰十分混杂的地区,往往一个镇上左边还是翘脊的庙宇,右边就成了带尖顶的穹窿,教徒们也分区而居,相互间井水不犯河水。令人惊异的应该是这个故事在两种信仰中都有教徒信奉,因为故事中形容的天国景象据说都与他们各自的教义相符,所以最终都成为天国(堂)真实不虚的一项有力的证据,这反过来对坚定他们各自的信仰也十分有好处。不同的是,故事在不同的区域内流传时都作了相应的变动,左边的说法是谷物能让仙人失去御风而行的能力,右边则说谷物能够损伤天使翅膀里的神经。你已经看到了,尽管两种解释各不相同,但传播者对故事的内容都持一种深信不疑的态度,而且,他们都不约而同地把谷物当成了尘世对天国(堂)最大的威胁。
那个自称就是失去了翅膀的天使(仙人)是近期才出现的,这多少有些蹊跷,我是说,这么多年过去了,似乎还没有哪个信徒或者传播者对故事中的原型,也就是那个失去天国的“天使”的下落深究过,也就是说,以前它在人们心目中还只是一则民间故事,“天使”的出现才陡然使它变得“真实”。这或许也是该故事到目前为止最具诱惑的地方了,天国(天堂)凭借着一个落魄“天使”的存在而变得触手可及。相反,如果“天使”的出现仅仅是一个谎言,那么那个流传甚久的天国也仅仅多了一则反例,对天国的“神圣”却无伤大雅,因此可以说当那个落魄的“天使”把我们引进了这个故事的腹地时,我就感觉到我们所处的位置并不像我希望的那么有利。
我就是那个受命前去调查整个事件原委的医生林克,现在我们正走在寻找“天使”的路上,和我结伴同行的还有来自省城的宣传干事小杨。一个星期前我和小杨被临时抽调到一起组成了一个临时调查小组,我们调查小组的名称是“‘天使’问题调查小组”,简称“天问小组”,代号TW,因为对该地区的熟悉我被任命为TW调查小组组长。
由于我们此行的责任仅仅是调查,所以我和小杨都必须选择一个临时身份,目的也是让我们的调查活动能够在不惊扰“天使”的情形下顺利进行。我的身份是一个游方郎中,专治“疑难杂症”,偶尔客串下兽医,这也是在我们那一带行走的江湖郎中必须兼备的素质。选择这个身份是因为十几年前我曾在老家行过几天医,诊治一些头痛脑热的小毛病应当不在话下,所以临行前我又从我父亲那儿把我当年做赤脚医生时用过的一个破医药箱找了出来。我母亲生前有收集旧物的习惯,破医药箱就藏在我们家一个阁楼里,和一个坏蒸笼,一把烂锄头,一只竹制的婴儿摇床放在一起,它的附近还有几个干瘪发芽的洋芋。我把药箱收拾出来,在里面放了一些常用药物,自然少不了给猪牛做阉割用的小弯刀,灌药用的细牛角。我还从箱子底找到了一件很久没有穿过的中山装,细细地一化妆几乎就回复到我十年前的模样。可能城市生活对我多少有些影响,我的皮肤变得细腻了,不过也难说,游方郎中尽管生活漂泊不定,但骨子里到底是一件手艺活,和种田卖气力的有些区别也十分自然。离家前我在镜子前最后一瞥,我让自己相信这就是我在农村干了十几年游方郎中的样子。
与我不同的是,和我同行的小杨却一直没能确定身份。他是与我不同的又一代,以他的年纪和大城市生活背景,在农村找一个对应而通行无阻的角色还相当地困难。小杨在大学学哲学,同时也爱好文艺,最后还是他自己的主意,扮成一个下乡写生的大学生,尽管免不了引人注目,但总算是与他的气质符合了,因此也还说得过去。我们俩先后坐车到了青田县的首府青田镇,为了避人耳目,尽管我们住在同一家旅店,也假装互不相识。
青田镇是我们寻找“天使”的第一站,也是二十年前我完成小学学业的地方。在所有与“天使”有关的消息来源中,青田镇是最微小的地名了,但当我们抵达时等待我们的仍然是一些说法含混的传闻,因此我们认定“天使”并不在这个范围之内。那些传闻与我们来之前听到的有些不同,可能少了几层传递还没有达到离奇的地步,主要还是“天使”神奇的治病能力,据说他(她)摸过的一把沙土冲水服下即可让一个高位截瘫的患者行走如常,或者用羽毛在眼睛上抚过,即可令瞎子复明。镇上的旅店里已经有一些慕名远道而来的求医者,一个久治不愈的麻脸姑娘即是来求医访药的,她准备把“天使”用过的刷锅水带回去分四个疗程服用。
来之前我们TW调查小组就对事情的原委进行过分析,最直接的感觉当然是有人利用了那个传说,将民间故事里缺乏实证的部分加以发挥,并做了最大的歪曲而化虚为实,换句话,就是说我老家出了一个骗子。我只是不知道别人对民间故事的感受到了何种程度,但如果你能体会那些民问传说中的美感,也就不难理解这种亵渎、欺骗为什么会让我产生如此巨大的愤慨了,甚至我把骗子的出现当成了对我自身的伤害。这也是我在调查会议上的一点感想。不过,小杨可能就不一定愿意这样看了,他虽然是学哲学的,但我以为他身上的文艺细胞远比他的哲学细胞发育健全,否则他也不会用一种抒情的态度来看待整个“天使”事件。我倒不是说他一定就确信“天使”的存在,而是他那种凡事都觉得新鲜的心理,那种观光心理,让他一开始就从“天使”这两个字上找到了乐趣,他甚至认为“天使”是一位民俗专家,这一点也是他用一种很玩笑的口吻说出来的。我记得那个会议也就是从小杨的发言开始变成了一次毫无目的的闲聊。来的路上小杨几乎都在东张西望,听到一点消息就毫不犹豫地张大嘴巴。不过,归结到底他选择一个大学生的身份看来还是对路了,这是一个有自知之明的选择,你看他头上一缕黄头发,颤巍巍地随着他的表情上下抖动,如果让他扮一个乡下的代课教师或者大队会计,大概真的要误事,有谁会有他那种走马观花的眼睛,满不在乎的腔调,至少在青田镇里是找不到的。
那天晚上我和小杨分头在镇上四处转了转,寺庙、教堂是我们特别留意的地方,因为到了晚上,寺庙的山门已经合拢,倒是教堂里热闹非凡,唱洋经的人还真不少。人们坐在礼堂,手捧着一本教堂免费使用的烂了封皮的赞美诗,跟着一架木风琴正在唱歌。我看到小杨抱着一只画夹坐在门边一张条凳上给人画速写,他身边渐渐围了不少人,不过一旦他想问点什么,那些围观的人就讪笑着飞快地躲开了。这也是很正常的,在那些人心目中小杨并不是这个镇上的一员,他还无法被他们认同。有一个小女孩,一直站在离小杨两三米的地方,小杨过去拉住她的手,不知小杨还对她做了什么,小女孩忽然哇的一声就哭开了。结果弄得不少人围在他们周围,一些挑着担子或推着自行车的人也挤在里面,远远地看就像一个才发生的交通事故现场。这自然比看速写更有意思,我看到街口一些散步的行人也开始朝这边跑过来。但事后小杨却说,没什么啊,我只是问可不可以去她家吃饭?我怎么劝她都不听我的。这件事怎么收的场我就不知道了,后来我找到了我小学时的一个同学,他现在是镇卫星电视收转站的副站长,国家干部,对他我没什么可隐瞒的,我直陈了来意,出乎我意料的是我的老同学竟然不知道他们这儿出了个“天使”,但随即我也就明白了,我的同学和我一样都是无神论者,对于一个“天使”一类的传闻当然不会太留意的。他的反问更有意思,有吗,天使?他一脸的怀疑很有说服力。每种信息都有它自己的流通渠道,这就像红头文件,必须是有一定级别的人才能够看到。由此我也得出一个结论,“天使”事件对当地的生活秩序还没有产生太大的负面影响,主要还是一些迷信“天使”治病的外乡人,由于他们的急不可耐,成了“天使”最好的传播者,不过,最终他们还将成为“天使”最大的受害人,对此我已经深信不疑。后来,还是我在那个住店的麻脸姑娘身上花了些工夫,我得到的消息是“天使”正在大龙村一带活动。
第二天我和小杨去青木垅找我的二叔。我们没有直接去大龙村,一是青木垅与大龙村紧挨着,二是我们还有一些事情需要预先打探清楚。一清早我就和小杨上路了,因为路远,我们必须搭乘沿途顺路的车辆,我们拦住一辆拉砖瓦的骡车。起初我想继续最初的设想,和小杨假装萍水相逢,在路边先后上车。但我们上的那辆骡车的主人,一位老汉一眼就认定我们是一起的,小杨还想解释,我却知道乡下人的固执,一旦认准的事就很难得动摇,这时候无论说什么都只会越抹越黑,最好的办法就是敷衍过去,所以我对小杨使了个眼色,示意他不要再做解释。老汉挥了挥鞭子让他的骡车重新上路,这时候他故作精明地看着我问,你是走亲戚?我点点头,接着报了我二叔的名字。老汉点点头,表示知道的。那他呢——老汉话锋一转,又回到小杨身上,我说他写生——画画!我比了个动作。你儿子啊?像,像!老汉不知是不是装傻,看看我,再扭头看看小杨。我看见小杨这时候气得脸都变了形,辩也不是,不辩也不是,干脆扭头朝车后的泥坑吐口水。这个误会也让我在心里乐了半天,可脸上还得绷着,我原以为我们的伪装是天衣无缝的,也不知什么地方就露出了破绽,大概我和小杨的组合原本就是一个失误吧,所幸的是变成父子关系倒还把原先的破绽和失误掩盖掉了。其后近一个小时的颠簸中,我都陪着老汉一路神聊,这一带的风情习俗我还记得一些,与老汉的应答也算有来言去语。小杨毕竟是年轻人,又是第一次下乡,闷了一会儿,那股不高兴很快地就过去了,他感兴趣的是几十年前的外国传教士,听赶车老汉说外国传教士当年骑着高头大马就在这条路上狂奔而过顿时精神来了。后来呢?后来,死了,打死了。打死了,谁打的?土匪嘛,那个洋和尚动了土匪的女人……
老人家,那您见过这个传教士没有?
洋和尚啊,见过,见过,高鼻子蓝眼睛,长得就跟现在电影上的美国人一模脱壳,对了,他还穿一件黑袍子,像个鬼一样,那时候我还小,见到他就绕起走,离他远远的。
他凶吗?
凶倒不凶,就是丑,过年还发糖给我们吃,吃完了就让我们背一些诗歌,还给我们一些画片……
上面是不是天使,长翅膀的那种?
对啊。
那你见过没有?小杨的兴趣可能会把我们此行的目的泄露出来,不过因为是坐在骡车上,我也没有阻止他把他的兴趣发展下去,他现在的身份是我的“儿子”,我不能做得太露骨。开玩笑,哪个人会长翅膀,你说的那是神话故事。
老汉的回答并没有让小杨失望,他还喋喋不休地加以分析,小杨说他读书时就知道这儿有庙宇和教堂并存了,落后地区总是便于教义流布,如果他是一名传教士,小杨说,他也会选择这样一个愚昧的地方作自己的教区。公正地说,小杨的兴趣还是合乎他的身份的,一个外面来的外乡人,很自然就应该对本地复杂的人文景观产生一些疑问,反而是我,因为从来就知道那些庙宇教堂以及牌坊仿佛天生就在那儿的,这是天经地义的事情,也就没有这么多需要解答的问题。这样一想我就释然了,不过,我还是抢过话题,和老汉聊起今年的收成情况,果然像我预料的,随着话题的转移,小杨就哑雀了,头歪向一边肩膀微微晃着开始打瞌睡,看来这不是他关心的东西。
我们在青木垅村头下了车,虽说是村头,离村子还有大概五里山路,这一段就全要靠脚走过去,小杨最初还有些兴致,指指这座山头像什么,那座山头又像什么,到后来便远远地落在我身后一大截,只能喘着粗气让我等一等,或者问我还有多远的路。我的回答也是农民的方式,我告诉他过了这个山头就可以望见了。
我大概有十来年没回过青木垅了,农村的变化与城市一比总显得微乎其微,包括青田镇,也不过添了几幢像样点的楼房,而青木垅更是十年前的样子,只是因为人口繁衍,才在四周加了几间土坯房,也难怪小杨说他是神父的话也会选这儿作教区。我们从一片刚收割完的稻田走过去,在村口遇到的第一个熟人是永亮,他是我小时候的玩伴,过河时曾经背过我。永亮正挑着一挑茶泡,看到我们时他的眼神是执著而茫然的,我还能依稀辨出他的模样,我说永亮不认识我了,我是细崽。这会儿永亮不再茫然了,他笑了一下说,永亮是我老者,你们找我老者?像,像,你和你老者简直一模脱壳,我忽然变得有些心不在焉,我不明白为什么这么小的一个失误竟会让我有一种受挫的感觉,这大概也就是那种所谓不祥的预感,总之我刚才的那股兴奋劲头一下子就没了,这一点同时也让我十分迷惑。我告诉永亮的孩子我并不找他父亲,我报了我二叔的名字。永亮的孩子一下子说,我知道你是谁了,我引你去。他尽管挑着茶泡,动作却十分灵敏,我当然知道二叔的住处,但他的好意我连拒绝的时间都没有。我对身后的小杨说,我二叔是本地有名的草医,很有声望的。小杨轻轻地噢了一声。
二叔家在村子的中部,门前院坝也晒着一地茶泡,房子看上去还是十几年前的样子,格局上没有太大变化,只是院里搭了一间偏房。我父亲这一辈原本有七个兄妹,其余的都已经过世了,只有二叔和我父亲还健在,他们都曾经跟我祖父学了一手好医术,二十年前,我父亲到城里谋生,在一家工厂里看仓库,才把原先的职业放弃了,可能这个原因,父亲和二叔很长一段时间都没有来往。我们到的时候二叔正在堂屋里切草药,听到永亮孩子的喊声他和我二婶一起迎到院门口。见面时自然有一番热闹的,二叔看上去精神还很好,下巴上留了一小撮山羊胡子,倒是二婶看上去比二叔老很多,二叔问我父亲好不好?我说好,他还让我代他向你问好。我和二叔握了手,递上两包在青田镇上买的糕点,谎称这是我父亲让我带给他的。事实上我来青木垅父亲并不知道,母亲去世后,他几乎每天都到街道办的一个茶室去打牌,连中饭都用饭盒装着去,对我的事情他从来不过问,当然更不用说青木垅了。我一直以为父亲放弃专业是个错误,现在这种感想更加强烈。我从药箱里取出一些药交给二叔,我说这是我送给叔叔的。这倒是实话,在农村看病一直不方便,更何况二叔还是一名医生,果然二叔拿着两包抗生素比得到糕点还要高兴。
青木垅因为不常有外人来,我们的到来的确惊动了不少人,邻居当然不用说,我的几个堂兄也放下手里的活跑来了,还有十几个侄子、侄女,最大的比我的年龄还要大,满腾腾地把我和小杨堵在二叔家的院子里。他们问我怎么不带老婆、崽女来搞——也就是玩?我把口袋里的烟拿出来散了,一包烟只剩下空壳。我说这一次主要是陪他,我指了指小杨,我说是陪他来青木垅写生,也就是来画画的,我说他是我老婆的弟弟,本来我想说他是我朋友的孩子,可能为了更可信些,我把他说成是我老婆的弟弟,这是我临时的主意。果然,大家的目光就被小杨吸引过去了,他真应该是被人注意的,有谁见过长黄头发的人,大家都很好奇地看着他的头发。
小杨却趁我认亲的当儿对我们老屋的门发生了兴趣,因为那扇门并不是堂堂正正地落在台阶上,小杨说,这门挺怪的,为什么扭着?我的一个侄子,也就是我二叔的一个孙子说,不清楚,这是老辈人弄的。另一个忙说,风水先生讲,要这个朝向开门才好。小杨对着门啧啧称奇,我的侄子又让他看对面的山,那山原来像一头狮子,后来炸山,才不像了。小杨看了看,他说还是有点像的。
我们在我二叔家吃的中饭,晚饭又移到我堂兄家,夜里再歇到我二叔家的阁楼上。到这个时候,还一切正常,我跟小杨说,这里离大龙村太近了,几乎就隔一座山头,说话稍不留心就可能走漏风声,所以我想我和小杨说话都还是非常小心的,至少我觉得后来发生的事不应该由我们来负责任,除非真有命中注定这么一说。临睡前我们在火塘前烤火,天好像突然间阴了下来,好像要下雨,我二婶说,已经有一百天没落雨了,你们是贵人,给我们带雨来了。贵人的说法让小杨很开心,我却没那么乐观,我在想这一下雨滑腻的山路怎么走?多少天没下雨可跟我没关系,这一下雨去大龙村就困难了,所以我心里最盼望的事情就是不要下雨。当时还有我的几个堂兄在火堆旁陪着我们,我们不过在聊一些小时候的事情。就在准备休息的时候小杨突然挑起个话题,他忽然问我二叔,你们这儿有鬼吗?我明白他的意思,他是想借鬼故事绕到天使身上,多少可以找到些线索。小杨说,我最喜欢听鬼故事了。我的一个堂妹说,有啊,怎么没有,我们村背后那棵大榕树下晚上总听见有人丢石子,又老看不见人。我的一个堂兄说,那地方以前吊死过人,我们晚上都不从那儿走。我看到这时候小杨把拳头支在下巴上,两个肩头耸着,缩成一团,好像非常害怕。接着我二叔也说了一个故事。这个故事说起来,也是我的亲身经历,这种阴沉沉的晚上说起来是有些怕人的。下面就是我二叔讲的故事:
那是快二十年前的事情了,有一次我去狮子山后一户老乡家急诊,急诊一般都是在半夜,因为想着有人帮一下忙,我就让他(二叔指了指我)跟我一起去了。那地方就是这位老乡一户人家,四周全是苞谷地,反正这种地方走夜路是很容易迷路的。生病的是老乡的独儿子,大概八九岁那么大,那天他忽然打摆子、发高烧,都开始抽筋了。我们是晚上半夜才到的,给他崽崽吃了点药,就在火塘边烤火——就是这种火塘,农村都是这种火塘。我坐在火塘的这一边,他呢(二叔又指了指我)靠在我腿上打瞌睡,火上还挂着一只沙罐正在熬药。我就听到一种声音,开始很小,听不清,后来连那位老乡都听到了,声音是——拿——不——来,拿——不——来——起初我以为是药罐子里的热气冲出来的声音。后来再一听,声音是从对面狮子山上传过来的,而且一直不停,越来越清楚。那位老乡再也坐不住了,冲到门口就开始和那个声音对骂,手里揪着一把柴刀就往身上砍、割,搞得浑身上下全是血,那地方又没别的人家,我也坐不住了,当天就带着细崽连夜赶了回来。
除了小杨外,我们都不止一次听二叔讲这个故事了,虽然我还是亲身经历,不过因为当时太小也没有太多的记忆,后来我回想,也幸亏当时懵懵懂懂的,什么都不知道。这时候我看见小杨正在抹眼角,大家都觉得怪,小杨说,没事,没事,我一听恐怖故事就会掉眼泪的,后来呢?二叔说,后来我去问了一下,这家崽崽还是没留住,半夜就落气了。小杨竟然会掉眼泪,临睡前我一直在想这件事,我不清楚小杨在他提出的这个问题上到底获得了什么有价值的东西,或者他原本就对这些神秘的事情感兴趣?小杨一直到很晚都在床上不停地翻身,他睡的床板又是竹篾编的,一动就吱吱乱响。后来,终于下雨了,我模模糊糊听到雨水在屋檐上嘀嘀嗒嗒滴落的声音。
第二天雨势很大,我想就是我们想走也走不成了。我对小杨说,在青木垅再待一天吧,这种天气爬山很够戗的。小杨同意了。他很快就找到了事做,因为他会画画,村里许多老人都请他去家里画像。而我呢,则被我的一群亲戚包围着,他们请我过去吃饭,又请我为他们的家庭问题出谋划策,比如我的几个侄儿,都想出去打工,可他们没出过远门,没经验也没经费。这种事我当然不能许诺什么。我含混其词,居然也让我混过去了。事后来看,我通过青木垅打探消息,小杨选择写生掩饰身份都是一种十分错误的尝试,因为这些都让我们更有理由留在青木垅了,我们都极想脱身,可同时又都身不由己。问题或许是我们无法脱身,还是有人不让我们脱身呢?可能要怪的话也只能怪我们自己最初做决定时欠考虑,至少我们给了别人机会。小杨回忆时说我的一个堂姐来找他画画时,他曾问过她是否知道天使,因为小杨怕鬼的笑话已经在青木垅传开了,大家都愿意用这个话题来寻开心。小杨说,但我没提大龙村,一个字都没提。是的,我们都没提,一个字都没提,但有什么用,这个问题大概已经不说自明了。我的堂姐回答小杨的是,有吧,天使最怕五谷杂粮,吃了就完了,翅膀就烧掉了。我没记错的话,我的堂姐第二次又来找我们谈这个问题,她为什么要找我们谈天使呢?她是否想从我们这儿探听一下我们此行的目的?我的态度自然是很明确的,我说这种东西是骗人的,谁见过人长翅膀,又见过哪个人会飞?堂姐还想说什么,她大概想反驳我,可能我多心吧,我看到我二叔这时候朝她努了一下嘴,把她的话题止住了。雨只下了一天就停了,第三天是个大晴天,我们却无法走,前面我说过,小杨要画像,而我有一帮亲戚要应付,那些堂兄弟,不去他们家吃饭还要生气,至少当时我和小杨都开始有一种疲于奔命的感觉,小杨的画越来越随意,越来越潦草,但收到画的人还是一样啧啧赞叹,我们是不是真的陷在一个溺水而沉的泥淖中了?
第四天我们终于离开了青木垅,我二叔带着我的一帮堂兄弟为我们送行,他们一直把我们送到村口的小路上,客气了又客气,可就是没一个人问接下来我和小杨会去哪儿,难道这也是预先就知道的?但我的疑惑并没有结束,当我和小杨下午赶到大龙村时,那位久违的“天使”却早已经无影无踪,我的预感终于应验了。有意思的是,我们找到村长加亮(他也是我的一名远亲),我们问他村里有没有一个“天使”,加亮竟然说,那只是一个外乡人,已经走掉了。
这当然是一个坏消息,我有一种感觉,加亮的回答是有备而来的,他似乎早已经在等我们的这句问话了,在我们来之前他就似乎已经准备得滴水不漏。我只得问那个外乡人的去向,加亮指了指我们的对面,他说可能到那边去了。我们对面就是小阴山,翻过小阴山就是另一个省份。我顺着加亮的手指朝山上望过去,山坡上是一片茂密葱绿的竹林,它们那么繁密细致,就像一层一层粘黏上去的,阳光下色泽也有了一些变化,慢慢地变淡了,变得凸出,那种距离仿佛一伸手就可以触摸到。突然之间我就有了一种宿命感,这是一个恰到好处的结果,它的合理性在于事情至此无疑各方面都能够接受,尽管这中间藏有某种先期设计的成分。但具体到我,那个耳熟能详的民间故事也因为“天使”的遁逸而留存了下来。这很像才看了场本以为胜券在握却以平局收场的球赛,失望也好,痛苦也好,转而又开始庆幸了。
当然,它来得或许还是太快了,一时之间我也分不清心里那种难以言传的轻松是出于怅然若失,还是因为如释重负?就这么,我呆呆地盯着对面的小阴山看了足足五六分钟,我不知道接下来该做点什么,所以想了半天,我还是决定让加亮村长先带我们去外乡人的住处看一看。
那是在一处坡地上,一个孤零零的茅草棚,这种茅草棚在农村只有夏天看青时才会用,但里面住过一位“天使”。我进去看了看,只有一床草席,连床被子都没有,也不知是“天使”带走了,还是他走后被别人收走。床下有一只锈迹斑斑的铁锅,还有一只差不多掉完瓷的搪瓷碗。这些疑点尽管明显却又无法深究下去,此外,最让我注意的就是棚外的一大卷草绳,盘在那里,我估计足足有十五六丈。加亮的说法是这个外乡人每天没事就坐在那儿编草绳,一编就是七八个小时,和谁也不来往,也不爱说话。说完这些加亮村长就离开了。于是我眼前出现了一个编草绳的妇人形象,她流着眼泪,正在膝头上费劲地把两把稻草搓成草绳,她的背上是一对行将枯萎的翅膀,它们耷拉着像一盆开败的玉兰花。小杨问我,“天使”要草绳干什么,难道这是她的回天之路?我当然不知道,也不会知道,所以我没有吭声。
回来后我写了一份含混其词的调查报告。报告中我说“天使”已经到了邻省。果然,几个月后又传来了“天使”在邻省活动的消息,但这已经与我没有太大的关系。
我想说的是有一次我八岁的女儿忽然问起这件事,她刚刚看完一部讲天使的电影,她问我,你不是去找过天使吗,你看到她了吗?我说没有,差一点。女儿为我惋惜,她说,要不然你就可以请她带你去天堂看一看了。是的,很可惜,大概是错过了。
女儿说,下一次你一定要她带你去,回来,你再把看到的告诉我。
我答应了。
1998年底我随老父回到他阔别近三十年的湖南老家省亲。尽管时间仓促,也谈不上有何有趣的游历,但此行还是会令我终生难忘。本文以誌纪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