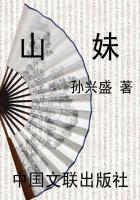林先生在八角到底呆了多久,我记不清。他下乡后好久我才进文学研究所进修(后改为文学讲习所,丁玲同志创办并任所长),我毕业了他还没回来。他去时是个不为人所知的小干部。等我毕业,他已发表了《新生》、《春雷》等红极一时的小说。老舍先生看了《新生》打心眼里高兴,马上就写了篇评介给以赞扬。这好像是老舍先生50年代写的第一篇为青年作者叫好的文章。我从文学研究所毕业后,响应“到生活第一线,到工农兵群众中去”的号召,转到建筑工地上做基层工作去了。那里也是林斤澜辅导的单位。林常来工地上和业余作者们见面,替他们看稿,提意见,开座谈会,并把改好的稿子推荐给《北京文艺)等刊物。像《台湾姑娘》这些名篇都是他在忙于辅导之余,挤休息时间写的。
1955年,我发表了《在悬崖上》,他很为我高兴。但指出我在文字上很不讲究的毛病。后来我写作注意在文字上严格要求自己,这跟他的提醒分不开。
1954年召开第一届全国青年作者会议,我俩一起参会。但不是正式代表,只是北京团的列席代表。有些文章在提到那次会时,把我俩也列入代表之中,这是误会。
1957年那场风暴,林斤澜逃脱了。我认为这要归功于他的女儿。坦白地说,当时某位有权势者想把他打成右派的热情很高,大概在预备打成右派名单中我是排在他后边的。他侥幸逃过此难,得感谢他的女儿和医院。正是召开“鸣放大会”那天他女儿出生了。过了几天开第二次会。医院偏巧又给小孩开错了药,差点造成事故。而参加这两次会的人,大部分被打成了右派,其“反动言论”,都是这两次会上的发言。
我定成右派,他的压力极大。有人是叫他用揭发、批判我来表明他的立场的。他什么都没讲。而在此后20年间,不管我是在北京劳动改造,还是“发配”东北时,他都是我最亲近的朋友。我忙不过来,他替我送妹妹上学;我不在北京,逢年过节他到家去看望我的母亲;有些我想不到的家务事,他想到都提醒我。1979年,我“提前退休”后回到北京。他被分配到一个电影院当勤杂工,但因病没有上班,没事在家中练习写篆字(曾给我写过一封完全是篆字的信,一看那字就是从康熙字典抄来的),我三天两头到他家聚会。有一天我在公园打拳,忽听到广播中报告重要新闻时,没提伟大的旗手和张春桥、王洪文的名字。此事不能跟别人讨论。我就忙去他家,故意卖关子说:“有件重大新闻,你知道了没有?”他问:“什么新闻?”我说:“今天的广播你听没听?”他说:“听了没发现什么。”我就说了我的发现。他也觉得不一般。我俩猜了一阵猜不出原因,我就回家了。第二天我又到他家去。这回轮到他卖关子了。他说:“你听到什么消息没有?”我说我不知道什么。他端着架子说:“我这才是重要新闻,可不能随便就告诉你。你得付点代价。”我听了就再三追问。并答应如果消息真有价值,我请他喝酒。他才告诉我说,昨天我走后他就去了杨沫那里。从杨沫处知道了打倒“四人帮”的消息。听了又惊又喜,又怕是误传。经过分析,两人都认为这样的谣言是没人敢造的。兴奋得想欢呼,但又还不敢声张。他不坚持要我请客,自己找出瓶酒来我俩举杯庆祝。几年来我们没少在一块喝酒,但从没像这天喝得那么痛快、高兴。
形势发展飞快,我俩又有权拿起笔写作了。北京出版社要出北京作家个人选集,林斤澜说:“出北京作家的选集,不能少了汪曾祺的一本。”但汪自己对此却不热心。他对编章说自己建国后写的小说不多,字数不够,不出也罢。林知道后马上去找汪曾祺,激动地说:“你的小说有自己的风格。为什么不出呢?字不够赶写几篇就成了嘛。你积极点好不好!”汪很感动,赶紧又写了几篇。这一写不仅把这本书的字数凑齐了,而且从此又燃起了写小说的热情,掀起汪曾祺小说写作第二次高潮,新时期文学史因此多了极为光彩的一页。
1984年我奉命到中国作协工作。在北京文联的同行给我送行的会上,斤澜坦率地说:“友梅去当书记,对他个人还是对工作,都未见得是好事。是得还是失很难说,恐怕还是失多得少。因为他的性格就是个作家,并不适合担任行政工作。”
我到中国作协后,工作有了成绩,他表示赞许。有失误他更毫不保留地当面指责,却从不怒形于色。我们相识数十年,他对任何人都没有怒形于色过。他会气得发抖而不会气得发火。最恼火时也只是摇摇头结结巴巴地说:“你瞧,你瞧,怎么会这样,怎么会这样……”我呆的地方是个是非焦点,我工作上、做人上确有缺点,但人们对我也常有不少误解。我极想离开这个岗位,但出于从小养成的组织观念,不得到批准,我做不出拂袖而去的事。这在特殊时期就引起非议。斤澜听到过非议,并且同意人们的看法。但他不在私下议论,也不因此而疏远我,而是当面对我说:“你把身外之物看得太重了吧!适可而止吧。”我很为他的诚恳和友情而感动。林斤澜是个好人,是个好作家。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我为有这样的朋友感到幸福和安慰。
好您哪,宗江大哥
写这篇东西我没跟宗江商量,商量了也白搭,他既不能阻止我写,也不能叫我按照他的意思写,大主意还得我自己拿。
世界不大,40年来闪展腾挪,东遛西窜,无意中竟跟黄氏五杰中的四位建交,就跟黄宗洛没有接触,可还是先后同事——50年代我在北京人艺搭过班。
1949年渡江不久,我团来了个新战士黄宗江。听说是红极一时的明星,周游世界的水手,《卖艺人家》的作者,《大团圆》的编剧。他怎么来当起小兵拉子呢?听到过传说,说法有几种,我也没考证哪一说最可靠。一说是于伶先生建议他参军的,一说是沈西蒙主动求贤的,最有趣而又最不可靠的一说是白文把他转让来的——白文当时正任特纵的文工团长,到上海招新兵,黄宗江到他那儿报名,白文觉得自己庙小,供不下这个大菩萨,就把他推荐到了军区文工团。
所以有此一说,因为这二位是老朋友。
白文是我敬重的老师和上级,我在他手下当过差,他是戏剧股长,我是他股里的小兵。他到解放区前是上海“苦干剧团”人台柱,《视察专员》演县长,《秋海棠》演副官,《大马戏团》里演慕容老头,红遍了大江南北。宗江比白文出道更早,锋头也更健,人们把他和石挥并列,连白文都承认演技上颇受宗江启发。上海人把石挥捧为“话剧皇帝”,在评议中认为惟一有资格与他较量的就是黄宗江。可宗江声明不参与竞选。既如此,只要宗江按部就班地演下去,“话剧丞相”的乌纱非他莫属,白文也少不了弄个“尚书”之类头衔。不料这两颗光芒四射的明星竟先后失踪了。这事在上海成了特大新闻,人们做过各种猜测,可谁也没猜准。因为连他们俩对自己的“下一步”都没猜准。原来白文本是中共地下党员,以演员身份作掩护进行抗日活动。正在一顺百顺之际,有人把个什么名单弄丢了,情况紧急,后果难料,组织上命令名单上的人立即转移,他就连夜带着老娘去了解放区,到解放区后就分到文工团当了我的顶头上司;宗江是报国心切,不肯在日寇占领下的上海受辱,投奔大后方去了,到了那继续演戏(这倒是他自己计划好的),可演着演着从舞台上一跳,跳到军舰上当水兵去了。
我听冯二哥(亦代)说过这件事。他说当年在重庆,有一天他上剧场后台聊天,看见位潇洒小生坐在化妆台上看书。看的竟是他散失掉的一本藏书,卞之琳的大著,不禁引起他的注意。这里的爱国剧人他熟识,这位却从没见过。听说上海来了个黄宗江,他估计八成就是他,便客气地问道:“您大概就是黄先生吧?”小生起立行礼,操一口京片子说:“不才是我,敢问您的台甫?”亦代指指书上原有的签名说:“在下就是冯亦代,请多指教。”两人脸对脸看了一会,都大笑了起来,马上就成了朋友。从此后宗江常到亦代寓所聊天,有一次聊晚了亦代安排他和一位亲戚同屋休息,那亲戚正准备投考海军,和宗江也一见如故,关上门他俩又接着聊。聊些什么不知道,总之天亮后再见宗江,他就宣布“投戏从戎”,说完跟那亲戚一块去报名去了,随后就换上了海魂衫跑到西洋受训,在英美扮演了个风流水手的形象。
白文和宗江分头奔向两个方向,谁也没想到何时再见面,等白文穿着军装带着手枪回到上海时,宗江又重登上剧坛了。海军训练一完日本就宣布投降,宗江乘着军舰在大西洋太平洋足转一阵后,一回到上海就又来个“投戎从戏”。白文替特纵文工团招收新人,宗江去看他时确也说过:“我要报名参军。”于是,以讹传讹,就说成宗江参军是由白文去引荐;其实宗江是有更大的来头的。
宗江穿上二尺半,很引起我们小字辈震动,像他这样的名家,在解放初期大团结的气氛下,到哪儿也少不了他一个位置、一份尊重,要参军也会得到照顾。身边例子很多,有位并不出色的什么家,一进门就享受团级待遇,也还过不惯,呆不住,干了几天又走掉。可黄宗江却坚持要从小兵当起,不要任何优待。我估计很少人知道黄宗江离休时的军阶硬是按照班排连营团师的台阶一级不拉爬上来的。他头一炮就来个锤震四平山!
当年像我这样行伍出身的文艺兵,本事不大可挺能挑眼,对新兵看不惯的时候多。新出校门的学生文化水平比我们高,可在艺术上不如我们有经验;名家艺术成就比我们高,按革命资历又没我资格老。对谁我也敢说三道四,惟独对宗江却只有服气。人家放着现成的统战对象、明星班头不当,自愿从最低级的文艺兵干起,没点真格的行吗?这就叫革命性、事业心,不服你来呀!
他对名利既然不屑一顾,也就不故作深沉状,对上级、下属、同伴都一视同仁。随随便便,坦率真诚,连对我这年龄、成就上根本不是一个档次的小老弟,他也毫不轻视。见面小邓长小邓短总要扯几句。我刚学写作跟他打听点学问,有问必答,既不摆架子也不讲客套,平等中透着亲切,指导时不失尊重。那时刚进城,生活还相当艰苦,纪律约束也严,可他咬着牙适应,决不含糊。他的自律和谦虚把大家征服了,热诚和恳切被大家接受了,成了我们中间能互相交心的一员。其实他总还有点知识分子的生活痕迹,在别人身上就会受到挑剔,对他却没人计较。比如:军装穿在他身上总比我们的板正干净,他自己买的皮鞋也比我们发的光亮俏皮,早上喝粥他还自己带点肉松之类小菜来,我们不光不说他特殊化,还凑上去夹一筷子。(注:对这点他坚决予以否认,说我诬陷他。我在此郑重把他的抗议注上,也同时补充一个细节:我还记得吃肉松的地点,是南京国民党最高法院二层楼的阳台。)
宗江参军后头一个任务是筹备开国大庆的演出。他和当时在南京的老艺术家戴涯、路翎等现编了一个戏,叫《国民党一团糟》。1949年10月1日毛主席在天安门上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他们就开始在玄武湖公园义务演出。这是出闹剧,写解放大军渡江后国民党一批要人的狼狈情景,剧中妙语惊人,洋相百出,逗得观众前仰后合。宗江演一位穿长袍的国民党元老,至今我还记得他神经质地高喊:“报告大家个好消息,第三次世界大战开始了!”据白文说他那“声音化装”的本事就是从宗江这里学来的。这次是我亲耳听到他的“化装声”,觉得他挺有本事。但这次演出给人主要的印象还是那股欢乐和团结的气氛。宗江回忆这件事时也说:“要是后来我们始终保持那样的大团结该有多好!”
1949年冬天,我调往北京,我想和宗江的交往会从此中断,有点遗憾。
我到北京文联报到,副秘书长王松声叫我随一位年轻同志先去熟悉环境,安排住处。那位同志抢过我的背包说:“来,你就跟我住一间屋好了。咱们文联的团员也都编在一个小组,我是小组长,名叫黄真,原名黄宗淮。”我笑道:“黄宗淮!有意思,我有个同志叫黄宗江,一江一淮很像哥俩。”他说:“那是我大哥,宗英是我妹妹。”这一来我倒跟宗江的关系更近了点。他来看黄真也跟我亲切地聊一阵。过了两年他也调到北京来了,还新结了婚,娶的竟是我们文工团的元老,荣任前线话剧团副团长的阮若珊。由于历史原因,我对阮若珊和对茹志鹃一样,始终看成是自己的大姐,由此我和宗江的关系更近一步。当然我也有所失——我和宗江差着档次,以前在交往中我常拿在文工团的资历来壮胆,可在若珊面前我永远是新兵,甚至还是孩子,我想这回我算小到家了(不出所料,至今花甲已过,宗江还是叫我小邓。只在写文章时后边加个注:“叫友梅的那个小老头!”)。
他是在《海魂》写完后正式调到北京来的。《海魂》有一部分题材来自起义的“长治号”军舰。“长治号”起义到南京我是最先采访的人之一,电影剧本的几位作者我都熟悉,我就打听他们的创作情况,这才知道他碰上多么尴尬的事。《海魂》剧本写得好,拍得也好,是要载人电影史的名片。可《海魂》的创作过程却是另一出好难演的闹剧。宗江在里边扮演了个觉新式的人物,我又看到了他忠厚宽大,忍辱负重的一面。宗江是个人道主义者,是个君子,不掺假的好人。
宗江的朋友遍天下。不论什么行当,不管什么流派,不计年龄档次,他都交往。他有句名言,叫:“多山头即无山头。”这句话对我做人颇有影响,但要学到他那火候不易。他表面上超脱随和,内心是非清楚、爱憎分明,正义感和责任心极强,强得把功利二字甩得好远。本来他能写的题材极多,要洋的他是燕京的科班出身,西方各种流派的作品他早就有所了解,而且读的是原文不是译本;要土的他书香门第,博览群书,真要弄什么京音律韵,我这样的根本不是个儿,在他写了《海魂》、《柳堡的故事》等名作之后有位负责人跟他说:“你总这样跟工农兵不着边不行啊,得深入工农兵生活。”他就扔下自己熟悉的一套,毫不犹豫地深入工农兵去。下农村,进西藏,随后就写出了热闹一时的《江山多娇》、《县委书记》和一部名垂永久的《农奴》到此也算是功德圆满了,可他还要再接再厉,竟视死如归地去了美国正进行“地毯式轰炸”的越南前线,并且在弹片横飞中写下一部剧本。天可怜见这剧本还没发表就被伟大旗手看中,赫然列入了重大“毒草”的名单。等他从美国炸弹下返回北京,便带着一身罪名,发往大西北“充军”了。
就我所知,宗江在“文化大革命”中的生命危险绝不比在越南小。可死里逃生后想干的第一件事还是写作。“文化大革命”过后我俩头次见面他就谈他正在写和正要写的作品,不久就给我送来两个剧本,一本是写一个连队,另一本是写一位被“四人帮”残酷迫害致死的烈士。他跟我说:“我知道这俩戏都不能拍,可我不写出来对不起死去的和活着的。我写出来了,哪怕只给朋友们看看我也算了结一番心愿。”我无法评判过去有些做法的得失,但宗江为人民,为事业的这种热诚勇敢劲头我是永远崇敬的。别看他喝了一肚子洋墨水,在十里洋场出过大风头,却绝不是文学、艺术前边加个“玩”字的公子哥儿。
宗江是个多栖、全才的艺术家。我弄不清他到底有多大本事,只看到凡是派给他的活他都干。50年代有一阵听说他在写越剧《春香传》,那剧彩排时我也看到他在台前台后忙活,可说明书里并没他的名字;又听说写了话剧,却又不见下文。有天我和画家彭彬在长安听侯宝林的相声。除去我二人,招待席的一排座位全空着,演出过一半,我觉得亮光一闪,有位穿蓝绸旗袍的小姐娉婷而至,紧挨我坐了下来。那时穿旗袍的人已经不多,何况小姐眼光在我脸上扫了一下,我便扭过头放肆地看了一眼,不看则已,一看招来几句好话。
“对不起,打扰您了,耽误您听段子了。”
“嗨,我当是谁呢,言小姐!”
“冲您点了半天头您理都没理,原来您还认识我呀。”
那一阵言慧珠正跟我熟悉的一位管事人闹气儿,不是一般的气,是气得要自杀。我既和她那位对手一个衙门里办公,挨几句抢白也算活该,我就连忙道歉。我看她精神焕发,不像要自杀的样儿,搭讪说:“您最近在忙什么?”她说:“排《春香传》哪,是宗江给帮的忙,作家里还是有人够交情的。”
我才知道宗江在帮她排《春香传》。
果然,《春香传》演出时门口牌子上写着“艺术指导黄宗江、郑律成”。
戏不错,得了奖,言慧珠是我最佩服的三位女演员之一。论功底,论扮相,论嗓子,论梅派戏的地道味,没几个人能赶上她。在这点上宗江和我有同感,不过他还是看到言小姐更多长处。他说《春香传》连编剧带导演其实都是慧珠自己干的,他只帮了点忙,慧珠却坚持要把他的名字写出来。这和他在另一出戏里的遭遇相比。就看出了慧珠的人品。不过宗江刚看到门外牌子时还有点不安。他说:“怎能把我的名字放在郑律成前边呢。人家是《延安颂》的作者呀。”后来又看到说明书,他心里才踏实。说明书上印的是“郑律成 黄宗江”。由此宗江得出个结论:“言慧珠才女也!”
可叹才女命运多舛,不久后自杀一次,幸好被抢救过来,但到“文化大革命”时终于还是拂袖而去了。
后来我还看过她一些戏,但最深的印象仍是抗美援朝时演的《凤还巢》和与宗江合作的《春香传》此外还有出《百花赠剑》,我觉得谁也没她演得好。
最先鼓励我写电影的是黄宗江,虽然我至今也没写成一个电影剧本,但这份关心我不能忘。
1956年我的《在悬崖上》发表后,接到在电影学院要毕业还没毕业的董克娜的电话,约我去谈谈。意思是要我把它改为电影剧本,他们作为毕业论文来拍片,后来桑夫同志又来约,说北影会拍得更好。但我对电影把握不大,兴致不高,就找宗江商量。他那时结婚不久,住在西单大院胡同。我去时他正享受天伦之乐,就背着小女儿,拉着大女儿跟我谈话。听说丹娣如今也做了妈妈了。我不知二小姐长大后的性格如何,小时给我的印象是十分可爱却颇欠文静。在她爹背上、脖子上不断地笑和叫,有时还加上跳!我们整个在她震耳的欢笑声中费劲地谈了一晚上。宗江听她的叫声像听交响乐,精神更能集中,思维更加敏捷,听完我诉说后极力鼓励我写,还在二小姐的伴奏下为我出点子,指出小说中哪些细节阅读起来虽有趣味,但无法用视觉艺术表现,并教给我如何改成可视形象。就这样我也还下不了决心,过了好久都没动手。
1957年4月30日这天大清早,接到黄宗江一通急电:“喂,小邓,你上我这来一趟好吗?”
“什么事?”
“来了再说。”
“多咱去?”
“吃了点心就来,越早越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