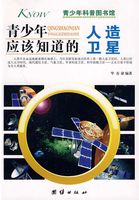多年前的老人还是女人,多年前的冬天奇冷无比。多年前,老人有一位十六岁的儿子。儿子是家中长子,有着与年龄极不相称的沉稳和责任。我仍然依稀记得那位少年的模样,他有着宽宽的肩膀和魁梧的身材,他的嘴巴上长着淡蓝色的茸毛,与人说话时,他喜欢低着头,红起脸。那是他永远的模样。他的人生如同一个突然静止的座钟,指针永远地停留在十六岁那年的刻度。
那时谁家生活都不宽裕,女人家的生活尤为艰难。不过即便如此,她也坚信自己可以让一家人在寒冷的冬天里穿上暖哄哄的棉衣。可是女人的儿子在那个冬天里突然拒绝棉衣。去年的棉衣小到不能再穿,他就不再需要棉衣了。他说他不怕冷,他说他可以为家里省下一点棉花和几尺棉布。
他也许真的不冷。每次回家,他的手和脸总是热的。其实村子里没有棉衣的远不止他一人,那些年月里,很多人把所有的单衣一件件全部套到身上,便可以熬过冬天,把那些衣服脱到只剩一件,便开始过夏天了。他们只有衣服的概念,绝没有冬衣与夏装之分。
可是女人还是心疼他。女人说我明天就给你买棉花扯棉布。他说你做了我也不穿。女人说可是冬天还长着呢。他说可是我真的不冷。他摘下帽子,头顶升腾起袅袅的白气。他说你要做的话就给弟弟妹妹们做两副棉手套吧……他们的手,都生了冻疮。
天生节俭的女人于是犹豫了。儿子的身体很好。儿子几乎从不感冒。也许,他真的不冷?
可是早春时候,她的儿子却突然感冒了。少年坐在院子里劈完一堆木柴,累到满头大汗。他脱到只剩一件小褂,他的胸膛崩起结实的肌肉。他就那样躺在土炕上睡着了,然后,半夜里,他开始咳嗽,并且,伴着低烧。
谁会把感冒当回事呢?包括她,包括她的丈夫,包括她的儿子,包括她的邻居。早晨儿子再一次衣衫单薄地走出家门,院子里,她发现自己的儿子打了一个极轻微的寒颤。
她什么都不管了。她一定要给自己的儿子做一件棉衣。她买了棉花,扯了布。可是棉衣还没有做出来,他的儿子就死去了。
感冒引起了肺炎。生命脆弱如纸。再结实再强壮的生命,也抵不住病毒的轻轻一击。
生活还得继续,女人的生命还得继续。然后,突然,有一天,轻轻眨一下眼睛,三十多年的光阴就溜走了,自己就老了。
清明那天我回老家祭奠一位英年早逝的朋友,旷野里,再一次遇见老人。风烛残年的老人似乎由皱纹雕刻而成,那天,她挪着僵硬的躯体,去旷野看望她十六岁的儿子。
她完全漠视了我的存在。她的世界里只有她的儿子。她为她的儿子烧了很多纸钱。她和她的儿子说了很多话。
那些话,让我唏嘘不已。
回家问过父亲,父亲说,这并不奇怪。每一年清明,她都要为自己的儿子烧些纸钱,都要把那句话,重复好多遍。
哪怕清明的阳光已经有了温度。
哪怕时光已经过去了三十多年。
哪怕她都快要忘记儿子的模样。
哪怕她的思维已经变得模糊不清。
她坐在清明的野地上,认真地把一张张纸钱投进面前的火堆。她说儿,听娘的话,用这些钱,买件棉衣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