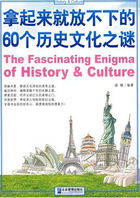雄鸡的神经系统如弓弦,被雄性激素拉得满满的,因此,它争强好胜不示弱,好斗。
鸡有五德,文、武、勇、仁、信。古今斗鸡的风俗,将这武这勇并用了。
斗鸡娱人吗?那简直是惨烈的刺激。这该是当今的保护动物一类组织所力主禁止的活动。这种活动有着久远的历史,据说夏朝时就已经开始了。它掀动的狂热,曾紧绷一代又一代人的心弦,闹出人间悲喜剧,甚至演成政治风云的变幻。
《史记·鲁周公世家》:“季氏与昇氏斗鸡,季氏芥鸡羽,昇氏金距。季平子怒而侵昇氏,昇昭伯亦怒平子。”斗鸡引起纠纷,鲁昭公也被拉进纠纷中来。鲁昭公发兵攻打季平子,季氏则联合其他力量抗击鲁昭公,把鲁昭公赶到齐国去。
这场斗鸡纠纷,起因不在于胜负结果,而在于因双方为增强鸡的战斗力,各自使用了花招,结果鸡的怒目相对,变成人的怒目相视。
“季氏芥鸡羽”,《左传·昭公二十五年》记为“季、昇之鸡斗,季氏介其鸡,昇氏为之金距”。介为甲。介其鸡,有种解释是:“为鸡著甲”。另有一说,介、芥相通,《史记》说“芥鸡羽”,宋代裴枓集解所引的解释是:“況芥子播其鸡羽,可以坌昇氏鸡目。”在鸡羽撒上些芥粒或芥末,用来眯住对手的眼睛。《史记》此段记载,据《左传》而来。司马迁用“芥”而不用“介”,大约是鉴于汉代斗鸡实际采用的“技术”吧。
但此后写斗鸡的诗文便常用“芥羽”一词了。如汉代有“芥羽张金距,连战何缤纷”诗句,南朝梁简文帝诗有“芥羽忽猜俦”句。北周王褒《看斗鸡》诗也有:“妒敌金芒起,猜群芥粉生”的说法。
为了取胜,斗鸡者的手段不止芥羽一项。依《左传》和《史记》所记,昇氏在与季氏斗鸡时也采取了置敌于死地的措施——金距。金距是给鸡爪套上锐利的金属爪套。鸡五德之一的“足傅距者武也”,说的就是经如此武装的鸡,与赤手空拳相比,杀伤力自然大增。
为提高斗鸡的战斗力,古人还发明了另一种小手段:在鸡头上涂狸膏。三国曹植《斗鸡篇》言:“愿蒙狸膏助,常得擅此场”,北周庾信《斗鸡》说“狸膏熏斗敌”,所言的便是此项手段。狸膏即狸的膏脂。狸,也叫狸猫,善于捕鸡,为鸡所惧。斗鸡前,将狸膏涂在鸡头上,以借助狸的气味,涣散对手的斗志。
斗鸡者对于胜券的把握,不仅在于为鸡装上明枪暗器,更重要的是对上场厮杀的鸡进行特殊的驯练。《庄子·达生》讲周宣王的斗鸡:
纪沬子为王养斗鸡。十日而问:“鸡已乎?”曰:“未也,方虚骄而恃气。”十日又问,曰:“未也,犹应向景。”十日又问,曰:“未也,犹疾视而盛气。”十日又问,曰:“几矣。鸡虽有鸣者,已无变矣,望之似木鸡矣,其德全矣,异鸡无敢应者,反走矣。”
这只鸡,为驯其善斗,至少专门驯养了40天。先驯十天,不行,还显气躁;再十天,不行,欠沉稳;又十天,驯鸡人仍不满意;又过了十天,可以了,那鸡被驯得沉着若呆,各种善斗的本领都掌握了,即使有鸡打鸣啼叫,它也阵脚不乱,似木鸡一般。旁的鸡见了它掉头就逃,没有敢于应战的。《列子·黄帝》中也可见相同的记载。
这个驯斗鸡的故事,就是成语“呆若木鸡”的来源。只不过,那成语用以形容因恐惧或惊讶而发愣发呆的样子,此一呆与彼一呆已是两码事。《庄子》所称赞的“望之似木鸡”的境界,是一种大智若愚一般的境界,确是不同凡响。
统治者、贵族阶层嗜好斗鸡,上行下效,使斗鸡之俗延续了几千年。《史记·高祖本纪》注引《括地志》云:“太上皇时凄怆不乐,高祖窃因左右问,答以平生所好皆屠贩少年,酤酒卖饼,斗鸡蹴鞠,以此为欢,今皆无此,故不乐。”原来刘邦的老子身在皇宫大内,却总想着踢球斗鸡的民间生活。于是,为使太上皇开心,刘邦建新丰城。《汉书·孝宣王皇后传》记,其父“奉光少时好斗鸡,宣帝在民间数与奉光会”。此外,正如上文所提到的,三国魏的曹植写过《斗鸡篇》,南朝梁简文帝有《斗鸡》诗传世,北周王褒也赋诗《看斗鸡》。凡此种种,不一而足。
唐代,因玄宗皇帝的喜好斗鸡之戏,而造成一种社会病态。据唐代《东城父老传》记,李隆基即位前就好斗鸡。那时斗鸡之戏是清明节俗的一项内容。李隆基当上皇帝后,在宫内建鸡坊,“索长安雄鸡,金毫、铁距、高冠、昂尾千数,养于坊中”,并有五百人专司驯鸡。结果,“上之好之,民风尤甚”。有钱的倾家荡产买鸡,没钱的就以假鸡为戏。长安有个名叫贾昌的少年,驯鸡有一套办法,博得玄宗欢心,一下子就荣华富贵,成了闻名天下的“神鸡童”。
这个“神鸡童”确有本事。据《东城父老传》描写,元宵节和清明节时,贾昌到骊山为唐玄宗表演斗鸡,他“冠雕翠金华冠,锦袖绣襦裤,执铎拂,导群鸡叙立于广场,顾眄如神,指挥风生。树毛振翼,砺吻磨距,抑怒待胜;进退有期,随鞭指低昂,不失昌度。胜负既决,强者前,弱者后,随昌雁行,归于鸡坊”。为使斗鸡昂奋起来,贾昌先激发之,使得雄鸡“树毛振翼”——毛羽竖立,亢奋地拍着翅膀,“砺吻磨距”——一再磨砺尖喙和跖距;“抑怒待胜”——处于一触即发的临战状态。斗鸡开始后,贾昌驯的鸡,随着他的指挥鞭,进退周旋。斗鸡结束后,这些鸡排着齐整的队形,随贾昌返回鸡坊。这不仅是斗鸡,也是出色的驯鸡表演。
唐代斗鸡驯鸡发达,社会却为此付出了世风奢靡的巨大代价。斗鸡使人如痴如狂,也使一些“斗鸡小儿”恃宠骄横,不可一世。诗人李白《古风》诗:“路逢斗鸡者,冠盖何辉赫。鼻息干虹泜,行人皆怵惕。”他们气喘得粗,路横着走,老百姓唯恐躲之不及。
如此玩物丧志,使斗鸡走马成了并不怎么光彩的词。对坐龙椅的皇帝也是如此。明代张居正等辑《帝鉴图说》,将历史故事付诸图画,进呈当朝天子,以事规谏。其中有两幅涉及斗鸡题材。一幅表现斗鸡场景,两只鸡正相持,周围站着观斗者;另一幅,不仅有抱鸡者步行于途,而且有抱鸡策马者疾驰而过,画面上端,云间依稀露出宫殿的屋脊。此画要讲的话,一目了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