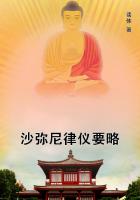这一次,她没有喝红色液体,我却没有感到因此而感到高兴,因为她说我不是她的孩子。她有什么不好承认的呢,我都承认一个恶魔是我“娘”了,难道我比恶魔还可怕?
晚上我听到了外面传来凄厉的叫声,我走出我的房间,没有遭到任何阻拦。
我的奶娘虽然自从我会走路后再也没有管过我,但是晚上一直会记得锁门,这次却没锁门……这是一件从来没有发生过的事情。
我想着她是不是也和上一个奶娘一样突然消失了。
我的奶娘总是换来换去,虽然我不知道这是为什么。
可是在我偷偷走到“娘”房外,看到全身流着红色液体的她时,我用我的方式理解了那些奶娘离开的原因,我想她们应该是被吓跑的。
毕竟她们平常看到我就害怕,要是看到她这般恐怖的样子,还不马上落荒而逃。
我突然对她惺惺相惜起来,因为我们都让人害怕。
我从窗户爬进去,因为门口守着一堆瑟瑟发抖的婢女,我下意识不想让她们知道我来了,所以我只好从窗户爬进去。
好在窗户并不高,勉勉强强我爬进去了。
她显然没有料到有人进来,只是一直不停地擦拭从她身上冒出来的红色液体,我想是不是因为她喝我体内的红色液体喝太多,一时间全流出来了。
都说了喝那个不好。
看着她身上不停冒出来想红色液体,我隐约明白,喝我的液体可以让她不再流。
我四处看了看,找到那个泛着碧绿色光芒的碗和一把匕首,对着自己的手臂割了一道口子,接了满碗,然后捧到她跟前。
这次,我没有叫她娘。
她看了我一眼,藏在那片红色液体下面的眼睛泛着光,估计是她眼前不断滴落的液体让她看不清我是谁,她摸索着接过我踮起脚高举的碗,咕噜咕噜喝着那碗红色液体。
她身上的红色液体果然没再往外,我瞪大了一双眼睛。
恢复正常的她却没有感谢我,反而瞪着一双大眼睛,指着我的鼻尖,失声尖叫:“你这个恶魔!”
我不是恶魔,你才是。
我心里想,如果能说话的话,我想我应该会说出来,因为我发现她没有看到我心中想的,反而是我看到了她内心一片紊乱,奔腾着各种情绪。
最后,在这些情绪高速运转间,她重重地倒在地上,晕倒了。
门口守着的婢女慌慌张张闯进来,看到我个个像是看到最可怕的东西般,眼珠子都快瞪出来了。
我悠悠地离开,那一刻我自己也不知道我在想什么,只是想离开,从容地离开。
从这以后,我再也没有见过她。
每个月,会有不同的人过来划开我的皮肤,取血,拜那些人所赐,我终于知道那个红色液体叫做血,并不是没有用的东西。
我的生活维持原样一直到八岁,除了每个月需要受一次伤,流一点血之外,其余时间我可以到处乱逛。
因为那些伤口都没有留下疤痕,我对被割伤的痛楚也麻木,所以我并没有多在意,反正从小这样过来,尽管这种流血在别人眼中都多可怕,
期间照顾我生活起居的奶娘不知道换了多少个,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她们消失不见了。
我并未关心,反正府中经常有人这样消失。消失对她们也许是好事,那时候在我眼中,消失就意味着离开,离开是一件多么美好的事情啊。
可是我不会离开,以前是因为离不开,现在则是因为她是我在这个世界上唯一的联系。我知道我一离开,她必然活不成,我则需要她和我一样的让人恐惧的特质。
八年来,我一直看人“说话”听人说话,坐在高高的树端,躲起来边看边听,有时候听着的和看到的有很大的差别,我就会觉得厌烦,然后开始看书。
书中记载的大部分无关听到的与看到的,很多是一些不带情绪的资料讯息,这让我觉得安全。
怎样学会认字的?
好像是通过各种方式偷学的,不记得了,反正不是她请人教的,在她眼中我不知道我算什么,反正不管是什么,总归不是一个与她有平等地位的人。用那些下人的话讲,我其实就是一昧药。
为此,我还多加留意了与药有关的各种词汇,也翻阅了很多与药有关的书籍,其中我犹为迷恋一种“药”……毒药。幸亏府内有一个藏书丰富的藏书阁。
就这样看书,看人说话,流血,日子循环着过。
本来以为这种时光会延续得很长,直到有一天我发现我眼睛开始冒出和她一样的绿光,我了解这种时光里又多了一件参与循环,算是一种改变吧。
刚开始我没察觉,还坐在树端看书,突然间觉得眼睛胀痛,才打算回房休息,一路上遇上的人纷纷躲避,我不以为意,虽然这次他们反映更激烈了点,但是对于我来说没有区别,都是恐惧,多一点少一点没有一点区别。
直到回到房间,看到镜中泛着绿光的眼睛,我才顿悟,我果然是她生的。然后就一直坐在凳子上等着全身流血。
在发现全身并没有变化后,我下意识地松了口气,豪不迟疑地要出门找她。
门一开,她已经站在门口。
“风儿。”她叫,这个称呼像是她已经叫了上千次上万次般熟稔,可是我却在里面听到了陌生,这是叫我吗?我怀疑。
那时候,我叫什么名字我自己都不知道,从来没有人叫过我名字,也从来没有人正式主动和我说过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