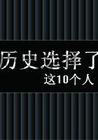(一)
村庄的出发,是从一条小溪开始的。
小溪如一弯新月,亮亮的,在农田的阡陌间时隐时现。
潺潺地,小溪的声音很清脆,很柔情,如响在深夜的琴弦,弹奏得空灵而又悠闲。
溪中青苔丝丝飘浮,画面很美,水墨似的,幽雅,真实。
总感觉到有一丝丝的凉,凉得让人心悸,凉得透心,从踏过田埂的那一刻起,那股股凉就无处不在,躲也躲不开。
溪畔的一些草,对于我,肯定好多叫不出名字。草也习惯开花,开很野很盛的花,满沟满壑地灿烂,晃得人睁不开眼。
要寻找什么,要想起什么,仿佛不能了,什么都遥远了。
(二)
太阳出来了,田埂上蒸腾起一股热气,很逼人。
村口,一棵黄葛树下,母亲在呼唤。
穿上鞋子,我爬上溪岸。
“回来了,回来了”
每家房顶的炊烟袅袅升起,让宁静优美的村庄浓墨重彩起来,散发出一股熟悉的乡村柴禾的味道。
吱嘎——开门的声音,噼啪——柴禾燃爆的声音,咣当——瓢盆碰撞的声音,汪汪——狗叫的声音,咯咯嗒——鸡鸣的声音,哞哞——牛吼的声音。
村庄的正午,除了这些声音,就是寂静,寂静得连人出大气的声音都能老远相闻。
“快洗洗,吃饭了!”母亲从屋里端出一盆热水,盆边搭一根新买的毛巾,忙不迭地叫我们洗手。
很不习惯,仿佛有一种深深的隔膜,无端地生出来,无法释怀,不知什么时候,母亲对于他的儿子变得这样的生份了,这种超乎寻常的关怀,让我接受不了,而又阻止不了。
母亲七十多岁,一个人孤苦伶仃地守在乡下,就是不愿进城,而事实上我们也不可能时时地下乡看她老人家,想起这些,多少有些无奈。
别看说其它的滔滔不绝,可是说出“回来了”三字却中气不足。
(三)
午后的村庄静谧而又空寂,一切仿佛都静止下来。
惟有微风,惟有阳光,脚步缓慢,盘旋缠绕;树叶绿得碧了眼睛,地上碎银似的光斑层叠着、闪烁着。
慵懒,闲散,碗筷一丢,洗涮、喂牲畜、泡衣服等等家务事忙完之后,母亲常常背上背篼到自留地里给种的小菜掐尖、打叉,或者清理地里的杂草。
小时候很少有午睡的习惯,也不想看书,有时在大人的催促下偶尔躺下眯一会,也是睁着眼睛数瓦片、桷子。为此,我常常跟在母亲的身后去地里帮忙,其实也说不上是帮忙,甚至还可以说是添乱,追逐花间的蜜蜂,把刚长出的南瓜苗踩坏,薅草却把种下的菜蔬铲除,闻到花香,就摘下花朵悄悄揣在怀里,听见蛐蛐的叫声,遍地里寻找,撬松母亲刚压紧的泥土,一些冒出地面的幼牙,被踩回了泥土,而母亲嗔怪的眼神却让我嬉笑不已,大声呵斥的声音中我落荒而逃。
父亲去世后,家里更显压抑,母亲就成为家中的主要劳动力,那时的我们似乎一点也不醒事,照样的调皮,照样的无忧无虑。多年之后回到家里,还时常会想起父亲,想起他劳累过后的那种疲惫样,吃完饭后躺在竹椅上,旁边燃起一堆浓烟的情景总在脑海中萦绕。其实我是非常怕父亲的,他的眼神非常严厉,从来没有一个好眼色,我是从来不敢正眼看一下他,现在回想起来,父亲也是迫于生活的贫困与无奈,一家子人的生活压得他喘不过气来,尽管辛苦劳累,但是地里的收获却是有限的,他面对那种局面也只能选择沉默,选择严厉,以我现在的猜测,他对我们几姊妹的期望却是很大的,他无法给我们提供智力等方面的支持,只能对我们严格要求,他的爱就只能选择这样的方式,让我们接受不了的方式,或者说是理解不到的方式呈现。
城里的生活节奏太快,我们都似乎忘了我们的村庄,村庄的一切似乎都遥远起来。
可是不能提到村庄,一提到村庄,我们就会心酸,就会无缘地流泪。
比如现在我站在老屋前的地坝上,几分钟内都没有挪动脚步,这在平时的生活中是很少见到的,这是为什么,可能没有人去深究。
(四)
那堆草垛还在,可是伊人不在。
草垛已经不是原来的草垛,但形状却保持完好。
草垛离家只有两条田埂的距离,就在小芳的屋子后面。
小芳屋后的田埂是我们家的柴山,田埂上长有很多的树,主要是柏树,大根大根的,柏树枝丫是我家灶前的柴禾,塞进灶堂时燃起的烟好香好香,至今我一闻到城里人熏制腊肉的香味时我就会想到那种香。
剃下柏树下半部分的枝条,草垛就扎在柏树上,扎草垛是有讲究的,如果从地面一直扎起,那这棵树肯定是毁了,因为稻草集中在一起,发出的热量足够把这棵柏树烧死,所以一般的草垛离地面都有一定的距离,这样就形成一个很好看的草垛形状,远远看去,就是一支纺线的坠子,两头尖尖,中间突出。
就是那么一个空间,成为我们学生时代玩耍的天堂。
小芳很美,是那种乡村最为质朴的美,一双大大的眼睛,扑闪着,充满了好奇与智慧,我们一院子的小朋友最爱听她讲话,最爱围在她周围,听她给我们讲不知她在什么地方听到的故事;小芳唱歌也好听,比起村头树上广播里播放的歌曲好听多了,她唱歌时,我就在旁边为她吹笛,笛声悠扬,歌声婉转,身旁趴着支起耳朵听歌的小伙伴都入迷了。
乡村夏天的夜是神秘的,是温馨的。
大伙儿都喜欢小芳,喜欢与她在一起。
后来,小芳远嫁他乡,我们几个楞头青在此聚了几次,感觉没意思,都散了,草垛下空余美好的回忆。
后来,我也有了我的新娘,但是我的诗中还反复出现草垛的意象,小芳的身影在诗中反复跳跃,让我抓捏不住。
(五)
山高水高,村庄就在半山腰上。
清晨,各家屋檐的炊烟缭绕在树尖,在房顶,与山间的雾岚纠缠在一起,如入仙境。
山泉,从山中巨石缝中流出,嘀嘀嗒嗒,山泉的旁边滴出一深潭,深潭清冽,潭岸垒垒石块,圈出一个椭圆的泉井,石块上青苔青绿,丝丝缕缕,摇弋多姿。
阴浸,凉爽,泉水叮叮咚咚的声音,鸟雀鸣叫的声音,落叶坠地的声音,岩土开裂的声音,树木生长的声音,汇成了优美宁静的旋律,百听不厌,百读不厌。
木桶咣当着来了,铁皮桶当当着来了,村里汉子来了,村里洗衣的村姑来了,小木凳斑驳着来了,凉椅吱嘎着来了,蒲扇摇晃着来了,村言俚语叽喳着来了,打情骂俏的浑言碎语来了,这里汇集成了村庄最为热闹的市场。
话题都是永久性话题,百谈不厌的话题。
从山泉边可以了解村庄,从话题中可以折射村庄。
山泉从古流到今,山泉见证了村庄的历史。
(六)
不常回,村庄已然陌生起来。
村头黄葛树依然,乡间小路依然,散落在半山腰中的村落依然。
山中草木丰茂了,山中巨石不在了,山泉的泉眼变小了,村里的人减少了,鸡鸣狗叫的声音稀少了,村庄安静得有些令人窒息,偶尔看见在田土中躬耕的乡亲,那身影就像是当年父亲的样子。
高速公路横穿了整个村庄,村庄一分为二,高速公路上的车流无声地驶过,路面上空留下阵阵震颤。
大巴在村庄前一晃而过,村庄已然找不到停靠的站点。
望着渐行渐远的村庄,我的眼前不禁模糊起来。
(原载《夜郎文学》2009年第7——8合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