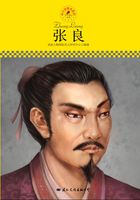袁世凯不让盛宣怀这个邮传部侍郎插手邮传部的事,最理直气壮的理由,是他所悉心筹划的赎回京汉铁路之事(主要由邮传部负责执行),眼下就要接近成功。而当初修铁路时,是由盛宣怀经手向比利时借的款,其中乱七八糟的猫腻很多,其理应回避。
这个京汉铁路,说起来和袁世凯关系很大,不过最早提出修建此路的,是时任湖广总督的张之洞,那会儿袁世凯还在小站练兵。
朝廷对张之洞的建议很感兴趣,但苦于没钱,只能向外国借款,负责该项工作的,正是中国铁路总公司督办盛宣怀。
1898年6月,借款合同签订,总金额高达1.12亿法郎。随后就是戊戌变法,再然后是义和团、八国联军,整个国家陷于一片混乱之中,所以直到1901年底,京汉铁路只修了从卢沟桥到保定这一小段。就这一小段路,还被义和团给拆了,并焚烧了不少沿线的天主教堂,沿线的百姓也没少遭殃,这给在山东剿办义和团的袁世凯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他因此认定铁路沿线不安全。
袁世凯署理直隶总督后不久,京汉铁路全线复工,按照最初的计划,铁路要从周家口经过。周家口历史上是河南的四大商业重镇之一,更是举足轻重的军事重镇,曾国藩就认为,江苏徐州、山东济宁、安徽临淮、河南周家口在军事上非常重要,尤其周家口,它是豫东和京师的门户。
但袁世凯看重的不是这些,他只是朴素地觉得周家口这地方,离项城太近,一旦通了火车,以后若再打起仗来,老家定会遭兵灾之患,于是建议铁路向西移100里。虽然只是建议,但出自直隶总督之口,况且那会儿盛、袁关系还好,盛宣怀自然照办,结果京汉铁路所经之地就从周家口移到了漯河。相应的,往北所经之处,也就由开封变成了郑州。
相对于通都大邑周家口,当时的漯河不过是个几千人的大村落;而相对于河南巡抚衙门所在地省会开封,当时的郑州还叫郑县,人口不到2万。1906年4月1日,京汉铁路全线通车,火车开过,郑州、漯河日趋繁盛,周家口却渐渐衰败下来,就连开封也已风光不再。什么叫好心办坏事?这就是!
京汉铁路自通车起,经营情况一直很好。袁世凯当上军机大臣后,觉得此铁路经营权居然掌握在比利时手里,其背后更有法国、俄国的影子,很是不妥,尤其是万一打起仗来,这条从汉口到北京的铁路若不能自主,那就等于被人扼住了咽喉,简直是岂有此理?
但赎回铁路要大把的钱。大清朝国库空虚早已是常态,袁世凯明知朝廷指望不上,便把筹款的事着落到了梁士诒头上。
梁士诒字燕荪,广东三水人,生于1869年。20岁时曾与梁启超在佛山书院同学,并于当年考中举人,两次失意之后,在25岁那年考中进士,被选为翰林院庶吉士。与当时的主流文人不同,他在饱读圣贤书的同时,也刻苦攻读经世济民之学,像财政、农业、河渠等方面的学问,都有所研究。
功夫不负有心人,1903年6月,清廷首开经济特科,这是晚清新政的一项重要举措。梁士诒考了一等第一名,可谁知他的名字犯了忌讳,因为有传言称他是梁启超的弟弟,而康有为字祖诒,这“梁士诒”分明就是“梁头康尾”,着实可恶,于是就被慈禧亲自取消了录取资格,到手的状元没了。一等第二名是前面说过的大才子杨度,他因为是湖南师范出身,和维新派领袖、与谭嗣同并称为“浏阳二杰”的唐才常是同学,当然也被老佛爷给斥之门外。
有类似乱七八糟问题的牛鬼蛇神还有不少,朝廷的眼睛是雪亮的,最终一等前五名只录取了一个,让人很是扫兴。老佛爷也觉得这事挺没劲的,结果大清朝的经济特科只开了一场就无疾而终。
好在是金子总会发光,梁士诒通“时务”的大名因为这次考试不胫而走,其时袁世凯正在直隶大刀阔斧地进行改革,求贤若渴,闻听翰林院里居然有此人物,便迫不及待地叫唐绍仪把他请到天津来一见。谁知梁士诒刚刚受挫,对经济之学心有余悸,所以当袁世凯问起“先生有何特长”,他张口就答:“我教过书,字写得不错,还会写诗。”袁世凯大失所望,草草结束了此次会见,认为他徒有虚名。
下来后梁士诒才搞明白袁总督是真心搞改革,看重的是实用的本事,当即求见,这一次,他大谈财政、外交、铁路方面的心得,谈得头头是道,很对袁世凯的胃口,认定这确实是个人才,便奏请把他留了下来,后来任命他当了北洋书局总办,很受重用。
接下来梁士诒跟随议藏约全权大臣唐绍仪全程参与了和英国的谈判,并签订《续订藏议条约》,确认了中国对西藏的领土主权。1905年12月,袁世凯任命他为直隶铁路总文案。第二年10月,清廷设立邮传部,梁士诒接管了铁路那一摊,并于后来出任五路提调处提调,主管京汉、沪宁、道清、正太、汴洛五条铁路的事宜。
上任之后,梁士诒大刀阔斧,先是设立交通银行独立筹款以避免过于依赖借外债,继而改五路提调处为铁路总局,自任局长兼交通银行帮理。就在这个时候,袁世凯把赎回京汉铁路的事儿交给了他。
赎路需要钱,梁士诒自有筹款办法:商借外债,发行公债,借用交通银行的存款。就这么三下五除二,京汉铁路还真就给赎了回来。
铁路刚赎回来,有一批官派留学生毕业回国了,照例这些学生要到军机处,接受各位重臣的考察,其实也就是大家照个面,以示朝廷对留学生的重视。
学生们拜见军机大臣,就像军机大臣见太后、皇上一样,都要磕头行礼。奕劻、张之洞他们心知这只是走个形式,也就不太在意,大大咧咧地坐在那里受礼,悠然自得。只有袁世凯,学生们磕头的时候,他居然站起来鞠躬还礼,表现得相当谦虚。这样整个接见仪式下来,袁宫保礼贤下士已满城皆知。
其实袁世凯也不完全是做作,礼贤下士本来就是他笼络人的一种手段,在没有利益冲突的前提下,上至七旬老妪,下自三岁幼女,他都客气得很。
比如刚来北京就任军机大臣的时候,袁世凯不辞辛劳挨家挨户地拜访了在慈禧面前说得起话的王公大臣,在拜访总管内务府大臣增崇的时候,增总管让年幼的儿子察存耆来给客人行礼。小察刚叫一声“大爷”,一个安还没请完,袁世凯早已起身离座,趋前几步给小孩子还了个安,还连说“不敢不敢”。
这就客气得有点过了,搞得增崇很尴尬,忙说:“小孩子家,袁中堂太客气了!”哪知袁世凯还没完,拉着小察的手连声夸奖:“老弟好!老弟好!”然后又侧着脸对增崇说:“老弟真英俊,真英俊!”
增崇也算慈禧面前的红人,家里座上客常满、樽中酒不空,哪位高官没来过?所以小察年纪虽小,见的可不少,像王文韶、鹿传霖等,他都给请过安,而这些家伙,最多冲他拱拱手就算答礼,从来就没人站起来过,更别说还礼了。
不用说,袁世凯的谦卑让小察大为感动,接下来回答问题也就极其认真,当被问到读书之事时,小察回道:“为将来考学堂,目前正预备学堂的各门功课,现用的教科书,只是上海文明书局出版的几种,似是有点不足。”袁世凯一听,想都不想就说:“明天我给你送些来。”
于是第二天增崇家院子里就多了五口大箱子,箱子里全是天文、地理、政治、经济、教育、兵法、法律、伦理、哲学、音乐等方面的新书,教科书更是应有尽有。所有的书,都是由京师大学堂编辑,直隶或湖北官书局出版发行,原装正品,绝无盗版。当朝一品军机大臣百忙之中居然能记得这等小事,父子俩顿时感动得说不出话来。
对小孩子尚且如此,其他更不用说。袁世凯从当直隶总督起,对待朝廷里的官员就像春天般的温暖,这些官员,无论三节两寿还是婚丧嫁娶,总是能收到他数目可观的红包,多年如一日,从不间断。当然,用的都是北洋的公款,而买来的,则是除政敌之外众口一词的“袁宫保不错”之类的由衷赞美。
人心都是肉长的,大家也不会光吃人不吐骨头,所以当袁世凯50岁大寿将要到来的时候,整个官场早已闻风而动,都想着要好好为他热闹一回。
就在这个时候,朝廷有了大动作,在查禁了梁启超发起的立宪派政治团体政闻社之后仅半个月,即以慈禧太后的名义,于8月27日颁布了为立宪而准备的《钦定宪法大纲》。
《钦定宪法大纲》由宪政编查馆参照1889年《日本帝国宪法》制定,但删除了其中有关限制君权的条款。大纲共计23条,分为“君上大权”14条和附则“臣民权利义务”9条,开宗明义地规定:“大清皇帝统治大清帝国万世一系,永永尊戴”;“君上神圣尊严,不可侵犯”。
君上大权当然不止这些虚的,大纲另有规定,皇帝有权颁布法律、发交议案、召集及解散议会、设官制禄、黜陟百司、编订军制、统帅陆海军、宣战媾和及订立条约、宣告戒严、爵赏恩赦、总揽司法权与在紧急情况下发布代法律之诏令。并且“用人之权”、“国交之事”、“一切军事”尽皆操之于君上,议院不得干预。
如此大权集于一身,皇帝和以前没有任何区别。至于臣民,则有履行纳税、当兵、遵纪守法的义务。
除此之外,臣民也有收获,比如大纲规定,“臣民于法律范围以内,所有言论、著作、出版及集会、结社等事,均准其自由”;“臣民非按照法律所定,不加以逮捕、监禁、处罚”等等,甚至于臣民还有当官或当选议员的权利。
当然,有没有这个大纲,臣民都有过生日的权利,而袁世凯的生日,马上就要到了。
袁世凯50岁生日,慈禧太后赐寿并赏了无量寿佛、金佛各两尊,以及寿字、如意、蟒衣、御酒等物,非常风光。
袁世凯此时住在锡拉胡同19号,这个地方,现在是一座幼儿园。锡拉胡同位于王府井附近的东华门大街东面、东安门大街北侧,因为上朝方便,有不少大臣住在这里,比如军机处的同事鹿传霖家就离袁宅不远。
1908年9月15日,农历八月二十,是袁世凯五十大寿的日子,锡拉胡同19号贺客盈门,据《泰晤士报》记者莫理循记载,大街上停满马车,军警沿途站岗,整个19号大院,从各个客厅到外面的走廊,从前院到后院,密密麻麻挤满了官员,几乎囊括了北京的所有权贵,总数当在1000人左右。
最尊贵的客人当然是庆王奕劻。庆王爷给足了袁世凯面子,不仅送了重礼,而且在礼单的落款处只写了“奕劻”二字,有意不提其王爷的身份,以示彼此交情的不同。载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直接在他的礼单落款上写了“盟弟”二字,一点都没有想要避嫌。
奕劻父子尚且是如此的态度,其他人就更不消说,比如直隶总督杨士骧,自感受恩深重,在致送的寿序中,竟自称“受业”,这是赤裸裸拜师门的表示,着实谦恭得可以。
以当时的习俗,像这种大庆典,若要排场到位,一场上档次的堂会是必不可少的。而堂会是否上档次,关键是要看角儿,戏提调就显得至关重要。这有现成的人,就是体仁阁大学士那桐,他是奕劻贪腐集团的核心人物之一,和袁世凯交情极好。
那桐和端方、荣庆一起,并称“旗下三才子”,他才有多大搞不清楚,贪财却贪得实实在在,什么钱都敢收。不过贪虽贪,他也有个可取之处,就是不装纯洁,还敢于自嘲——那桐曾自喻为“失节的寡妇”,既然已经无节可守,那么像什么卖身呀、偷汉子之类的勾当就毫不在乎了。
那桐属于能挣会花型,生活极为豪奢,其府第称作“那家花园”,占了半条金鱼胡同,面积足有20多亩,其中的一部分,就是现在王府饭店对面的和平饭店,绝对属于寸土寸金的地界。
毫无疑问那中堂是标准的成功男人。在咱们中国,自古以来成功男人的一大特点就是虽然家很豪华,但却不爱回家。那中堂自然也不能免俗,老爱往外跑,最爱去的地方,就是八大胡同。
那中堂是官场上的称呼,八大胡同的姑娘没人这么叫他,她们当面都亲切地称这个豪客为“小那”。小那高兴的时候,在胡同里一掷千金眼睛都不眨一下,很有英雄气概。
另一个爱好花销更大,那就是听戏。事实上,那中堂根本就是梨园界的一大护法。当时所有的名角,别人那里往往奉为偶像,而在那中堂这里,无非也就是些招之即来挥之即去的角色。当然,戏子们和八大胡同的姑娘还是有所不同的——他们不敢管那中堂叫小那。那桐倒是不摆谱,和艺人们相处得非常融洽,不仅堂会上打赏,逢年过节的还发红包,堪称模范衣食父母。艺人们提起那中堂,无不肃然起敬。
因此那桐这个戏提调干起来自是得心应手,但即使这样,还是遇到了点小麻烦。
当时最红的艺人叫谭鑫培,人称谭老板,又名小叫天,属于人民艺术家级别的京剧演员,谱极大,从来都只唱一出戏。因为是给袁世凯助兴,那桐分外卖力,想给他来个惊喜,便亲自来到谭家,希望谭老板这一次能破例唱两出。熟不拘礼的缘故,谭老板开了个玩笑,说中堂你给我请个安,我就答应。话音刚落,那桐就弯腰请了个安,搞得谭老板很不好意思。
可惜袁世凯对京剧兴趣不大,堂会办得非同一般的惊艳,他也只是感觉得意而已,反而觉得张之洞手书的那副寿联更有意义。寿联写的是:
朝有王商威九泽,
寿如召奭佐重光。
此寿联的意义不在于是否字字珠玑,而是其出自张之洞之手。袁世凯、张之洞同入军机,但两人来往并不密切,这主要是因为探花出身的张中堂,从骨子里根本就看不起没进过学的袁中堂,这让袁世凯相当郁闷。
郁闷的原因很简单,袁世凯其实也未必就很看得上张之洞,但是他虽然羽翼广泛,朋友众多,可同时政敌也多如牛毛,其中不少是清议。老袁很希望扩大自己的阵营,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而张之洞久负士林之望,很早以前就是公认的清流领袖,如果能赢得他的友谊,那么以后清议们再攻击起自己来,至少会多一层顾虑。
另外,论起势力,张之洞也委实不小,他在南边经营多年,门生故旧遍天下,其南洋系虽不足以与北洋系分庭抗礼,但因为得到了醇亲王载沣、肃亲王善耆、军机大臣鹿传霖、陆军部尚书铁良等朝中实力派的支持,真要和袁世凯对抗起来,也绝对不会落下风。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则是,当此满人排汉的关口,多一个像张之洞这样德高望重的军机盟友殊为重要。因为此,从两人开始共事那天起,袁中堂就费尽心机努力迎合张中堂,一开始成效并不显著,好在精诚所至金石为开,慢慢地张之洞开始有所转变,前些日子两人联手举荐蔡乃煌,让他当上了顶级肥差、官称苏松太道的上海道台,而现在张之洞又送来如此一副寿联,对袁世凯来说确实是个很大的安慰。
可是人生无常,袁世凯五十大寿风光过后,立马就被参了一本。
大概是树大招风的缘故,一直以来,参他的人就很多,当上军机大臣之后,这个局面并未有所缓解。率先发难的是张之洞的心腹、湖北按察使梁鼎芬,参劾他勾结奕劻把持朝政。接下来参劾的奏片源源不断,就连老淮军系统的直隶提督马玉昆都上了折子,只是因为大家都缺少充分的证据,虽然义愤填膺,却并不能真正打动慈禧太后。
但这一次不同,御史江春霖的参劾来得很猛,指责袁世凯以祝寿为名,广收财物,除结党营私等老生常谈之外,他还找到了一个很好的题目,就是袁世凯作为一个汉人,居然敢跟载振这样的宗室亲贵结拜兄弟,有违祖制,绝对不可容忍。
这个帽子太大,慈禧不能不有所反应。她还是很给袁世凯面子,没有公开此事,只是把他召到宫里训斥了一顿。袁世凯吓得不轻,谢罪出宫之后,惊慌失措间,居然在台阶上重重地摔了一跤,这下子,小时候因坠马而落下的足疾从此就加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