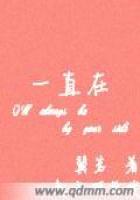听着方太傅提起此事,他眼里掠过一丝光亮,很快地消失,像是从来都没有出现过一样,“启刚在骁骑营里能谋得一位,已经是官家的隆恩,惟有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才能报答官家对我们护国将军府的隆恩。”
他应对得体,几乎做到滴水不漏,也不问方太傅上护国将军府来所谓何事,更不问那为何方府的厚礼几乎堵住门前的一条街,都不问,就是不想让方太傅把话题给引出来。
然而,他还是个年轻的,终不如方太傅阅历深厚,闻言,颇有深意地一笑,“老夫听闻小将军还有位未曾出嫁的姑姑?”
话终于到这份上,落在陈启刚的面上,不得不回。
陈启刚经过母亲张氏的提点,早已经对此事有所准备,以至于一直没让方太傅引出话题来,他小心翼翼地防着,忽听着方太傅已经直接地提将出来,只得硬头发相回。
“大人,启刚的姑姑确实未曾出嫁,早已经不是豆蔻年华……”
他的话说到这里,就见着方太傅微摇头,那个样子仿佛在告诉他,此事早已经知道,“老夫为着慎儿也只得豁出这张老脸来,冒失地前来,不知道以我们方家的门第是不是配得上小将军的姑姑?”
到最后,话已经说得很明白,说的已经是不是门第,他已经在说明白一件事,他的儿子完全配得上他们护国将军府的嫡女。
这话是对的,没有一丝错处,陈启刚不得不承认,当今太傅的公子,姑姑嫁过去,还是高攀的,且不说姑姑年纪这么大,就是如今他虽顶着个“护国公”的名头,护国将军满门忠烈又是如何,终已经是日落西山。
可……
方太傅家的慎儿,方慎,京中人皆知,虽是年已十八,心智如稚童般,这样的人能升任为人夫之大任吗?至于别人家的女儿要嫁给方慎,陈启刚怕是眼皮也不抬,这与他们何干。可现在,方太傅这个态度,就是想替方慎求娶自家姑姑。
他们护国将军府的嫡女,虽是年已有二十有二,可也不至于沧落到得嫁那样的人,他不是没有抗拒的,“只是怕我家姑姑自小生活在峨嵋山,礼数并不周全,怕冒犯了太傅大人的公子,也是配不上太傅大人的公子。”
即使他觉得身为护国将军府的一份子是他们的荣耀,在这样的事面前,不得不低下骄傲的头,把自家的姑姑往泥里贬去,以期得这门婚事不会成事,以至于话说到后面,他那张方正的脸硬是挤出几许羞惭的神色来。
“小将军这是哪里说的话。”方太傅那个是四两拨千斤,指节轻敲着桌面,发出清脆的声响,“护国将军府里的嫡女,哪里是普通姑娘家给比的,蒙官家的厚恩,太后娘娘的厚爱,老夫带着慎儿入宫,官家还问及慎儿的婚事,老夫到还来不及说话,慎儿早已经在官家的面前,口口声声地喊着‘姐姐’……”
陈启刚正听着,话到要紧处,竟是让方太傅给收住,他不由得抬眼望向方太傅,见他的脸,已经褪去初时的温和,神情已经多了些冷淡的意味。
他昨天是新郎官,压根儿不知道秋娘所做的事,也没有人把这事同他说起,毕竟那事就仅仅着秋娘、张氏,还有李管家知晓,这种事儿,也不好明说出来,一说出来,有碍秋娘的名节。
他纵是已经猜出来那方家公子嘴里喊的“姐姐”可能是自家姑姑,却是按振住焦急的心,坐在那里,没有主动地追问下去,便想扯开话题去,“今年的海棠花开得正好,不知太傅大人可有……”兴致去看看?
“小将军的心意,老夫领了。”方太傅显出他的强势来,把他的话毫不留情面地打断,眼底微沉,“小将军不想听听慎儿下面说了还说了什么话吗?”
“府上公子说的话,启刚不知。”陈启刚不想猜,没那个兴致,淡淡地回答,一派不好奇、不纠结的模样,“请恕启刚愚钝。”
然而方太傅前来,事情没有如他的愿,哪里会这么轻易地就放下去,自是把话儿给提出来,“官家问慎儿嘴里的‘姐姐’是谁,老夫迫于无奈才只得替慎儿说出他昨天睡在小将军姑姑房里的事……”
“请太傅大人自重!”陈启刚坐不住,“腾”地站起来,硬是克制住脾气,生硬地说道,“我家姑姑还未出阁,大人口出此言,岂不是伤我家姑姑的名誉,我陈家虽是武人出身,可也是识书知礼的,还请大人在官家面前澄清此事,我家姑姑断然不可能做出如此轻狂之事!”
他嘴里说得义正言辞,面上通红,似因着这些话而微微恼怒,心里到是不能一口咬定自家姑姑没做那样的事,毕竟,姑姑与一般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大家闺秀有所差距,这样的事,他心里没个准儿。
但,他们护国将军府上下都是极为护短的人,不管是有没有这个事,就算是有,也不能让姑姑嫁给方慎那样的人,这事儿,只能暗地里消弭,却不得传扬出去。万一,真传出去,这败坏名誉的不只姑姑一人,连带着护国将军府也是难逃另眼相待的!
“小将军,别激动。”方太傅仿佛早料到他的激动,面上一点儿多余的表情都没有,弧度刚好,显得是个极温和的长辈,“官家特命老夫前来送上聘礼……”
陈启刚猛然间起身,又觉得自己太过于失态,缓缓地坐回去,竭力地让他自己保持着心平气和,但心里早已如刚开的热水,沸腾得让他有些不知所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