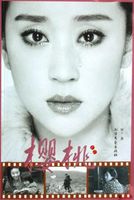那只漂亮的鸟儿是别人送他的,叫鹦鹉。
当时,那鸟儿见到他就挪着两只脚,好像向他致敬——局长好,局长好!他很高兴,说,好,好,好。
其实,他并不是局长,只是个副职而已,很管事的。来人看他很高兴,瞅着他的脸说,那事儿……
过后才知道,那鸟儿是个通人性且会说人话的尤物。收到这礼物,最兴奋的莫过于妻子。也许是更年期的缘故,妻子对任何人都存有疑心和戒心,却对这只鸟儿友爱有加,天天陪着它说这说那,都是些私房话,有的连自己的丈夫也不曾听到过。
经过妻子的调教和训练,鹦鹉大有长进,不但会礼貌用语,还会见啥人说啥话,且都是三个字。见是胳肢窝夹着皮包的,就说,放下吧,放下吧!人走时,就说,领导好,领导好!人家要走了,它必定送到门外,连声说,您走好,您走好!
去过他家的人,都夸这只鹦鹉是个鸟儿精——跟着啥入学啥人。
鸟儿精也有弄错的时候,但很少。有一次,来了一个年轻的女士谈事,恰好夫人进了卫生间,那鸟儿便欢叫道,包二奶,包二奶!
一听这,夫人放下急事,提着裤子出来了,脸上挂着怒色,双目圆睁,对着那位女士喊,原来就是你啊!
你瞎嚷嚷个啥!丈夫按住火,压低声音,人家是来说事的……
说事咋不到办公室说去!
那女士满脸通红,提起包就走。夫妻俩眼瞪眼地看,就听鹦鹉响亮的声音在屋里回荡,下次来,下次来……
他气得骂道,下次来你奶奶个头!上前就要拧那鸟儿,吓得那尤物翅膀乱扇。夫人慌忙横身挡住,眼角一挑给了他一个警告,你在它身上出啥气——有气给我耍!
都是你调教的好!
它没来咱家之前啥都懂,还用我调教吗?
有了这句话,多年来他第一次很认真地多看了妻子两眼,捎带着分给鹦鹉一点。这一切,都是在无声中完成的,也是在无声中塌落下去的。于是,出口的声音便软了下来,是的,是的……
春节过后,一种叫非典型性肺炎的疫病开始蔓延,又叫SARs。那天,市里召开防治“非典”紧急会议,要求很严,还宣布了纪律。会后,他应邀到一个星级宾馆吃饭。刚到大厅,一张张笑脸便把他包围了。他也笑了,问,这“非典”怪厉害吗?
“非典”不是不典型的肺炎吗?好治,咱该吃的吃,该喝的喝,有事别往心里搁。
交怀换盏之间,忘了灯外之天。酒后又是洗澡又是按摩,要多舒服有多舒服。到家后已是夜半时分。一进屋,有个声音便说,非典型,非典型!
他很兴奋,学着说非典型,非典型……、那声音说一句,他也说一句,就这样一递一句地交流,像是遇到知已一般。屋子里散落的音符怪怪的。
第二天早上,有电话打进来,先是笑语,后是严厉。听着电话,他还看着那鹦鹉。那鸟儿勾着头说,非典型,非典型……
它勾头的姿势极像他的夫人。他心里就想,这家伙啥都知道,便忘了电话那端。
其实,昨夜他在洗澡按摩时已出事了:一个从重疫区回来的打工者被专家确诊为SARS病人——这是本市第一例。
当时,许多人找他,因为他是值班负责人。找不着他,便往上汇报。
非常时期不是平常,许多人成夜不眠。这不眠之夜就有了非常故事:立即将他免职!
电话里,他还以为是笑话,便把笑话送给鹦鹉,领导好,领导好……
那尤物还是重复那句,非典型,非典型……
奶奶的,这家伙傻了,就会说这一句。
在近旁的夫人已听出些眉目,抛出一个冷眼,它不傻,是你傻了!
待他问清楚事由,身子忽地酥了。猛地将鹦鹉扯到地上,一脚踹过去,并没有踹到。还是老婆动作麻利,只一脚,便将那鸟儿踢飞,恨恨地道,你就是SARs——看我杀死你!
那鸟儿抖抖乱毛,歪着头还是说,非典型,非典型。
他惨惨地笑了几声,扑地做鸟儿状,两臂扇动,膝行如龟,渐与鸟儿近,头一低,磕了个响头——再给我一次机会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