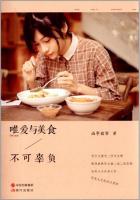难忘故乡的石拱桥。
那是一座典型的传统石拱桥,用青色的条石砌成。石拱桥的两边有石廊。粗重的石柱、宽大的石扇,以隼卯结构连接起来,上面雕刻着龙凤、花草图案,形成与桥身浑然一体的青色石廊。石拱桥谈不上宏伟壮观,约摸十多米长,七八米宽,静静地架在一条小溪上。远远望去,石拱桥与小溪之间形成的空间,好像半个月亮,静静地浮在蓝幽幽的水面上。因为村里小学的教室不够,我所在的班级先后到两个相邻村的小学去借读,每天上学和放学都要经过石拱桥。它就像一个美丽的童话,点燃我幼小心灵里无数灿烂的火花。
这条溪流源自两里开外的水口庙水库,那是上世纪五十年代大跃进时期人山人海战天斗地的产物。因为父亲和母亲就是在新婚不久作为移民离开那个已经被淹没的小山村的,所以我对它有着难以泯灭的印象。正是因为水库要发挥灌溉的作用,这条其实是自然水渠的小溪也就担当起浇灌几千亩田垄的使命。这座石拱桥是连接南北几个村庄的咽喉,它究竟在水库修建之前就已经建成,还是在水库修建之后建设的,我没有去考证。但从它近乎苍老的身姿来看,我估计年代比较久远,应该有上百年的历史了吧?!
说它的历史久远,其实从桥身并看不出什么端倪来。桥南侧那棵老槐树似乎在倾诉着什么。那是一棵写满沧桑的古树。树干需三人伸展双手才能合围,树皮已经全部掉光,深褐色的树干上满是疙瘩,好似沧桑老人脸上的褐斑。拱桥不远处是稠密的村落,那是拥有上百年历史的古建筑群,白墙青瓦,檐角高翘,远远望去,就像一幅水墨画。在远处青山和近处田野的陪衬下,古老的村庄透露着鲜活之气。老槐树的树冠稀疏,好像一个老头的秃顶,几根历历可数的枝条,散乱地向天空伸展开来。太阳透过树冠,像经过筛子似的,在地面形成斑斑驳驳、疏疏密密的亮点。据说乡里的几个老木匠为了防止老槐树成精,用长长的铁钉密密麻麻地绕树干钉了一圈,我曾经隐隐约约地看到那些老木匠锈迹斑斑的愿望。
小时候的我一直觉得石拱桥神秘莫测。它全是用厚重的石头砌起来的,怎么能够支撑得起来,并且上面还要过人、通车?怀着这些疑问的我,好久不敢跟小伙伴们一起去桥下戏水玩耍,我总是担心石拱桥哪一天说垮就会垮。后来,做泥工的父亲给我讲解了石拱桥的建筑力学原理,我听得似懂非懂,但终于相信它不会轻易垮下来,也就战战兢兢,继而大模大样地跟小伙伴们一起,在石拱桥下尽情地嬉闹着童年的时光。
一到夏天,石拱桥就格外热闹。桥下是清清的溪水,偌大的桥面挡住了毒辣辣的太阳,穿堂风在拱形的桥下恣意穿梭,给这个阴翳的空间足够的静逸和清凉。大人和小孩在劳动的间隙里偷偷来到这里,享受着炎热季节里特有的凉爽。许许多多女人在那里漂洗衣服、被子,她们张家长李家短的说笑声,荤段子引起的嬉戏笑骂声,和此起彼伏的棒槌声,随着潺潺的溪水悠悠远去。小孩子们挽起裤腿,站在水中,相互泼水取乐。有的干脆脱光衣裤,把整个身子浸在浅浅的溪水里,尽情地游泳、潜水,使劲舞动双腿,溅起水花。水花溅到哪个正在洗衣的女人身上,她就会霍地站起来,大声训斥:那是哪个屋里的细伢子,我等下去告诉你妈妈,打肿你的小屁股!
如今,石拱桥上的土路已经变成一条水泥路,许多人家都在自家的院子里打了水井,很少有人拿着衣服来桥下洗了。老槐树的枝条越来越少,但它还静静地站在那里,似乎在等待着什么。
(原载2011年1月31日《中国国土资源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