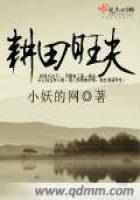“小爷,你这里……客人一定很多吧?生意一定很兴隆吧?”
小伙计差点要大笑了:“这关你这个要饭的啥事啊?难不成,你也要开个茶店?”
“小爷笑话小的了,连饭都吃不上,还开茶店?”
“走走走,小爷没空跟你废话。”
叫花子不再多嘴,跌跌撞撞地往外走,走出好大一截路了,他竟然往屋后走去。茶亭的后面,是两溜供客人歇脚的平房,还有一溜马厩。
“喂,你上那后头去干啥?难不成,想偷马啊?”站在门槛上,小伙什就像个指挥千军万马的将军,气吞山河地比划道。
“那不是客人住的嘛?”
“是啊?咋的,你还想住进那里头去?你有银子吗你?哼,一个叫花子,连饭都吃不上,还想住店?做你的大头梦去吧。快走快走,别大半夜的搅了客人的好梦。”
没想到,那叫花子倏地转过身来,以小伙子都难及的速度冲到小伙什的身边,将一锭银子塞进小伙计的手心里,阴恻恻地说:“将你这里最好的屋子给爷腾出来。”
小伙什将银子咬在嘴边咬了咬,不错,是真货!
若不是看在真金白银的份上,小伙计要跳起来了。这个叫花子咋就在眨眼间变了?变成了一个爷了?
“最好的屋子?嘿嘿,对不起,天黑的时候被四位客人先租下了。”
“他们就那般了不得啊?有银子是不?爷出双倍的价钱,你让他们让出房来。”
真是人不可貌相,这个叫花子似乎是个财神爷。这样的主不好得罪,一旦将他气走了,老板娘决不会饶了自个的,说不定明儿一早真的叫自个卷铺盖滚蛋了。
小伙计将这辈子的笑容全堆在脸上了,说:“这位爷,这……这似乎有点不妥吧?那四位客人看上去也是极有身份的,我……我只是一个当伙计的,没那个胆啊……”
“有身份的,啥身份?有银子就是大爷!”那人又从一个鼓囊囊的破袋子里抓出一锭更大的银子,晃了晃:“看见了吧,这个最大,最有身份。”
月光,照在那人手中的银子上,晃花了小伙计的双眼。他盯着那个破袋子,心想,那里头难道装得全是银子?
“咋样,看清了吗?”
“对……对不住了这位爷,”小伙计吞了吞口水,朝屋后看了看,为难地说:“那四位客人早就住下了,叫人家起来……不……不好吧?要不,那四位客人的右边那间屋,也算是间上等的房,里头啥都有,也干净,爷上那间去委屈一夜?”
“哪间?你领爷去看看。”
“好来,爷请随小的来。”小伙计心花怒放,他自认为自个很机灵,最后还是将这个叫花子财神爷给招揽住下了。明儿老板娘知道,一定会赏自个的。
很快,小伙计将那人引到了方正他们住屋的隔壁。
打开门,点上灯,那人很仔细也很挑剔,看了半天,还附耳听了半天,不满地说了句:“这般嘈杂,让人如何安歇?还说有身份的客人,这等客人想必就是不入流的行脚客!”
木板壁不隔音,隔壁的打鼾声清晰地地传来过来。
小伙计只能好言讨好:“爷啊,您不知道,这隔壁的隔壁,住着他们口中的二少爷,那架势,那气度,不是盖的,一看就是个有身份的人……爷,您就委屈在这屋住一夜吧?明儿他们一走,小的就立马您换房。”
想必那人也累了乏了,将破袋子往床上一扔,打着哈欠道:“好了好啦,别噪聒了,你出去吧,爷要歇息了。”
生意终于做成了,小伙计欢天喜地地出去了。
第二天天亮,另一个小伙计栓根来接班,这个值了一夜班的小伙计还算尽职,他跑到客房去看看那位客人,心想,也许那叫花子财神爷看到自个如此殷勤,随手赏自个一锭银子也说不定。
在门外很小心地敲了敲,见没有动静,便轻轻地推门进去。
那叫花子财神爷却不见了。
床上空空如也,小伙计四处看了看,发现那个人似乎没往床上躺过,小毯子还是如白日般那样折叠着。
“这个叫花子财神爷好古怪。”听完,夏璃韵说道。
“卑职怀疑,那个叫花子财神很可能是送酥饼糕点的神秘人物。”
夏璃韵点了点头:“很有可能……这到底会是谁呢?”
“卑职听完小伙计的诉说,也曾上那间屋去细细地看了看,没发现有价值的线索。”
“假如能让我们随意地看出来,这人也不必装神弄鬼地跟在身后了。”
“娘娘言之有理。”
夏璃韵看了看窗外,说:“我们走吧,这个叫花子财神的真实意图和身份我们一时也弄不清楚,先搁着吧。到陵区还有五十多里地吧?趁着日头没出来尽早上路,否则太热了。”
“是,皇后娘娘……卑职把鸡也抱上。”方正转身离去。
一行人重新上路。
山里的清晨都带着雾,迷迷茫茫的,好像天地之间盖着一层银纱。朦胧中,沿路的草木都像一幅静止凝固的墨画,十分的静谧,且带着处子般秀美。马车,驰进了如网的晨雾中,好似一把剪子,粗鲁地将银网剪碎,驰过后,雾气又渐渐地合拢,重新组合成漫无边际的纱网……伸出手去,却抓回一手的湿意与舒爽。
答,答,答的马蹄声,撕碎了清晨的静寂,也惊飞了许多爱睡懒觉的动物们,看见它们飞快地跑进浓雾深处,夏璃韵深有同感地说:“对不起,搅了朋友们的好觉了,我知道被人吵起来的感觉是怎样的,所以,我跟你们保证啊,下不为例,下不为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