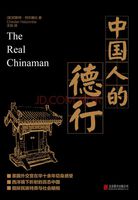1.岭南窗外的鸟鸣声巨大。
2.第一次这么清晰地看到了海浪的涌动。
3.我的新居被绿树、溪水、池塘、青草包围……
4.我和南疆小孩在一起。
飞机降落在深圳机场,潮热的暖风瞬间黏上鼻孔,南方味,迅疾包裹全身。
车启动,朝向东莞。窗外土壤和植被的颜色渐渐浓郁起来,在荔枝树丛后,陡然闪现出一片五彩的大酒店,我像刚行过成人礼的少年,亢奋起来,感觉的大门霍然敞开,浑身上下,每一根神经都警醒着,伸出无数触角,柔软敏锐。
不止一次,在珠三角,我仰望着这些高大的凸起物,如果没有它们,这里,便会兀自荒凉下去。白天,这些建筑物是锈的死物,冰冷僵硬,到了夜晚,诡秘的灯光,让它们浑身发烫,散发出骇人能量。有一次,在大巴上盹着,被车身一晃,睁开眼皮,我被逼向视网膜的水晶灯光震得无法呼吸:夜晚的东莞小镇,和香港,并无太大区别,灯光似烟花,永不熄灭。我甚而不能相信,我离这个魔幻世界的距离,如此接近。
南方于我,不仅仅是秦岭淮河以南,种植水稻,河流不结冰这个地理概念,而是一个巨大的生存场,一个隐秘而鲜活的边陲世界,一个暗潜着奋争、对抗和重生的疆域。我是凭着一种动物的本能,嗅到了那股混合味,便自己寻了过来。虽然我在这里没有度过少年、青年时代,而这里,也不是整个南方,不过是岭南一隅,但在那一刻——从机场走出,嗅到潮闷之味,看到荔枝树后的酒店灯光,无端亢奋起来时,我便确认下这样一个事实:这个尖锐之地,命中注定,它属于我。
出了十几本书后,我渐渐明白这样一个道理:写作,恐怕是世界上唯一越做越难做的行当。当年的一个中篇,坐三天,轻松完成;甚至,我还有过一天写十二首诗的巅峰期;可如今,写三百个字,我都要耗费很大劲。一遍遍想,一遍遍琢磨。在脑子里思忖许多遍后,让胚胎慢慢成形,再把它敲打下来。我在乌鲁木齐的写作,渐渐陷入瓶颈期。我知道,写作如晶体,早已沉淀在我的体内,即便我试图装作看不见,它,还在那里。表面上,我沉入琐事:做饭、洗衣、购物、娱乐;然而,作家的热血,却奔突在每一个细胞核内部。我陷落进荒岛的寂静,试图努力辨析出我的未来,像画家面对远景,不断移动画架,寻找最佳的着眼点,我不断问自己——是继续留在北方,还是移居别处?
当南方如钩子,从半空垂落,神使鬼差,我抓住了它。选择定居东莞后,我曾认识的某些文友,怀着嘲讽的兴味,揣测这个自命不凡的选择,到底能坚持多久。然而,连我自己都未曾料到,跨过南北界线后,我的文字,如汛期之鱼,陡然澎湃起来。我不明白在灵感和创作、直觉和理智间,有一个怎样的平衡杠杆在支撑;我亦无法修订这个衡量标准,我只是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去写,去写,不断地写,然后,再细心修改。我知道,当我在修改那些文字时,我同时,也在修改自己的命运。
我是在半山开始这场写作的:屋子是二手的,七十五平米,两居室,紧凑极了,其内,冰箱嗡嗡,窗帘陈旧,沙发凹陷,而我,居然在这个空间,为书桌找到了个向山的窗口。凌晨,在浓烈普洱茶的催化下,我以一种狂想诗文式的哲学方式,展开内心生活的探索。窗外,蝉叫蛙鸣,声波阵阵,鸟儿们,闪着翅膀,有时,会落在我的窗棂。
我惊诧地发现:一个人,不仅可以靠幻想创造出一个世界,甚而。还可以谋生。在小邮局,我兴冲冲地清点稿费单,盘算下个月的米、面、菜、水、电皆有了着落;而当我进入写作时,又会常常忘记稿费,而只思考一件事:如何让每一句话都更有效,让它们好得不可易一字,又节奏分明,音调铿锵。
是什么样的意志力,将我拴在书桌上,如头拉磨的驴,拖拽着整个世界一起旋转?我将自己关在小屋,从半夜写到凌晨,直至窗外的山脉,渐显曲线。然后,整个上午,继续写。午睡后,阅读。晚饭后跑步,仰望天空,那永恒的星体图案高悬头顶,我在心里默念,这一天,没有虚度。我消耗大量时间,盘桓在词语的交叉和重叠中。我不断调整思维,以便加入更新的内容。我全身心投入,渴望词语干净,冷如利刃。
在北方,我从未有过如此热情满怀的创作冲动。我出生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成长于农家,父母是文盲,小学一年级,我从学校带回的课本,是家里的第一本书。我吃过火柴烧烤的蚂蚱腿,新鲜的葡萄,青涩的西红柿,闻过雨滴砸在虚土后,腾空而起的味道,草灰埋入炉膛,烧出的锅盔(一种北方大饼)香。放学后,我奔跑在田野,听到风呼呼掠过耳畔,闻到韭菜被镰刀割断后,喷射出一股腥味。那些事物,至今仍完整地存储在我的体内,凝聚成一个隐秘内核。
我的家是北方常见的土坯房:厨房、父母居室、我的小屋、放农具和煤的屋、羊圈、菜窖、鸡圈。院里栽种着葡萄树,用木架撑到屋顶,将整个屋子裹起来。葡萄坑边种着苹果树、杏树和梨树。我非常孤独,一个人独自长大,没有和兄弟姐妹亲密相处的经验,更不善于斡旋和人群的关系。
最早说出“作家”这个词,是小学三年级,家里来了个卷发中年的远客,戴着厚眼镜,问我,你长大了想干什么?我坦然:当作家。从她惊诧的表情中,我明白了一件事:她认为,这是一个农村女孩的狂想,根本不可能实现。我的第一首诗是怎么开始的?是什么触发了它?我想我知道。那天午睡起来,抬头看窗外,葡萄半透明的翠绿色调,和浮动在阳光中雪白的苹果花瓣叠印,衬出一片浓重的蓝天,接着,花瓣被风吹拂,飘荡,垂落,解脱,形成花雨——这个瞬间让我震惊,像被魔杖轻敲了下脑壳。诗歌的光芒,就这样,通过曲折而精妙的途径,照临了我。
十五岁半,整个暑假,我坐在葡萄架下的那间小屋,在方格纸上写作,待上了高一,到了新班级,四万字的中篇小说《哦,玫瑰》,已变成铅字。我写一群中学生,搞了个文学社,他们和教师的矛盾,他们之间懵懂的恋情,而那时的我,还从未尝试过异性之恋。我沉浸在摆弄词语的劳作中,希望通过我的组合,比此前,更光彩夺目。这种新游戏,于我,不仅仅是情感表达,更是某种冒险和抵抗,而我从中获得的快感,因为神秘,难以对别人细说。
新疆,中国西北偏北;哈密小城,四周被戈壁沙漠环抱;我的父母,从甘肃逃荒而来,侍弄一亩五分菜地,希望西北风不要刮得太猛,不要将暖棚上的塑料都吹烂;我们生活在没有祠堂、没有族谱、没有亲戚的小村,村民是众多迁徙者为奔命,临时凑在一起的难民。
说白了,我是难民之女;我又拖着我的孩子,迁徙到南部偏南。这样的我,居然,想当……作家。贫穷而傲气,并非不聪明,又桀骜,这些特征,只能使我的前途更加黯淡。
在我青春期的成长阶段,我从未偏离过这个梦想。虽然我在学校里接受的教育是粗浅的,但我利用各种时间阅读,积累技能,让手指具有黏合力,唤醒各类词语,让它们围绕着思维,编织出一幅智力彩锦。成年后,我力图不仅遵守女人应履行的职责,且装作对它感兴趣,然而,我却不能全身心投入——我宁愿写作。我是主妇,可我日日夜夜,苦思冥想的,却是试图将作家这个最神秘、最孤独的职业坚持到底。我渴望飞奔在词语里,以超越狭窄的卧室,琐碎的厨房,四方四正的客厅,而到达大江、大海、湖泊、山岗。
定居小镇后,我慢慢发现,有三个南方重叠混杂。第一个南方属于原住民。他们从没见过雪,肌肤里闪烁着的黑,如矿物质深埋地层后,又被重新挖掘,他们习惯各种风雨虫蛇,坚韧胆大,又尽量回避外人的目光,而以沉默固守着某种祠堂里的戒律,让某种稳定性,得以延续。本地人的宽容,不仅是天性,而且是必须:这里必须要保持宽容,否则,一点点小事,都会演化成群体性的爆炸事件。
第二个南方属于打工族。打工者浩浩荡荡,直奔那个目标:工作机会。他们拎着编织袋,装着被子、枕头、凉席,拎着桶,装着牙具、毛巾、拖鞋,跳上公交车,目光从大王椰和棕榈的树梢上掠过,搜寻着招工信息。他们人数众多,流动性强,相互之间的联系,远胜于本地人。数字报告在不断变化——几乎是刚刚算清,情况又变了——总有打工者涌入,而南方的一个神秘特点是,它总有本事,派发给不同人以各种暧昧的礼品,它总在上演被摧毁或被成全的奇迹。
春节期间,若在珠三角转悠,会惊诧发现,那些原本喧嚣的高大厂房,变得死寂,像巨大的休止符,整个海滨如空落蜂巢,甚而像囚犯越狱后的监牢。而在正月十五后,宿舍里的灯,一格格亮起来,逐渐地,形成一片璀璨。傍晚,穿工装的女人,懒得脱掉那衣服,纷拥而出,簇拥上街。若要去寻找她们中的一个,便要盯牢她的面孔,否则,她便会在瞬间消失,像她在这条街和这些厂房里,曾消耗的那些时间般,变得不复存在。第三个南方属于迁居者。人类的探险基因,曾存在于哥伦布等人的身上,同样,也遗存于这些人身上。工业革命的火种,点燃了这些沉睡基因。轰隆隆的流水线,不仅消解了传统的牧业和农业的生产方式,同时,还颠覆了旧有的生活方式,让人们得以在相对自由的范围内,寻找另一个生存场。而南方的魅力,让西部和北部,望尘莫及:摩天大厦拔地而起,厂房鳞次栉比,高架桥盘旋如巨蟒,农田被挤成魔方,商品迅速流通,大排档通宵营业,彻夜不灭的灯光,将楼房托举成一束礼花。迁居者不断增加,如大剂量维他命补充进来,点燃着南方的热情,维持着此地的高速运转,让南方,形成某种独特的、国际化的、特殊的气场。
从西北到东南,在别人习以为常、习焉不察的环境里,我看到了陌生与惊诧。而陌生化,不一定就是新奇,总令人愉悦,有时,它甚至是危险的。常常,我会感觉自己冒犯了某种界限,而这种跨界的行为,又逼迫着我,放弃以往靠幻想的写作,而更喜欢真实的故事、真实的人物、真实的场景。这种做法,不啻为一种令人生畏的挑战:如从现实的秃鹫嘴里,抢夺回滴血的鲜肉。
必须深入到小镇的隐秘角落,才能从最平凡的东西中,发现文学意义……于是,我套上工衣坐在拉线上、啤机前干活,一天十一个小时。于是,手指烂了,体虚,晕厥,而从不后悔;于是,我去买馒头,拎着塑料袋不走,看主妇们如何吵架;于是,我的脸上涂着面膜,躺在帘子后,听化妆店女子聊天,心跳如炸雷;于是,我伫立棕榈树下,看小狗背后的靓女,靓女背后的男人。
我只写自己看到的、听到的、感受到的事物,那些没有物理基础,在半空中飘荡的风花雪月,被我摒弃;一切毛糙的,尚未定论的、正在突进的细节,都令我好奇,通过对切片的描述,我加深了自己与世界的紧贴感;我让自己成为熟练工,让词语变成钉子、螺丝、插销、暗扣,最终,完成一个物件。
我总是急匆匆赶回家,坐在一米宽的书桌前,掀开电脑,啜口茶,大脑里像插上根看不见的电线,嗡嗡运转。敲打键盘时,我能听到大脑和电脑,在同时嗡嗡响。我努力确认那曾真切生发的情感还醒着,然而,遗忘无法阻止,真相永不存在,因为,时间不会为任何曾经的快乐或悲愤停留片刻,我们听任自己随波逐流,将身躯塞入另一个空间,腐蚀掉储存于时间中的情感,在当时,它们甚至以咆哮的方式捶打过胸膛,而现在,却蒙上层灰色的面纱。
我实在匮乏幻想才能,等我迁居南方,某天清晨,伫立阳台,面对青葱宝山,终于顿悟:属于我的题材,就是我自己——作为父母从内地迁居边疆的孩子,当我再次迁居后,所经历的一切遭遇和努力。
是的——我并没有说出我所知道的全部。像一个穿过黑夜的人,他只说太阳散发着光芒多么温暖,而回避着那些阴冷、惊悚和凄惨。我将我的疼痛,压缩进我的词语中,而只在嘴角,挂一个淡淡的微笑。我将自己的一半折叠起来,而只展示出另一半。我写下了我所看到的南方,那么具体细致,然而,另一种对北方的痛楚,却藏在这些词语背后。
到达南方,应是我这一生中最大的波动,而在这里诞生的文字,绝不仅仅是手指敲打键盘的简单运动,它还与南方特殊的气压、气温、降雨量、空气中负氧离子的含量、房价高低、邻里间的友善程度有关,以及与矿物圈、水圈、大气圈、营养圈等更为复杂的因素有关。
定居樟木头后,我惊诧地发现,还有很多作家,因各种机缘,也迁居于此。
在“大量招收女工”的红色横幅下,在厢式货车鲨鱼般纵横穿梭的莞樟路上,在茅草丛生的五星级酒店旁,经常会走过一个零落的人,两手空空,眼里闪着灵光,像是无所事事,又像是所有的事都和他持有某种深切的关系。我看见那个人就是我,或别的作家。我们不是旅行、采风、疗养,而是……居住。我们,成为小镇最古怪的居民,每个人都像个探险者,用好奇的目光打量南方,每一个人所散发的光和热,都超过爱迪生联合公司,而小镇的文化系数,也因我们的存在,大大超过周边的平均值。
逐渐地,我们习惯了芒果树荔枝树,尝得出五指毛桃汤的浓淡,分得清妃子笑和桂味(荔枝的两个品种)的甜酸,对潮湿,对蚊子,对老鼠个头能膨胀到何等庞大的地步,都有了深切体味。我们离开了故乡,在这里形成了一个特殊的场域,过上了某种奇特的生活,这个现象,按经济学家、社会学家和评论家的综合分析:若早上三年五年,断不会在中国诞生。
在户籍制如铁链紧紧拴住脚踝的年代,迁徙的狂想,只能被扼杀在摇篮中;随着工厂的出现,政策的松动,南方如冰河解冻,陡然间,澎湃起来。人们来到此地,节奏变了,性情也变了,所做的努力,似乎都会遭到翻番的回报,即便同时,也会遭遇挫折和麻烦,但却不能不激越向前,因为他被周边环境所挟裹,不得不如落叶在溪水,一同载浮载沉。
故乡于我们,究竟是何物?它竟成了我们挥之不去的口味、习惯、风俗、礼仪和伤痛?!当我们的身体离开故乡,故乡并不会心甘情愿地退场,它总会在某个时候,露出藤蔓上的尖刺,让我们痛一下。我们必须承认,故乡对我们的意义重大,它不仅仅是面条和口音,不仅仅是肤色和习性,它将我们与过去相连,又把我们输送到未来,我们后来所收获的一切,都是从故乡这个母体里汲取养料的。
然而,离开却是必然。是在樟木头,我最正式,又最隐秘的形象——作家的形象——逐渐清晰起来。
我写下可怕的人群,无序的混乱,让一切显露原形的阳光,正在晾晒的衣服,电子厂外的小吃街,破街陋巷里的出租屋,我写下挣扎和热望,失落和忧伤,它们是别人的,也是我自己的,伴随着写作的深入,我感觉自己的命运已和南方的命运,紧紧地夹缠起来。
二0一0年八月至二0一三年四月于东莞樟木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