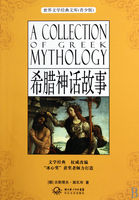格杰奥诺夫斯基跟瓦尔瓦拉·巴夫罗芙娜并肩而坐;她一路上寻他的开心,仿佛无意地把她的小脚尖儿放在他的脚上;他实在难为情,便对她恭维几句;她哧哧地笑着,当路灯的光线照到车里时,还对他做几个媚眼。她自己方才弹过的华尔兹舞曲仍在她头脑中回响,令她春心动荡;她无论身在何处,只要一想起灯光、舞池、音乐伴奏下急速的旋转——她的心便会火一般地燃烧,眼睛闪出奇异的光彩,微笑也会徘徊在唇边,某种优雅而狂热的东西便会散布到她的全身。到家了,瓦尔瓦拉·巴夫罗芙娜轻盈地一跃,便下了马车——只有母狮子才会这样地跳跃——回身面向格杰奥诺夫斯基,忽然冲他的鼻子尖发出一连串响亮的哈哈大笑。
“讨人爱的娘们儿啊,”这位五品文官在回家去的路上不停地想道,这时他的家仆正手持一瓶肥皂樟脑液等待他的归来,“幸亏我是个规矩人……只是她那么个笑法,是为个啥呢?”
玛尔法·季莫菲耶芙娜整夜坐在丽莎的床头,通宵未眠。
四十一
拉夫列茨基在瓦西列夫斯科耶待了一天半,几乎所有时间全都在四处漫游。他不能在一个地方停留很久:苦恼啃啮着他;一次次急切而又软弱无力的冲动不停地折磨着他。他想起回到乡下的第二天占据他心灵的那种情感;想起自己当时的种种打算,对自己非常气愤。有什么东西能够使他丢开他所认定的责任,他未来唯一的任务呢?对幸福的渴望——
又是对幸福的渴望!“显然,米哈烈维奇说得对,”他想着,“你想要再一次品尝人生的幸福,”他自言自语说,“你忘记了,幸福来光临你,哪怕只有一次,也是一种奢侈,一种你所不配享受的恩赏啊。幸福这东西从来是不完整的,它从来是虚假的,你也许会这样说;但是你有权享受完整而真实的幸福吗?把你的权利拿出来看看!你到处瞧瞧,在你的四周有哪个人是幸福的,哪个人在享受它的乐趣?瞧那个庄稼人赶车去割草;或许他是满足于自己命运的吧……怎么,你想跟他换个位置吗?回想一下你的母亲吧:她一生所要求过的东西实在少得可怜,而落到她头上的命运又如何呢?你啊,看得出,在潘申面前给他说,你回到俄国来是为了耕种土地,这只不过是吹吹牛皮而已;你回来是想在这把年纪上还去追求人家那些小姑娘的。一听到你有了自由的消息,你就把什么都抛开了,都忘记了,你连忙跑过去,像个抓蝴蝶的小孩子一样……”当他这样思索时,丽莎的形象不断地出现在他的眼前;他费尽气力把这个形象赶开,也把另一个在心头纠缠不去的形象,那张不动声色而又诡计多端的,美丽而又可恨的面孔赶开。
安东老头儿注意到,老爷不大舒服;他在门外叹过几声气,又站在门口叹几声气,便决定去找老爷,劝他喝点儿什么热的东西。拉夫列茨基对他大声地呵斥,叫他滚出去,而后来又向他道歉,说是自己不好;但是这一来老头儿倒更忧愁了。拉夫列茨基不能坐在客厅里:他好像觉得,曾祖父安德烈从画布上轻蔑地注视着他这个不肖儿孙。“你呀!还嫩得很呢!”
他那双歪向一边的嘴唇好像在说。“莫非我,”他想着,“连自己也对付不了,这点儿……小事情就抵挡不住啦?(战场上重伤倒地的人总是把自己的伤叫做“小事情”。人生在世,莫不自欺。)我就当真,怎么,是个小孩子?喏,是呀:近在眼前,终生幸福的可能性几乎已经捏在手里了——却忽然不知去向;轮盘赌也是这样啊——轮子只要再稍稍一转,穷光蛋,或许,就变成大富翁了。镜花水月,毕竟终成空——现在结束啦。我得咬紧牙关去干我该干的事,不许自己出声;好在我不是第一次控制住自己。我为什么要逃跑,为什么坐在这儿,像只把脑袋藏在树丛里的鸵鸟似的?灾祸临头先害怕,不敢睁开眼睛来——胡说!”“安东!”他大喊一声,“吩咐马上套车。”
“对,”他又想,“必须让自己保持沉默,必须牢牢地控制住自己……”
拉夫列茨基竭力想用这样一些思索来排解心头的痛苦,然而这痛苦是太大、太强烈了;他坐进马车要回城里去时,就连老得不仅头脑昏聩,而且知觉全无的阿普拉克西娅也摇起头来,伤心地用目光送他登程。马儿在奔跑;他一动不动地、直挺挺地坐着,眼睛也一动不动地凝视着前方的道路。
四十二
昨天夜里丽莎给拉夫列茨基写信,要他今晚上她们家来;但是他先回到了自己的住处。妻子和女儿都不在家;从佣人那里知道,她带女儿去卡里金家了。这个消息令他又惊又怒。
“看来瓦尔瓦拉·巴夫罗芙娜是决心不让我安生了,”他想,心中恨恨地激动不安。他开始来来回回地走动,把随处碰到的孩子玩具、书本、各种女人用的东西踢翻、扔开;他把茹斯汀叫来,吩咐她把这些“垃圾”全都拿走。“Oui,monsieur,”她说,做了一个鬼脸,便开始收拾房间,姿势优雅地弯下身子,她的每一个动作都让拉夫列茨基感到,她把他当做一头粗野的狗熊。他厌恶地瞧着她那张衰颓而依然“诱人的”、讥笑似的巴黎面孔,她雪白的袖套,丝织的围裙和轻巧的小帽子。他终于打发她走开,犹豫了好一阵子(瓦尔瓦拉·巴夫罗芙娜还没有回来)才决定到卡里金家去——不去玛丽娅·德密特里耶芙娜那边(他怎么也不愿走进她的客厅,那间他妻子待着的客厅),而去玛尔法·季莫菲耶芙娜那边;他记得,女仆们出入的后楼梯是直通她的房间的。拉夫列茨基便这样做了。他运气很好:在院子里就碰见了苏洛奇卡,她把他带到玛尔法·季莫菲耶芙娜屋里。他看见她跟往常不同,只是独自一人;她坐在屋角里,没戴帽子,俯着腰,两手交叉着放在胸前。看见拉夫列茨基走进来,老人家慌了手脚,连忙站起来,在屋子里到处走动,好像在找她的小帽子。
“啊,你来啦,啊,”她说着,躲开他的目光,显得很不安,“喏,你好呀。喏,怎么?这咋办呢?你昨天去哪儿啦?喏,她来啦,喏,是呀。喏,只好这么着……不管怎么样吧。”
拉夫列茨基在一把椅子上坐下。
“喏,你坐吧,坐吧,”老太太继续说着,“你直接上楼的吗?
喏,对呀,当然啦。怎么?你是来看我的吗?谢谢你。”
老太太不说话了;拉夫列茨基不知道给她说什么好;但是她明白他的意思。
“丽莎……对,丽莎刚刚还在这儿,”玛尔法·季莫菲耶芙娜继续说,一边把手提袋上的绳子结上又解开,“她不太舒服。
苏洛奇卡,你在哪儿?过来,我的妈呀,怎么你就坐不住呀?
我也头痛。一定是让这些个唱歌呀弹琴呀给闹出来的。”
“什么唱歌呀,姑妈?”
“怎么;刚才还这么,你们把这些玩意儿叫什么来着,二重唱,还在唱着呢。全是意大利话:唧唧喳喳的,简直是一帮子喜鹊。把那调子使劲儿一唱呀,就跟抽你的魂儿一样。这个潘申,还有你那口子。怎么这么快就混熟啦:真叫做,亲人一样啦,不讲规矩啦。不过嘛,按说是:狗也得给自个儿找个窝呀;不会死在外头的,好在人家不赶走它。”
“反正是,说真的,我没料到会这样,”拉夫列茨基回答,“这也得有很大的勇气呢。”
“不对,我的宝贝儿,这不叫勇气,这叫会打算盘呀。上帝保佑她吧!你要把她,人家说,送到拉夫里基去,是真的吗?”
“是的,我把这个庄园给瓦尔瓦拉·巴夫罗芙娜用了。”
“她找您要钱了吗?”
“暂时还没有。”
“喏,拖不了多久就会要的。我这会儿才把你看仔细了。
你身体好吗?”
“好的。”
“苏洛奇卡,”玛尔法·季莫菲耶芙娜突然喊一声,“你去给丽莎维塔·米哈依洛芙娜说——就说是……不,你去问问她……她是在楼下的吧?”
“在楼下。”
“喏,好的;那你就问问她:就说,她把我的书放哪儿啦?
她就明白啦。”
“听见啦。”
老太太又忙乱起来,把她的梳妆台抽屉一只只拉开。拉夫列茨基一动不动地坐在他的椅子上。
忽然听见楼梯上轻轻的脚步声——丽莎进来了。
拉夫列茨基站起来,鞠一个躬;丽莎在门边停住。
“丽莎,丽索奇卡,”玛尔法·季莫菲耶芙娜手忙脚乱地说,“你把我的书放哪儿啦,书你放哪儿啦?”
“什么书呀,姑奶?”
“那本书嘛,我的天啦!不过我没喊你来……喏,反正一个样。你在下面干什么呢?瞧,菲托尔·伊凡尼奇来啦。你的头还痛吗?”
“没什么。”
“你老是说:没什么。你们在下面干什么,又是搞音乐?”
“没有——玩牌呢。”
“是呀,她干什么都在行。苏洛奇卡,我看,你想去花园里跑跑吧。去吧。”
“啊不,玛尔法·季莫菲耶芙娜……”
“别犟嘴啦,得了,去吧。纳斯塔霞·卡尔坡芙娜一个人去花园了:你去陪陪她。对老人家要恭敬点儿。”苏洛奇卡出去了,“我的小帽子哪儿去啦?放哪儿啦,真的?”
“我去找找吧。”丽莎轻声地说。
“坐下,坐下,我的两条腿还没垮呢。大概是在我的睡房里。”
于是,玛尔法·季莫菲耶芙娜向拉夫列茨基斜瞟了一眼,就走开了。她本来是让房门开着的,可又忽然回身来关上了它。
丽莎靠在椅背上,默默地用手捂住自己的脸;拉夫列茨基停在他原先站着的地方。
“我们就像这样的见面了。”他终于说道。
丽莎把手从脸上移开。
“是的,”她声音低沉地说,“我们很快就要受到惩罚了。”
“惩罚,”拉夫列茨基说,“您为什么该受惩罚?”
丽莎向他抬起自己的眼睛。这双眼睛并没有显露出痛苦和惊慌:它们显得小一些,暗淡一些了。她的脸是苍白的;微微张开的嘴唇也是苍白的。
拉夫列茨基的心又怜又爱地战抖了一下。
“您给我写了信:说一切都结束了,”他喃喃地说,“是的,一切都结束了——结束在开始以前。”
“这一切都应该忘掉,”丽莎说,“我高兴您来了;我原想写给您看,可是这样更好些。只是要赶快利用这几分钟时间。
我们俩都得去尽自己的责任。您,菲托尔·伊凡尼奇,应该跟您的妻子和解。”
“丽莎!”
“我求您做到这一点;只有这样才能赎取……过去的一切。
您想想看——就不会拒绝了。”
“丽莎,看在上帝分上,您要我做的是办不到的事。无论您命令我做什么,我都肯做;可是现在跟她和解!……我什么都同意,我什么都忘记了;可是我不能强迫自己的心去……别这样吧,这是残酷的啊!”
“我也没要求您……像您说的那样做;不要跟她住一起,要是您做不到的话;可是要和解,”丽莎回答他,又把手捂在眼睛上,“想想您的女儿吧;您就为了我这样做吧。”
“好,”拉夫列茨基透过牙齿缝说道,“我就这样做,就算吧;这是我在尽自己的责任。可您呢——您要尽的责任是什么?”
“这一点我知道。”
拉夫列茨基突然一抖。“您不会是要嫁给潘申吧?”他问。
丽莎露出一丝几乎看不见的笑容。
“噢,不会的!”她轻轻地说。
“唉,丽莎,丽莎!”拉夫列茨基激动地叫道,“我们本来可以多么幸福啊!”
丽莎再次望了望他。
“现在您自己看见了,菲托尔·伊凡尼奇,幸福不由我们决定,由上帝决定。”
“是的,因为您……”
隔壁房间的门迅速打开了,玛尔法·季莫菲耶芙娜拿着她的小帽子走进来。
“好不容易找到了,”她说,站在拉夫列茨基和丽莎中间,“是我自己乱塞。这就叫做老啦,真要命啊!不过嘛,年纪轻也未必就强些。怎么,你自己带老婆上拉夫里基去?”她又转身向着菲托尔·伊凡尼奇,说了这最后一句。
“跟她去拉夫里基?我?我不知道这事。”他稍稍停了停,才说。
“你不去楼下?”
“今天吗?——不去。”
“喏,好的,随你吧;那你呢,丽莎我觉得,该去楼下了吧。
哎呀,我的老天爷,我忘记给我的红腹灰雀儿喂食啦。那你们就再等等,我这就……”
于是玛尔法·季莫菲耶芙娜跑出去了,并没有戴那顶小帽子。
拉夫列茨基急忙走到丽莎身边。
“丽莎,”他开始用恳求的语气说,“我们要永远被拆开了,我的心要碎了——把您的手给我,让我们告别吧。”
丽莎抬起头来。她疲倦的,几乎已经失去光芒的眼睛停在他的身上……
“不,”她轻声地说,把已经伸出的手收了回去,“不,拉夫列茨基(她第一次这样称呼他),我不把我的手给您。何必呢?您走吧,我请求您。您知道,我爱您……是的,我爱您,”
她迫使自己补充说了最后这句话,“可是不,不。”
她把手帕举到唇边。
“至少请您把这块手帕给我吧。”
门吱嘎地响了……手帕顺丽莎的膝盖滑落下来。拉夫列茨基在它还没落到地上的时候抓住了它,迅速塞进自己侧面的衣袋里,一回过头,遇上玛尔法·季莫菲耶芙娜的目光。
“丽索奇卡,我好像听见你妈妈叫你。”老太太说。
丽莎立即站起来走了。
玛尔法·季莫菲耶芙娜又坐到自己的角落里。拉夫列茨基开始跟她道别。
“菲佳。”她突然地说。
“什么,姑妈?”
“你是个诚实的人吧?”
“怎么?”
“我在问你:你是个诚实的人吗?”
“我希望我是的。”
“哼。那您给我说句担保的话,说你是个诚实人。”
“好吧。可这是为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