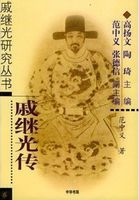鲁迅一走,许广平也是命苦的人,失去了丈夫,自己一个人带着孩子,因此,在萧红心中,她觉得最痛苦的就是许广平了,她吩咐萧军说:“既然住得很近,你可替我多跑两趟。别的朋友也可约同他们常到她家去玩。鲁迅没完成的事业,我们是接受下来了,但他的爱人,留给谁了呢?”
她就是这样一个女人,心细如尘,又敏感如丝,她体会到更多的痛,也同样能够体会更深的爱。她看任何东西,总是很透。
她想着给鲁迅出版全集的事,认为中国人集中国人的文章总比日本人收集得方便,而日文版的鲁迅全集11月份就可以出版了。这使她佩服不已,因之也更加焦急,跟萧军说,她要找胡风、聂绀弩、黄源诸人商量立即做起来。她觉得,自己应该为鲁迅做点什么。
萧红没有按约定的期限在东京住满一年,她提前回国了。此刻的她,已经归心似箭,再也容不得在东京驻足。
12月间,大约萧军曾经写信劝她归去,所以她会在几封信里一连谈及,但是,声明还没有这个意思。当时,她的弟弟张秀珂已经到了上海。
也就在这时,情势发生了变化,萧军再度坠入爱河了。是他的甜蜜再恋,却是他的晴天霹雳。
萧军在晚年承认说:“那是她在日本期间,由于某种偶然的际遇,我曾经和某君有过一段短时期感情上的纠葛--所谓‘恋爱’--但是我和对方全清楚意识到为了道义上的考虑彼此没有结合的可能。为了要结束这种‘无结果的恋爱’,我们彼此同意促使萧红由日本马上回来。这种‘结束’,也并不能说彼此没有痛苦的!”
其中说的“某君”,就是离日返沪的许粤华。
萧军也同样有他的痛苦,在这期间一个人拼命地喝酒。黄源把他喝酒的情形告诉了萧红,她看不清他埋藏在深海的心,所以她也只能心系他的健康,这样对他说:“清说,你近来的喝酒是在报复我的吃烟,这不应该了,你不能和一个草叶来分胜负,真的,我孤独得和一张草叶似的了。我们刚来上海时,那滋味你是忘记了,而我又在开头尝着……”
她一遍一遍地尝着苦。一片草叶,迷失在一程又一程的跋涉中。
大约启程回国前夕,萧军在信中向她坦陈了自己的隐情。对此,萧红表示出了唯“五四新女性”才有的理解和宽容。她说,发生在男女之间的爱情,只要是真诚的,哪怕带着点“罪恶”,哪怕对她构成了侵犯,她也是可以接受的。她崇敬真正的爱情,甚至于这种爱伤害到了她的感情。
再经受尘世一番又一番风雨后,她心中的智慧之光渐渐苏醒。漫漫前路,她将不会再度迷失。
4.疯长的墓草
1937年1月中旬,萧红回到上海。
第一次来上海,这里是异乡;如今再一次来到上海,却是归乡客。同样的地方,同样的风景,却再找不回当时的心情。所有爱与伤愁,散在时光的长河里,随着浪潮奔流到海。
萧红和萧军把家从北四川路搬到吕班路,住进一家由俄国人经营的家庭公寓里。
吕班路是一个很有劲的地方,行人很少,周围一片静寂。弄堂里是一排西班牙式楼房,里面有些空房出租,房客大多是白俄,许多文化人,包括一群东北作家都集中居住在这里。
安顿下来以后,萧红就去拜谒鲁迅墓。
阴沉的天气,如同萧红阴霾的心,沉甸甸的,却找不到一个发泄的出口。落叶簌簌地飘着,萧红和萧军踏着走进万国公墓。在墓前,她看见了鲁迅的瓷半身像,看见了地面上许多巳经枯萎的花束,但是她却偏偏觉得那花是美的。因为回忆似乎总是比现实珍贵。
四周长满了青草。她想象着,再过一些时日,墓草就将埋没了墓碑。
萧红将手中的鲜花轻轻放在上面,又在近旁拔了一株小小的花草,竖在墓边的泥土里。然后,她对着鲁迅墓深深鞠了一躬,低下头,默默垂泪,泪点破了心海,回忆一圈一圈地涤荡。使得她心中涌出一阵阵几近崩溃的
离去时,刚刚走了几步,她突然急转身,奔到鲁迅墓前,扑倒在地上,放声痛哭起,情感太深,也就没有了坚强的力气。
生活还是要过,未来的路还是要走,咽下悲伤的泪,她依然要更加坚强地走着她的人生的。
回国以后,萧红的一头烫发又变成了平顺的短发,穿着也十分朴素,完全回到了过去的样子。发型和着装可以回到过去,可是时光易逝,难再倒回,她再也回不到过去的光景和心情。
她在文坛的地位可跟从前大不相同了。许多刊物向她约稿,许多活动请她参加,显然,她和萧军已经进入了名作家的行列。
开始时,她努力振作,看上去要比刚到上海的时候好很多,她一心都扑到了文学上。然而,似乎所有美好的时光总是太短暂。
萧红的心中始终方不下旧时光,哈尔滨时代是她所纪念的,“牵牛房”的一段日子,始终是她心里的一片抹不去的阳光。如果能回到从前那般单纯的境地里去,该有多好!她常常在心里这样念着、盼着、回忆着。却眼看着现实把回忆里的甜美梦境推倒。
许粤华怀了孩子,得做人工流产的手术。这样,萧军便忙着照顾她,无暇顾及萧红了。
文艺界的活动,萧军多是自己应酬去,编刊物也是以个人的名义进行的。他们不常在一起,作家白危在马路上见到他们,也是一前一后地走着,萧军大踏步走在前面,萧红在后面跟着,并排走着的情况很少。一对原本相爱的人,渐渐分离成了两个独立的个体,过程中的疼痛,也只有亲身经历过的人才能够懂得。
当两个人都各自独立,彼此的棱角会互相划伤。
张秀珂曾经回忆说,他经常见到两个人起冲突,而对于两人之间的冲突,萧红一直抱持沉默的态度,即使对胞弟也不愿说出真相。
强者使用暴力,弱者作心理的抵抗,就是这样,两个人才能够得以维持表面完美的和平。
有一个日本作家来到上海,特别想见见许广平和一些进步作家。在一家小咖啡室里,聚集了萧军、萧红,还有另外几位。梅志、靳以……他们都见证了家庭暴力的事实。
萧红的右眼青紫了很大的一块,吸引了大家的注意。“怎么啦,碰伤了眼睛?”
“我自己不加小心,昨天跌伤了。”萧红平淡地回答,又补充说道:“黑夜里看不见,没关系……”
“什么跌伤的,别不要脸了!”萧军在一旁得意地说,“我昨天喝了酒,借点酒气就打她一拳,把她的眼睛打青了!”
“不要为我辩护,……我喝我的酒……”他就是这样的决绝,完全不给她为他辩护的机会。
萧红的眼中涨满了委屈的泪水,一份感情,走到了如今的境地,怎么能不让她伤心。
萧军是个决绝之人,爱的时候,情深意切,舍尽生命的待她。然而,当爱随着岁月逝去,他便匆匆撒手,不留办点情分。
萧红,从爱,到伤害,都一分一分地用力承受。
这样一对角色,似乎是浓缩了世间不少眷恋的影子。
时间仿佛倒退到一年以前,萧红又常常一个人往许广平那里跑。然而,这个时候,鲁迅已经不在了,她也再不似从前的那个萧红了。物是人非,她无法回到最初,她只能在这份越走越冷的感情里,体味亘古的荒凉。
她一去,又是一坐半天。她的痛苦,只能向许广平一个人倾诉。这时,许广平就像母亲一样,安慰她,让她在跟前慢慢地舔自己的伤口。当她诉说着的时候,有时遇到梅志进来,也并不避忌。
朋友们都知道,对于二萧之间的感情事,他们也是无力回天,情易逝,人还在。他们劝慰萧红,希望她珍惜身体。
朋友们的劝慰,萧红当然是很感激,然而,内心的伤痛依旧无法抹平。
快乐的时光又总是那么的短暂,痛苦的时光总是会被恶意的拉长。萧红只能独自度过这段难熬的日子。
她尽量地让自己沉浸在写作中去,专注到另一件事中,心中的愁苦偶尔也能放一放。想法是好的。可是每当提笔写到一些感性的情节时,她又很不自觉地会想起来,情绪时不时地再心中汹涌地波动,痛苦堵住了她的胸口,闷得她好似要难以呼吸。这时候,她会从屋子里溜出来,像一个无主的孤魂,在街上游荡着,任周围人声车声总耳畔掠过,任一段段街景从眼风中流走,她荒凉空旷地望着远方,穿越时光,走进回忆里……
鲁迅逝世时,许粤华同胡风、黄源、周文和萧军等一起值夜守灵;从她以雨田的笔名发表的纪念鲁迅的文章看,她对鲁迅有着很好的理解。再加上在日本时她对自己关爱有加,所以
一天,萧红到黄源家去,正好遇见萧军在同黄源、许粤华夫妇说话。但是,萧红一出现,他们的谈话就突然停止了。萧红向许粤华招呼道:“这时候到公园里去走走多好呀!”见到许粤华躺在床上,窗子敞开着,她说:“你这样不冷吗?”说着,要把大衣给她披上,黄源说话了:“请你不要管。”
萧红沉默,心中却很不是滋味。
她想:这和我有什么关系呢?为了对待萧军,竟然拿我出气了。可是,我们之中谁和太太们的友谊不是建立在做丈夫的朋友身上呢?谁不是一旦和朋友决裂,就连同太太作为一体而摈弃的呢?
萧红忽然看清楚了自己,和作为男人的附属物而存在的事实,一种悲凉之感。
如今种种,她的心中更是诸多感叹。感一段韶华易逝,叹一声情字两难全。
她同萧军的爱,经历了种种辛苦,好不容易得来,因此,她心中一直有一种不灭的信仰,就算是在日本时,对于和萧军的爱,萧红还有些自信,总以为他们的爱,在苦难里已经融为一个整体,也就不会轻易被割离的。生生割离的剧痛,她是不能承受,而萧军也同样如此。
所以萧红回来,她要以独立地展示自己,希望自己曾经选择的男人也同样地选择她,而且无悔于这种选择。这是她的自信,也是她的性格。他相信萧军会欣赏这样一个独立的自己。
然而,情运难测,她所有关于萧军的爱的幻想一一幻灭。萧红终于发现,萧军没有悔意,他不但不爱她,甚至连起码的尊重也没有。爱已从指缝中流走,摊开手,满是伤痕。
萧红始终还是没办法公开决绝地与萧军分手,她还是没办法承受这样隆重正式的分离。然而,情已至此,已经无法再继续,进退两难之间,她选择了逃离。
她想到去北平,住一段时间再作打算。总之,她要离开上海,离开萧军,以及他的朋友们!
她把前往北平的想法正式向萧军提了出来,至于理由,仅说是出于怀念而已。从现在开始,好像她变得不那么坦白了,经历了太多伤害之后,她已经渐渐学会保护自己,将自己的心事藏匿起来。
萧军虽然对北平的印象并不算太好,为了弥补对萧红的过失,也就同意了她的决定,让她先到北平,自己随后再到。
近期,他虽然变得粗暴,但是旧情旧事,他是不能不系念的,陪萧红在北平住上一段日子,或许会生出一点感情来,至少两个人的关系不至于太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