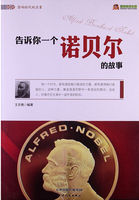如果以一句话概括两种审判方式的不同,那就是“英美法是以保护被告利益为前提的”。比如,虽然《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宪章》明文规定:尽最大可能采取并适用便捷而不拘泥于技术性的程序。但实际情况却是,由于严格按照英美法审判方式,程序烦琐而冗长:审判开始,法庭必须询问被告是否认罪。如果认罪,就不用审理了;如果不认罪,才能正式进入审理。
对每一个被告,庭长得先用英语问一遍:“你是否认罪?”日语翻译一遍,被告回答后,再翻译成英文。28个被告,每个人都如此这般地询问、翻译、回答、翻译。所有的程序走完一遍后,一次开庭也就结束了。好不容易进入审理阶段,对证人的讯问,先是直接讯问,即由举证方检察官(或律师)发问,然后由对方反讯问(或称“反诘”或“质讯”),接着还可有再直接讯问和再反讯问(或称“再反诘”或“再质讯”)。就这样,没完没了,可以无休止地进行下去,让人生厌,但又绝对不能偷工减料,因为这些都是当事人的权利,是神圣不可侵犯的。
从这个时候开始,向哲浚满脑子想的就是“证据”二字。自此,他和裘劭恒频繁回国,一是请求政府增派人手,二是四处搜集证据。他们穿梭于受害区、难民营,但收获寥寥。所有的受害者都对日本鬼子咬牙切齿,却都无法提供明了的证据加以证明。这个时候,向哲浚不停地告诫自己,义愤是没有用的,复仇心理也是要竭力克制的,唯有证据才是一切。
在南京,在司法部刑事司司长杨兆龙的帮助下,向哲浚和裘劭恒面对堆积如山的南京大屠杀档案,来不及看内容,来不及细细辨别,一股脑儿地装箱运回东京。
与此同时,季南特别划拨资金,又派检察局的工作人员到中国,协助向哲浚登报公开招募了5名工作人员,其中有向哲浚的内弟、经济学硕士周锡卿,另外还有东吴法学院的毕业生高文彬、郑鲁达、刘继盛以及日文翻译刘子健。
相比苏联原计划派出70个检察人员,后来在盟军总部的力劝下减至30人参加检察工作的庞大检察团,中国仅有以向哲浚为首的7名检察人员。这不能说当时的政府对此次审判丝毫不重视,而是对真正的法律、法律程序认识不足。在他们看来,所谓审判,不过是一种形式而已。在梅汝璈法官临行前,立法院院长孙科对他说的一段话,颇有意味。他说:“这是千载难逢的机会,不但有价值有趣味,而且可以历史留名。”
不知法官梅汝璈、检察官向哲浚最初的动机是否真的只是为了抓住这个“可以历史留名”的机会。然而,当他们真正置身于东京法庭这样一个充满法律气味的氛围之中时,陡然体会到了法律的神圣,也感受到了审判的艰难。
废墟里的东京,在一座名叫市谷高地的小山上,有一幢侥幸逃过一劫的庞大建筑赫然挺立,醒目又孤独。它是原陆军士官学校,战争中,它是陆军省和参谋本部。侵略的指示从这里发出,罪恶的暴行在这里得到默许。如今,在大门前,一座假山上,一株业已枯萎的松树上,钉着一块褐色木牌,用英文标示着:远东国际军事法庭。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外景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判大厅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于1946年5月3日正式开庭。然而在开庭前,向哲浚就已经嗅到了浓重的火药味。这火药味并不只是来自于检方和被告之间的对立,也因为检察官之间的显著分歧和法官之间的明争暗斗。
在纽纶堡审判中,所有的辩护律师都是德国籍,没有一位属于盟国国籍。这是很容易理解的:本国人为本国人辩护。但是,《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宪章》中只规定了法庭所用语言,即英文和日文,却并没有规定律师的国籍。也就是说,被告的辩护律师除了日本国籍之外,也允许有盟国国籍。这似乎难以解释,原本是战胜者,却又要反过来为战败者涂脂抹粉而竭力开脱罪责,岂不荒唐。然而事实的确如此,被起诉的28名战犯,除了每人有一或两位日本律师外,盟军驻日总部以审判适用英美法,而日本适用的是大陆法,故日本律师不谙英美法规则,为维护被告合法权益,所以特别批准为每名战犯再配备一两名美国律师。
面对上百人的庞大律师团,向哲浚几乎要窒息。“这太不可思议了。”他暗自嘀咕。但是,当他将眼光从死板而没有生气的法律条文中抽离出来而站在一个更高的层次往下俯视时,他明白了:政治格局瞬息万变,美苏关系、美日关系正在发生着微妙的变化,美国人除了对珍珠港事件仍然耿耿于怀以外,对日本人的其他侵略行为已经不很在意,也不准备严加惩处了。
在国际检察局起草对战犯们的起诉书时,检察官们因是否应当将日本天皇也列入战犯名单而发生激烈争辩。然而就在此刻,向哲浚却听说盟军总部驻日统帅麦克阿瑟正秘密会见天皇。他们之间的谈话内容,至今也将永远是个谜,但他们之间的交易是明摆着的。因为之后,天皇被豁免起诉。
更让向哲浚郁闷又愤恨的是,曾给中国人民带来深重灾难的日军“七三一”细菌部队也未被起诉,原因是美方与日方达成了协议:只要日方交出试验数据,就不起诉。
向哲浚明白这一切,他和他的同事们是无力改变的。他们能做的,也只有在他们的职权能力范围之内,力争将侵略中国者送上绞架。
东京审判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控方(即检察方)提起诉讼,宣读起诉书,并提供证据;第二个阶段是被告作集体答辩,提出反证,控方可以反击;第三个阶段是被告个人单独反证,与控方对质。
在第一阶段的中国部分中,溥仪已经算是一个比较有力的证人了,但他的傀儡身份又注定他只是受日本人摆布,而不可能洞悉日方的具体计划和暴行,特别没有提出控诉土肥原、板垣主要罪行的确切证据。加上他有所顾忌,留有一手,所以仅仅依据他的证言,实难达到目的。
检方的另一个证人是国民党政府军政部次长秦德纯。他曾是国民党第27军宋哲元的部下,担任过北平市长,与土肥原打过交道,签订过所谓“秦土协定”。然而,向哲浚虽然曾经留学美国,但他更多地获取了法学理论知识,并没有诉讼经验,对英美法诉讼中的证据法则不甚了了,以为有个证人出庭,那就是证据,却不想证人证言是否能被法庭采信,也是要经过辩方鸡蛋里挑骨头几近苛责的质问和反诘的。
秦德纯是一个军人,更不知道这些。他精神抖擞地走上证人栏,慷慨激昂地控诉日军“到处杀人放火,无所不为”。当辩方一句“如何的杀人放火,如何的无所不为,你又如何证明”,他就傻了眼。他的证词被斥为空言无据,几乎被轰下证人台。
向哲浚万分懊丧。可以说,第一阶段对土肥原和板垣的控诉,因为证据的不足,对中方极为不利。在第二、三个阶段中,控方已经不能提交证据,而只能将证据融进对被告的反诘中。如果这时中方还是没有有力证据,因证据不力而盘问、反驳不得力,后果将不堪设想。土肥原和板垣恐怕也有所意识,因此有些张狂。土肥原自开庭后就一直守护着他的“沉默权”,自始至终不发一言,但向哲浚能从他逐渐放松的脸上看到些许不屑、些许得意;板垣没有土肥原那样有心机,他直接将他的内心写在脸上,甚至口出狂言,“要与中国人大战三百回合”。
雪上加霜,就在这时,检察长季南告诉向哲浚,他已经决定在即将开始的第二阶段审理中,由菲律宾检察官罗贝茨担任主审土肥原和板垣的检察官。也就是说,中方将失去盘问、反驳,与这两个刽子手面对面的机会。失去这样的机会,意味着他们在中国的侵略事实有可能永远被掩盖,从而使他们逃脱应有的、中国人民给予的惩罚。“为什么?”向哲浚反复追问的同时,其实他的心里是知道为什么的,因为中方没有证据。就连中国法官梅汝璈也不免为此焦躁不安,颇有些怨气地说:“你们检察官拿不出证据,让我怎么判?”
怎么办?在法庭审理由中国部分转向太平洋战争部分,也就是第一阶段即将结束时,向哲浚抽空返回南京,向政府述职,也设法找寻解决证据的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