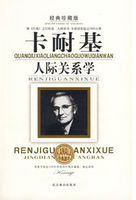在王小波逝世5周年、诞生50周年之际,许多刊物都发表了纪念文章。对于这位文坛“怪”杰,我以为了解一下他的知识背景和成功原因,也是一种纪念。小波去世后,他的哥哥王小平说:80年代初,他师从沈有鼎先生攻读符号逻辑和数理逻辑时,小波对前者也感兴趣,因此小波文章中的那些“怪”论,大抵与此有关。他还说:中国人常常思路不清,缺乏逻辑训练;相比之下,西方人往往训练有素。
既然如此,沈有鼎是个什么样的人呢?在了解这位逻辑学家之前,不妨先看一看浦江清的《清华园日记》。1937年初,因为受“一二,九”运动的影响,清华大学提前放了寒假。也许是闲来无事吧,浦江清邀请吴晗去清华合作社喝茶。为此他在日记中写道:“过沈有鼎君卧室,入之,凌乱无序。沈君西装,弹古琴,为奏《平沙落雁》一曲。亦强之出喝茶。沈君于西服外更穿上棉袍,真可怪也。”
说到沈氏之“怪”,有一篇轶文披露过令人吃惊的情况。这篇文章发表于1948年《人物杂志》,题目是《哲学家沈有鼎像赞》。文章说,沈是一个十分怪异的人。第一,他不善理财。每次开支,都把全部薪水放在手提箱里,然后每天去数一遍。数来数去,难免要数糊涂。有一次他少了10元,便怀疑是同宿舍的钱穆所为。钱先生和他分辨不清,气得打了他一个嘴巴。第二,他不爱换洗衣服。一件衣服穿在身上,“一直到破烂不堪脱掉丢了为止,中间连一水都不洗。”有时候他到表兄潘光旦家,潘才强迫他换洗一下。第三,他的眼睛总是发呆。这种神态和那邋遢模样,很容易引起别人误会,甚至被警察捉去。为此关于他的谣言很多,有人说他逛商店时被当成小偷,有人说他想看表便爬上人家的墙头,有人甚至说他“是因为看女人洗澡”而被捉。第四,他不大关心外界的变化。抗日战争时期,他随学校到了昆明。当地多雨,他总是穿着皮鞋被淋得像落汤鸡一样,即便如此他也不乱方寸,我行我素。他不爱看报,对社会上的事情也不关注。第五,他勤学好问、兴趣广泛。在昆明西南联大时,他听遍文学院每个教师的课,听课时还总爱提问。他会弹古琴,会唱昆曲,“不过他的昆曲是坐在马桶上的时候才唱的”。他嗜书如命,据说有借书不还的“毛病”。此外他还吃遍当地的风味食品,就连寺院的斋饭也不放过。正因为如此,他的婚姻生活很不顺利。该文作者认为:沈有鼎出身于一个“坐享其成的士大夫大家庭,又受着与现实生活脱节的麻醉教育,而玄奥的经院哲学又给他一个自我的精神世界”,所以他成了“20世纪的一大奇迹”。
对于这些匪夷所思的传闻,我不敢相信,便请教我的同事李元庆先生。早在六七十年代,李和沈先生同在中国科学院哲学所工作。从他的介绍中,我感到该文虽有漫画色彩和夸张成分,但沈先生给人的印象就是那样。此外,李还借给我一本书,名为《摹物求比——沈有鼎及其治学之路》。这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逻辑室为纪念沈先生诞辰90周年而编的。该书除收集了沈先生的文章和“沈有鼎思想学术讨论会”的论文外,还有其学生写的几篇回忆文章。我不懂逻辑学,无法窥其堂奥,只能从这些回忆文章和其他资料中去解读这个人物。
沈有鼎(1908—1989),字公武,上海市人。他出生于书香门第,父亲沈恩孚是清末举人。辛亥革命时,沈恩孚担任江苏民政次长和省公署秘书长。后来退出政界,专门从事文化教育活动,曾发起中华职业教育社,筹建南京河海工程专科学校,创办鸿英图书馆。他酷爱昆曲,与著名实业家穆藕初交往甚密。穆于1921年在苏州创办昆曲传习所,培养了一批人才,沈有鼎的昆曲修养,显然与此有关。
早在中学时代,沈有鼎就读过一本逻辑学的小册子,从此对逻辑学产生浓厚兴趣。进入清华以后,他经常和同学们讨论逻辑问题。有一次,他们正在教室里高谈阔论,金岳霖路过这里,为其天赋所吸引,便站在外面听了很久。金先生说,当年清华的逻辑课应该由赵元任讲,赵请他代替,他便答应下来。我不知道他是不是为了沈有鼎,但有人说清华大学哲学系的成立,与金、沈二人有关。
1929年,沈有鼎从清华大学毕业后赴美国哈佛大学留学,师从谢非和怀特海二人。1931年,他又到德国海德堡大学和弗菜堡大学,先后在杰浦斯和海德格尔的指导下进行研究,并结识了著名哲学家胡塞尔和数学家策梅罗等人。1934年他回到清华大学,成为该校最年轻的教授。有意思的是,就在沈有鼎离开美国的那一年,金岳霖也步其后尘来到哈佛,跟谢非学起逻辑学来。为此,金先生对谢非说:“我教过逻辑,可是没有学过……”(《金岳霖的回忆与回忆金岳霖》,46页,四川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
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尽管金岳霖是我国公认的逻辑学权威,但是他却认为沈有鼎比他高明。抗日战争前夕,殷海光从武汉来到北平。有一天,他跟金先生参加逻辑研究会的聚会,有人提到哥德尔的研究非常重要,金先生便想买一本哥德尔的书看看,沈有鼎对他说:“老实讲,你看不懂。”金听了这话,先是“哦哦”两声,然后说:“那就算了。”当时殷海光才十七八岁,听到他们的对话非常惊讶。他说:“学生毫不客气的批评,老师立刻接受他的建议,这在内地是从来没有的。”(同上,163页)这个故事有几个版本,有人从中看到金先生的雅量,我则发现沈先生的率直和坦诚。冯友兰说过,“美国的哲学界认为有一种技术性很高的专业哲学。一个讲哲学的人必须能讲这样的哲学,才能算是一个真正的哲学专家。”他认为金岳霖的《知识论》就是这样一部技术性很高的哲学专著,应该译成英文介绍出去,尽管他自己并没有读懂(《世纪清华》,154页,光明日报出版社,1998年版)。
我不知道冯先生所谓“专业哲学”指的是什么,但逻辑学的确是一门技术性很高的学问。沈有鼎一生非常强调逻辑学的技术性,到了70多岁时他还表示,他“要像王小平说的那样,趁年轻的时候多学一些技术”。他的学生王路听到这话后颇有感触,认为这表达了沈先生对逻辑学的真诚。也许就是因为这种技术性的原因吧,金先生承认在他的著述中《逻辑》一书“写得最糟”;他还对另一位学生诸葛殷同说,他搞逻辑学是一个“历史的误会”。尽管如此,金先生对这门学问还是情有独钟。1949年初,著名马克思主义哲学家艾思奇到清华大学批判形式逻辑。批完之后,金岳霖幽默地说:艾先生讲的不错,不过他的每一句话都符合形式逻辑。
抗日战争中,沈有鼎一直在西南联大任教,与金岳霖共同培养出王浩、殷海光等人。王浩说,1949年以后,金先生在一篇文章中谈到,沈有鼎、王浩和殷海光是他的“三个跟不上时代的学生”。这种说法在海外影响很大。其实,看看这三个人的成就和金先生当年的处境,就会发现他们是金岳霖最得意、最有作为的学生。1972年中美建交以后,王浩从美国回来,金岳霖对人说:“沈先生有学问,其实王浩不是我的学生,是沈先生的学生,他们在一起讨论,我根本插不上嘴。”后来沈与王在通信中讨论数理逻辑问题,这些信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
抗战胜利后,沈有鼎以访问学者的身份与陈寅恪前往牛津大学,同行的还有邵循正、孙毓棠、洪谦等人,据说这是由陈寅恪推荐的,可见陈先生也对他十分看重。沈有鼎是1948年回国的,回国后穿着虽然整齐了,但个性依然如故。1949年,正在清华读研究生的苏天辅听金岳霖讲课,突然发现沈先生坐在后面。此后沈不仅每课必到,还争着发言。无奈之下,金先生只好制止他:“你别说,让苏天辅说。”还有一天,沈先生要带苏天辅下馆子,出门时怎么也找不到钥匙,便对苏说:“肯定是在你的衣兜里。”这与当年他怀疑钱穆是同样的心理。我估计,他对这种话的理解与常人不大一样。
在五六十年代,形式逻辑研究处于极不正常的状况,沈有鼎的处境不难想象。尽管如此,他还是改不了“不识时务”的“毛病”。听李元庆先生讲,“文革”开始后,大家天天都要手举《毛主席语录》搞所谓“早请示、晚汇报”。有一次,沈先生因为把手中的语录本拿颠倒了,便遭到红卫兵批斗。批斗了半天,他还不知道原因何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的梁志学和王路都谈到这样一件事:1969年1月,毛泽东发表了一项“最高指示”。人们敲锣打鼓游行归来之后,沈先生竟然在学习会上说,“最高指示”里有一个标点符号用错了。工宣队和军宣队的负责人认为这是“公然攻击毛主席”,当即召开大会把他狠狠斗了一顿。
沈有鼎的好学深思、博学多才是大家公认的。他精通英文、德文,还懂希腊文、拉丁文和梵文,对中国哲学如儒家、道家、墨家、名家、禅宗和西方哲学家如亚里士多德、康德、罗素、维特根斯坦、哥德尔、胡塞尔都有精深研究,是我国数理逻辑研究的先驱和逻辑史方面的权威。在生活上,他布衣破履,落拓不羁,在普通人眼里几乎是不能自理;但是在学术上,他却思维清晰,论证严密,表达准确。为了科学事业,他一生追求简朴,淡洎名利,崇尚独立思考,主张平等争论。在我看来,他之所以给人以怪异的印象,大概和陈景润一样,是因为太单纯、太天真、太痴迷于学问之故。所不同的是,他文理兼通,因此知识更渊博,兴趣更广泛。
沈有鼎先生一生沉醉于形而上的思考,对形而下的需求兴趣不大,这对于那些追逐物质利益的人来说是不可思议的。基于上述原因,我对所谓他出身于一个“坐享其成的士大夫大家庭,又受着与现实生活脱节的麻醉教育”的说法,实在不敢苟同。我以为,对于这种人是不能用世俗的价值尺度来衡量的,而健康的社会应该给他们更多的理解、更多的宽容。否则,我们不仅无法摆脱生生不息的平庸,还可能因为过于追求物质利益而影响整个社会的文明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