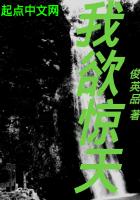三月的滇南蒙自山区,临近中午时分了,仍然有点儿春寒料峭。雾气不断从大地深处升腾而起,天地一片混沌,山野因此格外寂静。雾露浓密而汹涌,湿漉漉的扑打到脸上,竟似微雨拂面,同时还有些呛人。各种山雀婉转的啁啾,或远或近,在迷雾中飘荡,水洗过一般清脆。
崎岖的村道被雾堵塞,如核桃样的碎石,似拳头大小的石子,或者更大一些的狗头石,星落棋布于山道上,蓬松的红黄色尘土被雾水浸得潮湿,人走在上面微微地有些粘脚。道路两旁,青绿的麦田浓雾弥漫,那些正在灌浆的麦穗,贪婪地吮吸清凉的水气,看不见但想像得出的乳白浆汁,正在绿色的麦壳里一点点凝结。间或有一大片一大片的油菜,时隐时现在茫茫白雾中,朦胧而又暖意融融的黄花,弥散着赏心悦目的神秘光芒。
跟随一匹健壮的大骡子,翻过一个垭口,我们走进了这个白雾笼罩下的名叫老营盘的山寨。寨子是安静不动的,雾却在一阵一阵翻滚,湿漉漉的浓雾在房屋之间、柴草堆上、寨中巷道里流动飘散。看家狗警惕地狺狺狂吠,母鸡下蛋洋洋自得的啼鸣,猪儿们兴奋抢食的争夺声,在雾幛中此起彼伏。那些爬着牵牛花的竹篱笆,多。与我们相遇时,她低着头快步走过,不好意思正眼看我们。经过村子中央的池塘,只见一层薄薄的白色雾气,从黄绿的水面上升腾起来,萦绕着池塘四周高高矮矮开满白花的梨树,像轻烟一样缓缓飘舞。湿润清冽的空气里,飘满淡淡的花香。几缕明亮的阳光,潮气。透过正在渐渐消散的雾气,我突然发现,这个飘散着柴草轻烟和牛屎马粪气息的小山村,房前屋后铺天盖地开满素白的梨花。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多的梨花,一株一株显然还没有被人工改良过的梨树,自然健康地生长,树干粗壮,枝条茂密,树冠上仿佛缀满千朵万朵的雪花。我觉得这一定是有一个我们看不见的神灵,为这个滇南群山中的小山村,下了一场纷纷扬扬的白雪。这些被自然之神的巨手拂开的雪白梨花,不像桃花一样鲜艳得灼眼,流露出来的是一种与姹紫嫣红无争的淡泊和超然,它们开得如此纯洁素雅,我想这大约得益于山里湿润的天空,就像那些深山里边的俊俏女子,一旦被爱情滋润,就一个个清新朴素得楚楚动人。在去村长家的路上,一匹披红挂绿的小母马,辔头上戴着一面小圆镜,轻轻摇甩着修长的尾巴,神气十足地与我们擦身而过。相比之下,这匹马儿的主人,一个中年苗族妇女,就显得害羞得使劲穿透白雾,从微晃的梨树枝头撒落下来,水面上漂浮着的一大段落散文集片梨花花瓣,被那些迷乱的阳光灿烂地照亮,随着微微的水波轻轻荡漾。这时候,突然听见忧伤而又情意绵绵的山歌,像沾满晶莹水珠的落花,从某一片梨花深处飘荡过来。白雾与梨花淹没了唱歌人的身影,但是能够感觉得到,歌声轻轻颤栗着,犹如山村怀春少女忐忑不安的心跳。
村长家的院门敞开着,我们喊了一声就往里走。一只毛色黑亮的大狗,狂吠着朝我们这群不速之客冲来,马上又在村长的大声呵斥中,摇着粗而短的尾巴退回正堂屋去,雄纠纠地爬在堂屋门口,哈着粗气紧盯着我们。脸庞黧黑的村长,全身上下的基调全是沓沓的老式军帽,已被长年累月的汗水浸得有些黑亮(后来从他的闲谈中得知,这顶帽子是十多年前退伍带回来的,年轻时舍不得戴,人到中年了才常年戴在头上),脚上穿着一双旧旧的解放鞋,沾满了灰黑的泥巴,双手也黑糊糊的——原来他正在忙活着,用散发着青草气息的牛粪,糊在已经开始风化的土墙上,为蜜蜂建造一个结实而富饶的家园。一大群人站在院子里谈村委会换届选举的事,敦厚老实的村长不紧不慢地说,选嘛,选就选嘛,如果大家信任我呢,就会接着选我嘛,选上了就带着大家想办法一起发家致富嘛,选不上就算了,我也不会想不通,还不是一样的要过日子嘛。看来声势浩大、程序复杂、竞争剧烈的农村民主选举,并没有影响这个退伍老兵的豁达。
村长家宽大的院子里,栽着两棵高大的梨树,也是繁花盛开如云的样子。越来越亮的阳光,在枝叶间与薄雾缠绵融合。在明亮纯净的阳光里,我好象听见许多半开的花苞,吸足雾气后粲然绽开的声音。热情好客的村长,说什么也要留我们吃午饭。他憨厚地对我们说,你们检查指导村民选举来到我家,酒怕是要喝两口呢,革命不是请客,但饭还是要吃的嘛。说着,就要去抓那只在院墙脚刨食虫子的母鸡宰杀。我们一行人连忙劝住村长,大家都劝说他,有什么就吃什么,家常菜最好。村长有点不高兴,但还是笑着说,你们怕我腐蚀干部,不杀就不杀嘛,留着下蛋给我儿子媳妇坐月子,你们国家干部油水多,今天就只给你们吃点清汤寡水。在村长的吆喝下,村长婆娘和挺着大肚子的儿媳妇,麻利地在灶房里忙出忙进,锅铲与铁锅摩擦,碗盆不时轻碰,发出一阵阵欢快悦耳的声音。人多,堂屋里不大好坐,所以干脆把饭桌摆到了院子里。村长婆娘和儿媳妇把饭菜、碗筷摆好,吃饭时却躲到厨房里不出来。村长说,我们山里人待客,女人从来不上桌,这是传统的风俗,传统的东西嘛,不一定像你们干部说的是封建思想,山里乡下不能哪嘛。
香。
就着没有任何污染的肉菜,一小土碗包谷酒很快落肚,我的额头开始微微冒汗。酒酣时,白雾终于散尽,阳光温暖而灿烂。一阵微风吹来,那些在不住枝头的梨花片,纷纷扬扬地飘落,洒满了老是古老点,不过嘛,能让我们这些山里人家庭不吵不闹,隔壁邻居和和睦睦,老祖宗定下来、传下来的规矩,我们不敢随便就丢掉村长像一位知书达理的乡村土秀才,边说些充满生活气息的家常话,边劝我们多吃菜。笨重结实的四方木桌上,简单但分量充足、味道鲜美的农家菜热气腾腾:一大碗肥瘦相间的烟熏腊肉,散发出松针的芬芳与猪肉混合的香味;一大碗素炒野生厥菜,颜色黑绿清爽;一盆滇南一带特有的从过年就开始反复熬炖的酸汤菜,快煮烂了的肉皮飘散出微酸的诱人味道;二十多分钟前还水灵灵地生长在屋后园子里的青菜,现在煮好装在一只大瓦钵里,新鲜得无与伦比,菜叶碧绿,汤色清澈,钵头旁边还有一碗糊辣子加老姜末的蘸水;一只不大的竹箕里,放着几个在火塘炭灰里烤出来的荞面厚饼,村长用粗糙的大手把荞饼一个个掰开,饼心冒着热气,金黄喷饭桌,落到我们的头上、脸上和身上,漂浮在酒香四溢的土碗里。段落散文集村长眯着微醺的双眼说,我家这两棵老梨树,花开得多也掉得多,你们可能没有见过,结出的梨嘛,样子是不好看,像我一样憨包包的,不过能长得像小磨盘一样大呢。村长劝了大家一口酒,接着说,有一年,我坐在树下吸水烟筒,风一吹,几个被雀偷啄过的梨果,像下雪弹子(冰雹)一样,突然就掉了下来嘛,有一个不偏不歪正正地砸在我头上,一下子就把我砸得差点晕过去,比蜜还甜的梨水淌了我一头一脸,等我眼睛不再发花了,发现蜜蜂飞过来往我脸上爬,我现在养的这窝蜂子,就是那回引来家里养的嘛。
这个雾散日暖的正午,在这个怀抱梨花的村庄里,坐在农家院子的梨树下喝酒,听着闻所未闻的乡间趣事,农家自酿的包谷酒,将我的身心泡得酥酥软软的。我紧闭上嘴巴,细细回味青菜汤清心去火的苦凉,把那些带有官方色彩的套话咽进肚里,心甘情愿地任凭素白的梨花,不停地飘落到我的身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