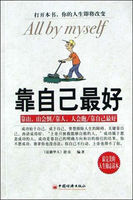去年的圣诞节,是我女朋友的生日,那天我们在一起喝酒,一直喝到夜里12点,我准备回家的时候,她拉住我,让我别走了,说实话,当时我清楚如果留下来将会发生什么事情,有点儿害怕,但是我知道如果那时候我坚持要走,肯定会让她看不起的,所以我硬着头皮留了下来。那个晚上,我和她有了身体的接触,但是我……是我不行,根本不能勃起,你明白我的意思吗?我们没有做成。我女朋友特别惊讶特别沮丧,我也觉得很没有面子,后来我们又试着做了一次,还是不行。我女朋友一直让我去医院看看,我不肯去,她很无奈,后来就不来找我了,我也没有主动去找她,我们一年多的交往,就这样不了了之了。
我不肯去医院,是因为我知道我的生理上没有问题,问题出在心理上。
说起我的心理问题,直觉告诉我一定和我的父亲有关。我父亲是派出所的所长,在我们老家,他是很有名的,大家都传说着许多他和犯罪分子斗智斗勇的故事。他对我的管教极其严厉粗暴,印象最深的一次,我才六岁吧,去幼儿园的路上摘了农民的豆角,后来农民跑到我家里来告状,我父亲知道了,一把抓起我走到离家不远的一座桥上,二话不说就扔了下去,我吓得哭都哭不出来,后来还是邻居把我给救了。
从小我对父亲一方面是崇拜一方面是愤恨,相反对母亲却没什么感觉,我母亲就是一个家庭主妇,每天洗衣做饭收拾屋子,什么都不问什么也不懂,我想要的爱和安全感,她没有能力给我。我觉得父亲是有能力给我这些的,但他对我总是一副爱理不理的样子,似乎我对于他,是一个可有可无的人。记得那时候在《中国少年报》上看过一篇介绍童话大王郑渊洁的文章,说他非常爱自己的儿子,和儿子的关系非常民主,像朋友一样。我特别羡慕,想如果自己有那样一个父亲该有多幸福,那之后我老向往着能有一个郑渊洁那样的人来取代我的父亲,这是我整个童年和少年时期最大的梦想。
读高中的时候,我们的历史老师和我父亲年龄相仿,非常温文尔雅,我不知道为什么,就对他产生了一种类似爱情的感觉,天天盼着上历史课,真到了他的课,我又紧张得不得了,有时候他的目光无意中和我的目光碰到了一起,我的心就狂跳不止,晚上躺在床上,我喜欢想他,想他的眼睛、他的笑容、他的胸膛一一如果我能躺在上面会是一种什么感觉呢?在那样的想象里我总是忍不住手淫……
参加工作以后,我的这种情况愈演愈烈,只有那些温文尔雅的中年男子才能激起我的性冲动,所以现在我最担心的是自己是不是同性恋?可是如果我是同性恋的话,为什么我只对温文尔雅的中年男人有好感,对其他男人却没感觉呢?
我明确地告诉左岸,他并不是典型的同性恋者,出现这样的问题,很可能是源于自己幼年时期的“俄狄浦斯情结”——每个人的幼年时期,都会有一个阶段存在着对双亲中异性者的乱伦幻想和双亲中同性者的嫉妒和谋杀冲动,由于这种幻想与古希腊传说中的俄狄浦斯的经历十分相似(他杀死了父亲并与母亲结婚),弗洛伊德将之称为俄狄浦斯情结。俄狄浦斯情结是一个人正常性心理发展过程中所必须经历的阶段,在这个阶段中要完成许多性心理发育的任务,比如道德观的逐步建立、认识自己的性别等等,但从目前左岸的情况来看,他的性心理发育在俄狄浦斯期出现了停滞——父亲的严厉与强悍对他而言是一种无处不在的威胁,让他觉得做男人是可怕的事,他不敢成为男人,不敢和父亲竞争。最初的俄狄浦斯幻想会一直保留在人的潜意识当中,并且随着年龄的增长发展为更高级的形式,对人的精神生活、性格形成、性活动的形式和对象等等各个方面产生重大影响。
这些理论,我没有说给左岸听,也没有给他提出什么建议,作为从事精神分析的心理治疗师,我相信每个人都具有自我成长的力量,我所做的只是给左岸提供一个时间与空间,一个有安全感、受接纳的谈话氛围,让他能自然地主动地将自己的内部语言表达出来,这种表达,是一条他对自己潜意识里的东西进行发掘、释放、梳理和处理的途径,更是一趟漫长而艰难的心灵之旅,这趟旅程对于左岸的意义无异于重生。
左岸自述:
小时候我身体很弱,性格也很文雅,像女孩子一样,所以别的男孩子总是欺负我。记得有一次,他们将我的帽子撸下来,扔到了屋顶上,我哭着跑回家,母亲正在洗衣服,我以为她会将我抱进怀里,安慰我,但是她只看了我一眼,说:
“打架了吧?快去擦擦脸!”父亲听见了,过来劈头给了我两巴掌:“哭哭哭!你这眼泪怎么像自来水一样!哪像个男孩子,一点出息都没有!”记得那一天,我坐在厨房里,哭了很久很久,特别特别伤心和无助,我多么渴望能有人保护我,一个强壮的哥哥,或者是一个慈爱的父亲,用他们有力的臂膀将我温柔地抱进怀中,不让我受一点儿伤害。
似乎从小我就有这样的幻想——我躺在一个中年男人的怀中,他环抱住我,是那样的温暖与安全。长大以后,这样的幻想让我激动,我总是控制不住自己手淫,可是在快感之后,我又感到特别地自责与痛苦。
对于女性,对于女性的身体,我反倒没有什么感觉,就连我交的那个女朋友,也不是我心甘情愿的,而是我觉得自己都这么大了,再不交女朋友,别人会发现我的不正常。现在想想,真是挺对不起她的。
在和左岸的接触中,我能感觉到他身上有许多女性的特质,比如敏感、脆弱、害羞、渴望安全感等等,这是因为在父亲强大的压力下,他所有作为男性应有的意识尚未完全觉醒就已被扼杀在摇篮中,所以,从心理上来说,他更像是一个女人。
在大约进行了三四次心理治疗之后,左岸说他这段日子对中年男性的性冲动越来越少了,但我很清楚,这并不意味着他真的好转了,而是他将情感从他幻想中的中年男性身上转移到了我身上,因为在我这里,他可以获得从幻想中的中年男性那里不曾获得的平静、力量、支持和关怀,这是心理治疗中经常出现的现象。这时候就要求心理治疗师有足够的清醒和理性,一方面,要敢于走进患者的情绪中,敢于成为他(她)情感的寄托,敢于成为他(她)生活中的一部分;
另一方面,要保持自己的中立位置,不要被患者的情绪牵着走。比如在左岸向我诉说父亲对他的暴力时,我能体会到他当时的心情,但我不能说:你父亲怎么这样啊?这对你太不公平了!这样说,表面上似乎是在给他支持,实际上只会让他更委屈更脆弱,我需要做的是帮助他理解症状背后潜意识当中的冲突,从而慢慢打开内心深处的枷锁。
随着左岸对我越来越信任与依赖,他的自我设防越来越弱,对自我内心的挖掘也越来越深。
左岸自述:
我七岁的时候,邻居家有一个阿姨,离婚了独自生活,她很喜欢我,有时候母亲要出去办事,就将我托付给她照看。
有一次,这个阿姨将我带到她的房间里,关上门,脱掉了裤子……她让我看她那个地方,还让我用舌头舔,我懵懵懂懂的,虽然不喜欢那样,但是为了讨好她吧,还是照她说的做了……她扭动着身体,脸上的表情是接近癫狂的,我很害怕,不明白平时和蔼可亲的阿姨怎么会变成这种样子。后来这样的事还发生了好几次,我越来越害怕,越来越反感了,似乎也知道这样的事是见不得人的,所以也没有对母亲说,但是以后母亲再让我去那个阿姨家,我说什么也不肯去了。稍大一点以后,我每次想到这件事都觉得特别恶心,特别后悔,有一种耻辱的感觉。对我而言,这种恶心和耻辱的感觉是和女性的生殖器联系在一起的,一直到现在,我都觉得女性的生殖器是很肮脏的。
我也不知道该怎样和女性相处,和她们在一起总是很别扭,有时候看着那些女孩子,一个个都挺好看挺温柔的,我会产生一种很奇怪的想法:她们脱掉衣服是什么样子?这样一想就觉得很恶心。有时候这样想着脸就先红了,所以我们单位的人都说我老实——一和女孩子说话就脸红,紧张得说不出话来。
左岸讲述的这件往事对他的负面影响无疑是很大的。性是一种本能,它需要一个合理满足的途径,很遗憾,这件事对于左岸来讲是一个严重的性的创伤,使得他无法通过一个正常的途径来满足自己的性需求,从而也使他丧失了和异性建立亲密关系的能力,再加上他潜意识里一直惧怕成为男人,这一切都有可能使他在性取向上出现偏差。
左岸自述:
现在有时候想想,真是对我的父亲恨之入骨,想不通他为什么要对我那样!
记得我都读初中了,有一次考试没考好,他让我自己抱着一只钟跪在楼梯口,要跪满两个钟头才能起来,楼梯口来来往往那么多人,我都要疯了,心里有一种强烈的想把那只钟砸碎、把一切砸碎的冲动,可是我不敢,内心的激烈斗争使我身体抖个不停,当然最终我还是没有砸碎那只钟,我不敢。但到现在我都清晰地记得那种愤怒得头几乎要爆裂的感觉。
别人都不知道,其实从小学到高中我都有尿床的毛病,而且一般都是在我和父亲有过冲突之后,我曾经为此苦恼不已,但这个毛病在我参加工作以后慢慢没有了,蛮奇怪的…… 一直在父亲暴力阴影下成长的左岸,内心压抑着巨大的愤怒和恐惧,“尿床”
事实上是他对父亲强权的一种无声又无力的反抗,这些愤怒和恐惧让他一直处于紧张、焦虑、胆怯、自卑和不安的情绪当中,这时候,给他一个表达的机会,让他通过表达从这些情绪当中解脱出来是很有必要的。
经过大约11次心理治疗以后,左岸告诉我他对中年男性的性冲动已经明显减少,而且现在也能时常想起女性的身体,想起那起伏的曲线,觉得也真是很优美的。
变化就是这样以悄无声息的姿态发生,这听起来似乎很神奇,因为在整个治疗的过程中,我大部分时间只是在倾听。只不过在倾听的过程中,我能清醒地把握谈话的分寸,判断他语言背后隐藏的内容,适时地变换自己的角色。我偶尔会说几句话,表示鼓励、理解和安慰,这些话都是极其简单和朴实的,比如“你这一次比上次进步了不少”、“看来你真的遇到了麻烦”之类,或者仅仅是一个关注的眼神,但是在当时那种特有的工作氛围当中,这些语言和神情往往就会产生神奇的力量。
运用精神分析法进行心理治疗是一个潜移默化的过程,就像是养育一个孩子一样,你不能指望一蹴而就,更不能拔苗助长,只能帮助他(她)一点点成长,一点点坚强,直到他(她)有足够的能力独立上路。一个称职的心理治疗师会清楚应该在什么时候撤出患者的生活。不过就目前情况看,左岸还远远不到那个时候,尽管一切都在向好的方向发展。
左岸曾经和我说:“每一次和您交谈,我都有一种蜕皮的感觉,每蜕去一层皮心里就舒服了一点,阳光就洒进来多一点。”而这,又何尝不是我们每一个人要做的功课呢?那些在过往的岁月中累积的创伤,一层又一层包裹着我们的心灵,像一只密封的茧,无边无际的黑暗与沉郁,大部分人的一生都有一段时间是被密封在茧里的吧?有些人可能就此绝望,而更多的人会在黑暗与沉郁中积蓄着勇气、力量和智慧,终将有一天,我们可以突破那层层封锁重重包围。到那个时候,我们的心会如破茧而出的彩蝶,向着阳光,轻盈地,自由地,展翅高飞。
少女神秘的“强暴恐惧”
文/卫亚莉
伪装的青春萌动
江云在我的斜对面坐下时,怯怯地只坐了沙发的前半部分,身子向前倾斜着,眼睛低垂,是个文静、纤弱的漂亮女孩。
我从预约电话中得知,她是某理工大学的大一学生。为她倒上一杯热茶时,我告诉她,初次来咨询的女孩都会有点紧张,她这才慢慢将身体放松了一些。
“真是有点难以启齿。”江云垂下眼帘,直直地盯着她自己的脚尖,沉默着,最后深深地吸一口气,断断续续地叙述:
这一年半以来,我一到晚上就特别害怕,尤其睡觉时,常常莫名地担心有人闯进来强暴我,其实只要冷静下来,就知道这种情况不太可能发生,因为学校的治安比较好,何况寝室共有8个女孩呢!室友们都睡得好好的,我的床铺又不在靠门的位置,甚至还从下铺跟室友换到上铺,可是,一睡到床上,我就不由自主地紧张,脑海里全是以前看过的女孩被强暴的电视镜头,觉得特恐怖。
我们学校男生居多,每次上公共课,看见教室里黑压压的一片男生,我的神经就绷得很紧。而且,男同学从我身边走过时,我也会很紧张,觉得很厌烦。每天上、下晚自习,我都必须有女同学陪伴着,不敢独自在校园里走,特别害怕男生从后面袭击我。
刚入学的时候,我跟室友相处得很融洽。由于我是唯一的本市人,她们好几次约我一起出校园走走,带领她们观赏城市的夜景,可我死活不敢去,害怕路上突然遭遇歹徒的强暴。但是,我这种担心哪好意思说出口,每次只能推三阻四,所以她们觉得我太不近人情了,结果关系越来越疏远。
经询问,江云明确说她从未被人强暴过,由此推知,她有“强暴恐惧”,属于恐惧症的一种。恐惧症的发生,一般与个性、认知偏差、经历的生活事件及心理应激密切相关。根据江云给我的初步印象,可判断出她个性比较敏感和内向,这可能是问题发生的心理基础,但还应该有一些外部因素的诱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