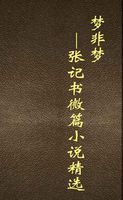嗜甜可能是家传,所以我也怀疑糖尿病是我们这个家族的宿命。不过现在看,很多吃得不甜的人也得糖尿病,我稍许心安。
在所有的调味品当中,白糖是唯一可以做零食的。小时候馋起来,直接从糖罐中挖一勺糖,含到嘴里,任一把甜蜜在口舌间粒粒地融化开来,化成一嘴浓甜的口水,舍不得直接咽下去。若干年后,在山东某个偏僻的乡镇上,我买一罐蜂蜜,用来拌豆奶粉喝,叫旅馆的老板娘看到,她说,你小时候一定是在家被惯得不行的孩子,吃这样甜上加甜的东西,还真不是一般的奢侈与纵容。
我以前不喜欢吃过于复杂的粥,有个情况可以例外,就是给粥里加糖,这个习惯,我弟弟比我还要恶劣。一碗红豆粥或者红米粥不加点糖,就不能接受那粥清淡的味道,我弟弟即使白粥也要加糖。那些物资匮乏的岁月,我们家的厨房里,唯一不能缺少的,怕也是白糖。因为我们兄弟俩的惦记,糖这个东西,代表着我们生活快乐的质量。
好多年后,我才在老婆那里学会,用红豆粥就咸菜。之前,我勉为其难地吃起放各种肉类与海鲜的粥。那些年,我游历各地,惊奇地发现,似乎也只有我们淮扬一带的人吃甜,北如山东,南如广西,全都没有在菜里放糖的习惯。以致我经常去吃的饭店,必定要为我专门买上一包糖。
记得那年在桂林,有一个据说抗战中日本人也没有兴趣搭理的偏僻乡村。我和一个朋友结伴去拜访他在那里的卫生院做护士的女同学。看上去路途不远,但车在蜿蜒的山路上盘旋了几个小时才到,下车刚到那个卫生院,正碰到人家在做饭,我自告奋勇炒个肉丝,东西准备好,才发现没有糖。那个女孩子倒是很干脆利落,说我给你去找,跑出去不大一会,抱回一个类似石板样的家伙。听她介绍,我才知道这叫黄糖,用刀背好不容易敲下一块,也不知道甜度,随便放了一点,就让那个肉丝如愿以偿地毁在我手里——甜得连我也进不了口。
那个乡村,宁静的中午,我们围着吃不下去的肉丝谈笑,许多村里的年轻人过来看我这个外地人,后来一个年纪略大的女子跑过来,边跑边问:江苏来的人在哪里?
我说我是,她一把抓住我的手,问你认识我的姐姐吧,她也在江苏。我问江苏哪里,她说:“常州。”是的,我无法解释我这个长江北面的人如何会认识一个长江南边城市的女子,世界在他们眼睛里也许是婉约而袖珍的,这个吃甜的外地人,也必然应该认识所有外地的其他人。我们在大笑中结束了这个很难延续的话题,那些不会再见的陌生人们,在彼此记忆中,如戴望舒的诗一样“过客在往昔生活了一瞬”。
情僧苏曼殊好吃糖,结果满口牙都被虫蛀掉,后装上金牙,但仍嗜糖如故。有一天,他糖瘾上来口袋里却无钱,于是干脆拔下口中的金牙来换糖吃。章士钊为此还特意写了一首诗调笑他,诗曰:“齿豁曾教金作床,只缘偏嗜胶牙糖;忽然糖尽囊羞涩,又脱金床付质房。”而著名连载小说名家包天笑,更曾有一诗调侃苏曼殊的嗜糖:
松糖桔饼又玫瑰,甜蜜香酥笑口开;
想是大师心里苦,要从苦处得甘来。
所以我觉得,爱吃甜的人,也确实达观得可爱。
至于京剧大师尚小云,1949年后将珍藏的字画玉器全部捐献。文革时又被抄家穷到潦倒时,仅有的家当是三个碗六根筷,游街示众还会“被人揪住四肢,像扔东西一样扔上大卡车,回來时又被人一脚从车上踢下來”,唯一“好处”是凡有大人物被批斗,都拉他去陪斗,被打骂一番后赏三分钱,他拿一分买咸菜,两分买白糖。
咬着咸菜,还惦记着那缕甜味。达观,是糖分修炼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