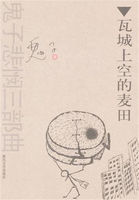男人身体在崩盘的瞬间,所有的狂欢参与者都停止了动作,定格为某一个造型——那些骨灰盒重新老实地趴在了那里。红绸布盖上去的时候,外面刮起了风,铁海感到一股阴风直刺腰间,顺着腰眼进入了慵懒的身体。
他不由得打了一个寒噤。
“怎么?怎么啦?”
“有点儿冷。”铁海没有撒谎。
杨茉莉伸手抓起毛毯,盖住了他的身体。她的臀部偶尔还蠢蠢地扭动一下。
月亮从云层后走了出来,屋子里挤进一丝光亮。
十二
入冬的时候,杨茉莉经营的歇斯康出了问题。作为一种消炎药,如果患者连续服用三盒,无论男女,其肾功能都将大大衰竭,轻微者视力下降,严重的可能从此失去生育能力。市药监局已经下文,明令市内各医院暂停使用歇斯康。
杨茉莉有些后怕,但是她手上还有十箱子二十万块钱的货。她很不甘心。
找到于雷,于雷说没办法,损失二十万吧。杨茉莉就骂于雷没用。于雷也勃然大怒,骂杨茉莉掉在钱眼儿里去了,“竟然连老子死活都不管了”。杨茉莉悻悻而去。
去找铁海。铁海眼珠一转,答应说试试。然后他找到卫生局长,如实说明情况,让局长下令县城最大的一家医院把“我表妹”的药接过去,损失由医院担着。当时,局长立刻面露难色。“小铁,这可是掉脑袋的事,你有这个胆量,我没有。”
铁海说:“512医院的门诊楼不是要改建吗?”
卫生局长没明白什么意思,“是啊。”
“不是指望县里出点钱吗?”铁海又问。
卫生局长还是没明白什么意思,“是啊。”
“研究时书记那儿多给点儿,不好吗?”铁海再问。他心想,卫生局长大概还不知道自己已经是县委书记的秘书了。
卫生局长终于明白了。他并非不知道铁海的书记秘书的身份,只是他胆子太小,脑子缺乏想象力,一时没有搞清铁海的意图。“你瞧我这脑子,真朽!农村出来的,反应就是慢。”
“局长您别客气。我也是山里出来的,一样,都一样。”
“铁秘书,这么着好不好?你让书记跟我打个招呼,我好跟下面说。”局长既然承认自己是农村人,就拿出了农村人最大的实在和执拗。
“那不可能。我这么看这件事,平常我们受领导关心,关键时候我们应该保护领导。这是我的原则,您说呢?”铁海往犄角旮旯逼局长。
局长的脸顿时就有些红,后来又出了点儿汗。
“您别有顾虑。我早想好了,这十箱子药咱们不用,可以捐给灾区呀。”铁海懒得跟他周旋了,当即摊出底牌,“张家口不是地震了吗?灾区缺医少药,咱们把这些药像手榴弹一样扔过去,对他们是无私的捐助,有什么问题呢?”
“可是人家……”
“一人一盒药都摊不上,吃不死人!而且,这种药在河北省不是还没禁吗?”
卫生局长终于“投降”了。
当天下午,铁海把好消息告诉了杨茉莉,杨茉莉激动万分:“铁哥,太棒了!你对妹妹太好了!”
铁海得意地说:“那是!是不是特绅士?”
杨茉莉说:“岂止绅士?简直爷们儿!纯爷们儿!”
回到家里,杨茉莉把事情告诉了王稼轩。王稼轩大惊失色,“这、这……怎么行啊?!缺德的事儿啊!”
“缺什么德?保准没问题……铁哥简直太义气了!”杨茉莉不耐烦地说,在丈夫面前都没忘了夸一次自己的“铁哥”,“铁哥太棒了!”
“不好!我觉得不好!”正派而胆小的王稼轩忧心忡忡,他再次大胆地提出质疑。但是,仅仅是质疑。他没有足够的力量去推翻自己心爱的妻子的任何的主张。
“春节放假,咱请他去趟海南。怎么样?”
“咱?”
“你我,他们俩。咱们掏钱。”
“那……当然行。听你的。”王稼轩在金钱上绝不抠门儿,同时也知恩图报。
而铁海,根本没向小丫提卖药的事。相反,他从妻子那里听到了一个令他吃惊的消息:诸葛小丫把杨茉莉给的回扣统共两万四千块钱,一分不差地,捐给了张家口地震灾区。
“全捐啦?!”铁海瞪大眼珠子问。
诸葛小丫点点头,等待着丈夫的表扬。
“嘿——,你!你可……真有你的!”铁海气得牙根子直疼。但是他忍着疼痛,脸上尽量欣慰着,狠狠地给妻子挺了挺大拇哥,然后立刻走到另外一间屋子,朝着墙壁狠狠砸了一拳。
十三
原计划大年初二出发,连来带去在海南待上五天,初七飞回,初八上班,但是到了大年初一,县委书记突然从美国通知铁海代他陪客人。腊月二十六书记就到纽约了,他国内的一些同学要来郊区过年,就闹着书记从美利坚遥控安排。铁海本来特渴望踏实地过一个年——为此他甚至把乔老板的邀请都推掉了——没想到书记下旨,也只好牺牲掉节假日了。
“真讨厌!不是说好的吗?”杨茉莉在电话里埋怨。
“没办法,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啊。”铁海无奈地答复。
“那怎么办?机票都订好了。”
“退掉我的那张,你们去吧。”铁海语气坚定,绝不拖泥带水。
杨茉莉在电话里沉默了三秒钟,“我也不想去了。”
“那怎么办?”
“我留下来陪你。”
“你是说让他们两个人去?”铁海很惊讶。
“是啊!你不放心吗?”杨茉莉很诡谲。
“哪儿的话?我怕你不放心你们家王稼轩。”
“既然咱们都放心,那就让他们去好了。一个旅游团又不是只有他们两个人。”
“就这么定了。”铁海斩钉截铁。
回到家里,两个人把这个临时改变的计划告诉自己的妻子和丈夫,妻子和丈夫都表示反对和担心,经过一番劝解,他们才勉强接受。
“你不去,我去,有什么意思?算怎么一回事?”诸葛小丫说。
“我不是有公务吗?你以为我不想去呢!没关系,杨茉莉也是一番心意。何况你们也是朋友。”
“问题是,她也不去呀!”
“她姨妈死了,她总得陪陪她母亲呀。”铁海撒谎道。这句谎言出口后,他有些想笑,但咬了咬嘴唇子,硬是忍住了。
“她姨妈死了?我怎么没听说。”小丫睁大眼睛问。
“今天上午的事情。才四十八岁。”铁海撇着嘴说,以显示他的同情,“挺好的一个人呢。”
“嗛,好像你认识人家似的。”诸葛小丫带着闺怨讽刺道。
“你想啊,四十八,肯定是挺好的一个人!”
“我问候一下吧。”小丫伸手去摸手机。
“歇着吧你!”铁海立刻制止道。他不想让杨茉莉被小丫问得傻啦吧唧的,那样非露馅儿不可。“人家全家正乱着呢!问候也得找个时候。”
诸葛小丫只好把手机放回茶几上。铁海又劝了几句,小丫答应去海南了。
同样,在另外一个家里,杨茉莉也说服了王稼轩。
王稼轩头句话就是:“我去海南你怎么办?”他觉得妻子离开他简直没法生活。
“没关系,我去妈家吃饭,住那儿也成,全托!”杨茉莉把自己当成一个儿童,把王稼轩母亲的家当成幼儿园,她觉得这样表达一定会让丈夫放心。
果然,王稼轩的脸上有些释然,但是好像又有了新的忧虑。“问题是……”
杨茉莉有些不耐烦,她抢过话,“嗨,不是我不想去,还不是为了生意吗?要不是为了那批骨灰盒,我干吗不去海南晒晒太阳啊?!”她说自己没法去海南,理由是春节期间老干部局可能“要货”。“冬天老天爷本来就爱收人,你又不是不知道。关键的是,七八个得了癌症的老干部已经奄奄一息,也就是三五天的事了。”
“让他们提前买上不就得了。”王稼轩瞳孔里的幼稚毕露无遗。
“哪有提前送骨灰盒的?只有老干部一死,才能写请示打报告买骨灰盒,这事才能提上议事日程。”杨茉莉振振有词,她无形中从铁海那里学到了许多撒谎的本领。
“那……以后再去海南不成吗?反正这次铁海那小子也去不了。”王稼轩还是不情愿离开妻子。
“他去不了就去不了,诸葛能去就行。反正诸葛也没少帮咱忙。”杨茉莉把一张信用卡掏出来,扔到王稼轩面前,“拿上这张卡,想买什么就买。”
见杨茉莉沉下了脸,王稼轩只好听命。末了,他心血来潮,跟妻子开了个玩笑:
“让我和诸葛出去,你这么放心?!”
“嘿——!”杨茉莉被这突如其来的一问弄愣了,继而她莞尔一笑,走到丈夫跟前,揪住他的鼻子,“你敢?!舌头给你割喽!”
王稼轩幸福地抱住了杨茉莉。
到海南的第一天,旅游团就遇到了一个问题:晚上打骚扰电话的特多,甚至有直接敲门的,你不开门她就不走;开了门更不走,坐在床头“忽悠”着想跟你上床,直到确认了枉费口舌才拂袖而去。
第二天上午,团友们就跟导游提意见,说不是说没有这种情况了吗?怎么还有?大家提议换酒店。导游忙解释,说毕竟是海南,好多年的特色一下子也绝不了根儿。导游态度还不错,恳切地说换酒店也不那么容易,还要跟旅行社计调部商量,计调考虑换酒店会赔偿酒店损失,所以同意的可能相当小。最后,她教了大家一招儿:晚上,女团友到男团友房间打牌,遇到骚扰电话了女的接,那边儿立刻就会挂了。大家只好点头赞成。
这时,车上一个胖胖的男团友问:那边打电话的要是男的呢?
导游说:不可能。
胖子说:女同志也是人,也需要服务啊!
车上哄堂大笑。
王稼轩侧脸瞟了眼诸葛小丫,小丫的脸已经红了。那个胖子跟王稼轩同室,坐在他们前面一排,这时,回过头看了眼王稼轩,王稼轩立刻说:“除了你没人打电话。”车上又是一阵笑声。
“诸葛美女,我冤枉!”胖子转而看诸葛小丫,做了个无辜的表情,“说说你们家的,不许他侮辱人。”
“别瞎说……”诸葛小丫被胖子的表情逗乐了。
“行,看在美女的份上,我暂且饶了你。”胖子冲王稼轩挥了挥拳头。
就是这个有趣的家伙,本来可以跟王稼轩和诸葛小丫成为朋友的人,后来办了一件傻事,令王稼轩十分不齿。
第三天晚上,三个人加上小丫的室友,一起出去吃宵夜喝啤酒。席间,胖子巧言令色巧舌如簧,撺掇诸葛小丫喝酒。诸葛小丫碍不过面子,加之对胖子的好感,就喝了两杯。喝前,她没忘了征求一下王稼轩的意见:怎么样,要不我喝一杯?——好像他是她的丈夫。
王稼轩被这一问弄得很温暖,立刻有了一种很责任很特别的感觉。“喝上一两杯也没关系,你自己把握。”王稼轩说。他看得出她很高兴,有一定的兴致。于是,诸葛小丫就喝上了。
“美女,你是山上的甘泉/我额头的沧桑/渴望你清冽的流淌//美丽地划过/音乐叮咚/仿若天籁。怎么样,我敬你一杯。”胖子原来是一诗人。诗人劝酒时充分展示他的诗才,诸葛小丫挺开心的。
“美女,你是天上的太阳/我心中的阴霾/愿得到你的垂青/无情的照耀/阳光灿烂/春光无限。我喜欢连干三杯,第二杯。”
诸葛小丫真的很高兴了,就又干了一杯。
“诸葛大姐,我黔驴技穷了,没诗可写了,别笑话我。我仅以我这颗比紫檀木还实在的心,敬您一杯。”胖子的表情十分夸张,小丫呵呵笑着喝了第三杯。
“得,够意思。不跟美女喝了。来,王稼轩,咱俩喝,也是三个。”胖子说。
“有你这么喝的吗?逮着一人就先来三个?”王稼轩笑着举起杯子。
“喝酒也要分出层次,搞倒一个是一个。”胖子说。
“谁搞谁呀?你整个一葫芦岛人喝酒,”王稼轩也觉得胖子很有意思。“不管别人好不好,先把自己抇撸倒。”
“待会儿也要跟我喝三个吗?”小丫的室友——另外一个女人问。
“那是。不这么喝我喝不醉。”胖子大手一挥,仰脖就往嘴里灌。
“哎,诗人,给我作首诗呀!”喝一半时王稼轩忽然说。
“操,你哪配呀!一个傻老爷们儿,我没灵感。”胖子大大咧咧有口无心道。他瞟了眼诸葛小丫,小丫脸上美滋滋的。
“什么人呀?!”王稼轩把剩下的半杯也喝下去了。
轮到跟另外那个女子喝时,那女子缠着让胖子作诗,胖子结巴着说:“不……不行,多、多了。”
“不写诗也行,咱们喝六个。后三个算我回敬你的。”女子说。
“行。六个。”胖子答应。
“我也敬你三个。”这时,诸葛小丫说。
“你不能再喝了。”王稼轩小声阻止她。
她立刻伸出手碰了下王稼轩的手,小声说:“我知道。逗逗他。”
王稼轩很激动,手上立刻有了一种触电似的感觉,有些心猿意马。
回酒店后,几个人照例到男士屋里打牌,刚打了几把,诸葛小丫就撑不住了。她跑到洗手间里呕吐。王稼轩跟到洗手间里,嗔怪道:“没有金钢钻就别揽瓷器活!吐吐吧,吐出来就好了。”他伸出手,准备在小丫的后背上拍一拍,但是他犹豫了,胳臂在空气中定住了……他喊了一嗓子小丫的室友,让她过来帮忙。
按理说,一个说京韵大鼓的也算文艺界人士了,是不能信奉“男女授受不亲”的,可王稼轩偏偏就挺传统,连给女性拍拍后背的勇气都没有。从内心深处讲,王稼轩并不反对一个男人一生有一两件风流事,但是他坚决反对从朋友那里——或者妻子的朋友那里,有任何觊觎和贪欢。
在王稼轩总记不住名字的那个女人的帮助下,诸葛小丫吐了几口秽物,然后要回自己屋子里。胖子“嗖”地走过去,扶住诸葛小丫的另一只胳臂,“都是我的错,罪孽!罪孽!”诸葛小丫笑着说:“不怪你……长这么大,还是头一回喝醉,挺好玩的。”
五分钟后,胖子和女人又回来了,还带来了另外一个人。四个人继续打牌。
半小时后,胖子说受不了蚊子的肆虐,要出去找服务员要蚊香。蚊香他倒是要到了,但是他没回自己屋子,而是以“我爱人最怕蚊子咬”为由,让服务员打开了隔壁诸葛小丫的房间,然后他冲服务员说了声“谢谢”。
三分钟后,屋子里传出一阵尖叫和求救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