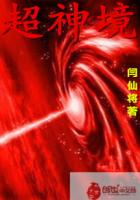这就是少校给我说的那个故事,我现在尽量照我所能回忆的叙述出来:
1873年秋天,我在康涅狄格州新伦敦特伦布尔要塞当司令官。我们在那儿的生活也许不如在前线那么丰富;不过那儿有那儿的情况,基本还算是丰富的——我们头脑并没有因为有什么情况促使它经常紧张而闲得发呆。就说一件事情吧,那时候北方的整个天空充满了神秘的谣言——谣传叛军的间谍到处神出鬼没,准备炸毁北方的重要设施,烧毁我们的电站,把带有细菌的衣服运送到到我们的城市里来,以及诸如此类的事情。这个你都记得吧。这一切都足以使我们经常提高警惕,打破驻防生活一向的沉闷。除此之外,我们那儿还是个招募新兵的地方——这也就是说我们简直不能浪费一点时间去打瞌睡、或是做梦、或是游手好闲。咳,我们尽管看得很严,每天招来的新兵还是有一少半人从我们身边溜,有的当天夜里偷跑了。入伍的补助非常大,以致个别新兵可以拿出两三百块钱贿赂看守的兵,让他逃跑,结果他所得的补助费还可以剩下不少,对于一个穷人来说也是一项收入。是呀,就像我刚才讲的,我们的生活并不沉闷。
那么,有一天我独自一人在营房里正在写材料的时候,有一个年轻小伙、脸色苍白、穿得很破烂的径直走进来。他规规矩矩敬了一个礼,说道:
你们这是招新兵的地方吧。是的。您能不能收下我呢,长官?
不行,不行,你的岁数太小,而且个子也太矮。他一脸稚气现出失望的表情,很快就变得更厉害,成为一种丧气的表情。他扭转过身去,似乎是要离开似的。他犹豫了一会,慢慢转过身来对着我,用一种使我深深感动的语调说道:我没有家,在这里无亲无故。我真心希望你能把我收下!
可是这事情是绝对不可能的,我就极力温和地给他讲明这个道理。然后我叫他在火炉旁边坐下来烤烤,并且还补上了两句:
我这就去弄点东西给你吃,饿坏了吧?他没有说话,也无须回答;他那双柔和的大眼睛里的感激神情比任何语言都更能说明是这样的。他在火炉旁边坐下,我继续写材料。偶尔我偷偷地望他一眼。我看出他穿的衣服和鞋子虽然很破旧,可是样式和材料却很好。这一点挺耐人寻味的。除此之外,我还发现他说话时轻声而悦耳;他的眼睛深沉而忧郁;他的举动和言谈都很文雅;我是个可爱的小伙子,肯定是遇到了麻烦。于是我十分同情他。
可是我又开始专心写我的材料去了,完全忘记了那个小青年。我不知道这样过了多大工夫,后来我才偶然抬头看了一眼。那孩子的背向着我,可是他的脸也稍微侧过来一点,所以我可以看得见他的一边脸蛋——一道无声的泪珠正在顺着脸上淌下来。
哎呀,太粗心了!我心这么想:我大意了,小可怜虫的肚子肯饿坏了。于是我为了刚才的大意向他表示歉意,就对他说,跟我来吧,小朋友,你和我一块儿吃饭吧,今天就只我一人。他又那么含着感激的目光向我望了一眼,脸上露出一点灿烂的微笑。到了餐桌旁边,他把手扶着椅背站着,一直等我坐定了,他才坐下来。我拿起刀叉——唉,我只好拿着不动,因为这孩子低下了头,默默地在祈祷。许多有关过去的联想和童年的圣洁的回忆浮现在我的脑海,我不禁悲叹地想起我已经与宗教漂离了很远,它对受了创伤的心灵的医疗作用,以及它的安慰、解脱和鼓舞的作用,都与我无缘了。
在我们吃饭的时候,我看出了年轻的汤普森——他的全名是沃尔特·汤普森——知道怎样使用餐具;还有——唉,总而言之,我感觉到他是个很有教养的孩子,详细情况不用细说了。从他言谈举止中看到一种纯朴态度,这也使我很中意。我们谈的主要是有关他自己身世,我直截了当地向他问清楚了他的来历。当他谈到他的家在路易斯安那的时候,我显然对他更加同情,因为我在那边呆过一段时间。我对密西西比河近海一带都非常熟悉,又特别喜欢那个地方,离开那儿没有多长时间,所以我对它的记忆还没有开始淡下来。连他嘴里说出来的一些名字都叫我听了很愉快——正因为觉得非常愉快,所以我就有意把话题引到某些方面,使他多讲出一些这类名字来。利奥尼达、斯迈利、克莱斯勒、五十里铺、克里托弗、小码头、卡迪拉、货轮码头、汽轮码头、洛克希德、凯洛格街、堤坝、坏孩子街、哥伦布旅馆、里卡多草场、大马咱、欧茨克湖;特别使我愉快的是再听到马将军号、托特号、月光号、卜克纳将军号、乔·布什号,还有以前一直很熟悉的别的轮船的名字。那简直就像是故地重游一样那样高兴,这些名字使它们所代表的事物很生动地重新活现在我心头。简单点说,小汤普森的身世是这样的:战争爆发的时候,他和他的有病的姑母和他的父亲住在克里斯托弗附近一个富丽的大农场里,这个农场属于他们这一家已经40年了。父亲是个联邦统一派。他受尽各种的迫害,但是始终坚持他的立场。后来终于有一天夜里,一批蒙面的歹徒烧毁了他家的房子,他们一家人就不得不逃命。他们被人四处追杀,尝尽了一切饥寒交迫和苦难的滋味。害病的姑母再也坚持不住了:困苦和风吹雨打的流浪生活把她折磨死了;她像一个流浪汉似地死在露天的田野里,雨飘在她身上,雷在头上轰隆轰隆地响。没过多久,他的父亲又被一伙武装分子抓走了;儿子一面在旁边告哀求饶,有好些人在他跟前活活勒死了。(说到这里,这小伙子眼睛里闪出悲惨的泪光,他以自言自语的语气说道:如果不让我当兵,也无关紧要——我还会想出其它办法——我还会想出其它办法。)那些人宣布他的父亲已经死了之后,叫他马上离开,他要是在12小时内没离开那个地方,他也要遭殃。当晚趁天黑他就悄悄地跑到河边,在一个大农场的码头上躲藏起来。后来,乔·布什号在码头停下来了,他就泅水过去,藏到它后面所拖的一只小船上。天还没有亮,船就开到了汽轮码头,他偷偷地上了岸。那地方离洛克希德很近,他徒步走了这段路,走到坏孩子街他的一个叔父家里,这才结束了他的苦难生活。可是这个叔父也是一个联邦统一派,过了没多久,他就打定主意,还是离开这个地方。于是他就和汤普森搭上一只帆船悄悄地离开了那里,不久就到了纽约。他们在布鲁纳旅馆住下来。年轻的汤普森暂时过了一段愉快的光景,经常到唐人街去闲逛,看了不少北方的奇花异草;但是后来形势发生了转变——而且并不是好转。他的叔父起初还很高兴,现在却开始显得愁眉苦脸;另外他脾气越来越坏,动不动就摔东西,要想法子怎样赚钱——剩下的钱连一个人都养不活,两个人就更不用说啦。后来有一天早上,不知他去哪——早饭也没来吃。这孩子到账房一问,才知叔叔头一天晚上就付清了账走了——旅馆里的服务员告诉他可能是到波士顿去了,可也不敢确定。
这孩子独自一人,无依无靠。他几乎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思来想去,还是决定到波士顿去找一找他的叔父。他赶快到轮船码头,才知道他口袋里剩下的那一点点钱不够他到波士顿去的路费,不过到新伦敦去还可以;所以他就买了到伦敦的船票,决定靠老天保佑,让他能有办法渡过其余一段路程。现在他已经在新伦敦的街上晃来晃去地游荡了三天三夜,靠别人发善心四处要点剩饭,晚上在大街边躺一会。可是后来他越来越灰心,感觉真得没有希望了。后来就想起当兵,假如能当上兵,那就真的太感谢了,如果当兵不够格,让他当号手,也还可吧?呵,他情愿拼命拼命地干,使人满意,并且还感激不尽!
小汤普森的来历就是这样,除了细节之外,都是和他对我说的一样,我说:
孩子,你现在就算到家了——你再也不用发愁啦。这下子他的眼睛立刻闪出光芒来!我把邦克·努森上士叫进来——他是哈特阜人;现在还住在哈特阜;你也许认识他——我对他说:努森,叫这个孩子和军乐队的弟兄们住在一块吧。我打算收下他来当个号手,你要好好照顾他,千万注意别叫他受到任何伤害。
那么,要塞司令官和小号手之间的交涉到这时候就是告一段落了;可是这个可怜虫、无依无靠的小家伙仍旧在我心头牵挂着。我时刻提心,老希望看见他高兴快活,变得心情愉快;可是枉然,日复一日,他还是那个样子。他和谁也不来往;老是心不在焉,老是在想;他的脸色总显得忧虑。有一天早上努森请求我和他单独谈话。他说:
我希望您不会见怪,司令官,不过现在的情况是这样,军乐队的弟兄们几乎快要死了,好像非有人出来说话不可似的。咦,到底是怎么回事?
是汤普森那孩子,司令官。军乐队的弟兄们把他烦透啦,您想不到已到了什么程度。
好吧,你说下去,说下去。他都干些什么?老在祷告哩,司令官。
祷告!是呀,司令官,这孩子每天都祷告,弄得军乐队的弟兄们总是不能安宁。早起第一件事,他就是祷告;中午也差不多一样;晚上——唉,整夜整夜地他就像是着了魔似的,把别人弄得心神不宁!睡觉吗?哪能睡得着觉;照一句俗话说,他那苦心祈祷的风车转开了,他转开了头,就停不下来。他先从乐队长开始,给他祷告,接着就是号手头儿,又给他祷告;再接着就是低音鼓手,他甚至引着他也祷告起来啦;一个接一个,整个乐队都要轮到,一个不少都给认真地祷告一番,而且他那种认真的样子会使你觉得他自己以为在人间活不长了,总想着去西天的时候带上一个乐队一块去,所以他要给他自己挑选乐队,好让他们在天上叫他信得过,奏起国歌来奏得能配上那儿的场面。唉,司令官,往他那儿投靴子也不管用;屋子里是黑的,并且他又不光明正大地干,老是躲在大鼓后面;因此大家一急就把靴子朝他扔过去,也没惊动他,他毫不在意——照样颤悠悠地祷告,就好像那是人家给他喝彩似的。他们大声喊起来,“快,停下来吧!”“让我们休息一会吧!”“揍死他”“啊,让他滚出去!”以及诸如此类的话。可是还是不顶用。简直就惊动不了他,他干脆就不理。停了一会又说:真是个认真的小傻瓜;清早起床就把那满地的靴子拣回去,再一对一对挑好,放到各人的床头。这些靴子丢过去打他已经丢得次数太多了,所以全队的靴子他全部认识——他就是不睁眼也会挑出来。
又停了一会,我忍住没有打岔。但是最叫人不能忍受的是他祷告完了的时候——他要是居然有个完的话——他就清一清嗓子唱起歌来。唉,您知道他说话的声音柔声细气多么好听;您知道他那种声音简直可以引得一只铁铸的狗从门口台阶上跑下来舐他的手。可是您要是相信我的话,司令官,那他说得没有唱的好听!比起这个孩子的歌声来,吹笛子的声音都显得刺耳。啊,他就在那黑暗中像高山流水一样地唱,低低的声音是那么柔和悦耳动听,简直叫你觉得有点飘飘然了。
那又怎么会“叫人受不了”呢?呵,问题就在这儿,司令官,您听他唱吧。就像我这样——贫穷、倒霉、眼睛又看不见——您听了他唱这个,只要细心一听,就会感觉浑身都发酥,眼睛里会含着泪水!不管他唱什么,都是一直钻进你心窝里——深深地打动你的心——每回都叫你神魂颠倒。您只要听听他唱:
我要找到你,不管南北东西,真觉会给我指引;爱上你别问什么原因,第一眼就能够认出你——听这些歌,让人觉得心里总有点酸酸的感觉。他唱起他那些关于家乡、关于母亲、关于童年、关于从前的回忆、关于烟消云散了的事情和关于死去了的老朋友的歌来,就把你以不值得怀念或不堪回首的往事都引到你面前来了——那才真是唱得漂亮,唱得出神,叫人心潮翻滚,司令官——可是,天哪,那才真让人伤心之极哩!军乐队——唉,他们个个泪流满面——这些家伙个个都哭出声来,而且毫不掩饰;给您这么说吧,就连以前用靴子打孩子的那人也被他的歌声感动了,一下子又从床铺上跳下来,在黑暗中跑过去拥抱他!是呀,他们就是这样——还拼命和他亲吻,弄得他浑身都是唾沫,并且还用亲爱的名字叫他,求他原谅。在这种时候,如果再有人敢拔小精灵一根汗毛,他们就会扑上去和这些人拼命!
又停片刻。就是这些话吗?我说。是的,司令官。
哎呀,原来如此,那有什么可埋怨的!他们想要怎么样呀!
怎么样!唉,就是请你出来阻止他唱歌。你们咋能这样呢?刚才不是说他唱的精彩吗?问题就在这儿。唱得太精彩啦,一般凡人真是受不了。他唱的大家心驰神往,撕心裂肺;简直把人的心都挖走了;它把他的感情捣得粉碎,使他心里很不舒服,觉得自己有罪过,除了到地狱去谢罪之外,什么地方也不配去,叫人老是忏悔个没有完,什么都显得不对劲,觉得人生一点意思也没有。还有那个哭劲,您瞧——大家都跟着擦眼抹泪,唱到伤心处,竟有人号啕大哭。咳,这倒是个新鲜事,告状也告得奇怪。那么他们当真要叫他不要唱了吗?是呀,司令官,就是这个意思。他们也不愿意太多要求;要是能叫他不要再祷告了,或是叫他不要祷告起来没有完,那他们当然是太感谢了;不过最主要的还是解决唱的问题。只要能把他那唱歌的嘴堵住,他们觉得祷告还可以勉强接受了,虽然老让他那么用祷告来折磨,也实在是难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