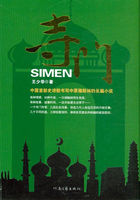这些念头,应力民只是心里暗自忖度一下而已,尽管都是老知青,当年插队在不同的公社,不同的村寨上,并不熟悉,不少人都是回沪以后,在知青联谊会和各种名目繁多的聚会中相识,说到底互相间的关系都是很客气的,相互之间真正知根知底的不多。
丘维维双手撑在轮椅上,目光斜乜着罗幼杏,轻飘飘地道:“你当初一条道走到黑,和何强一直好下去,也不会是今天这副样子啊。”
“我哪想得到啊,”罗幼杏一脸的懊丧,“你凭良心说说,丘维维,插队落户时好上的,有几对今天成了夫妻的?”
汪人龙笑道:“那你也不要说得这么肯定,安康青和丘维维,眼面前不就是好好的一对嘛!”
罗幼杏的手指向丘维维,又指一下安康青,不无刻薄地把脸转向汪人龙:“你问问他俩的心里,是不是像你说的那么幸福。哼,不要以为我不知道。”
说完一甩手,抽身就走了开去。
人堆里一下冷了场,沈迅凤凑近汪人龙的耳根,悄声说:“这人怎么了?像有毛病。”
汪人龙扯一下沈迅凤的衣角,嘀咕似的道:“知青之间的事儿,你别管。走,我们也逛逛工艺品店去。”
众人四散走去,应力民跟前又安静下来。从市区到浦东机场,是缉毒大队的警车掐着点送他过来的。下车后他拖着拉杆箱,只是抱歉地微笑着,朝众人点头算是打了招呼,刚才汪人龙带头走过来,让他和相识的几个男女知青一一打了招呼,也算作了弥补。其实他并没有迟到,只是这些平时较少出门的老知青到得太早。
现在安静下来,应力民透过落地玻璃,眺望着浦东机场宽阔无边的停机坪,心里渐渐平静下来。交代了缉毒大队的工作,他的脑际又浮起了盘旋多日的徐眉案件。
在为这次出差准备行装时,他特意打开了久未起封的樟木箱子。这只坚固扎实的樟木箱,是他在桂山地区插队落户时出钱请老乡打的。他离开上海插队落户时,家里只为他提供了一只人造革大箱子和凭上山下乡证花七元钱购买的一只红色的小薄皮箱。插队落户两三年之后,知青们兴起了购买樟木箱子之风,应力民起先按兵不动,只在跟家里通信时提及此事,并说山乡里樟木很便宜,老乡的木匠活儿也不差。没料到在螺帽厂当工人的父亲,用他只读过两年半小学的粗大歪扭的字体,给他写了一封回信,信中提到,新的樟木箱子,在上海几乎已经绝迹,可以出钱请老乡打一只真正的樟木箱。应力民花了三十五块钱,请老乡打出了一只樟木箱。调回上海工作时,应力民绝大多数东西都舍弃或是留给了同事,惟独把这只樟木箱托运回来了。和樟木箱一起托回上海的,是几本当年审讯了岑达成十几个月的个人笔记和会议记录。樟木箱托运回上海,已经退休的父亲说这只花了青工一个月工资的樟木箱买得值,在上海滩,起码值二百块。故而父亲又请厂里的徒弟,为樟木箱配装了铜角片和铜钥匙。改革开放以后,木箱子在家里已显得碍手碍脚,很多家庭都扔掉了。应力民舍不得丢掉这只箱子,这是他插队落户的纪念,也是已故父亲倾注了心血的箱子。应力民对自己的儿子说,只要我活着,这只箱子就要放在家中。我死以后,你看着不顺眼,可以把它扔出去。不料儿子叫起来,我为什么要把它扔掉啊,爸爸,这是爷爷和您留下来的,我还要把它留给我的儿子呢!应力民听了这话很舒心,他拍着儿子的肩膀说,这只箱子里,还留着一件离奇古怪案件的记录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