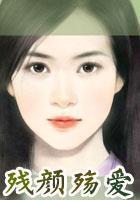“别人给的。”小桑的脸有点儿红。于思猜想这人是毛勇,就不再问啥。于思看着小桑一针一线地缝着,小拇指翘着。他想起了小丹,她叠纸玩意儿的时候,也是这样翘着小拇指。他的心里疼了起来,好像又有一块铅压在上面。他站起来往外走。临出门的时候,他听见小桑说了一句:“我妈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回来。”于思想说点儿啥,可又说不出来,他二意思思地关上了门。
外面有风,所有的树都在摇晃,发出哗哗啦啦的响声。地上铺满了落叶,厚厚的一层。一条胡同都变成了黄的,看不见一个脚印。行人不多,低着头的仰着脸的全都脚步匆匆。老范太太拎着菜篮子,从楼前走过来,倒腾着两只小脚,走得很吃力。
他不知道自己应该上哪去,被风一吹心里多少舒服了点儿。不知不觉,于思走到了解放广场的边上。树林子里的树全都黄了,深深浅浅地发出光泽。几棵枫树鲜红的叶子夹在里面,显得分外扎眼。落叶松几乎落尽了针叶,光秃秃分开深深浅浅间杂的黄色。
他是在绕过纪念碑的时候,看见“长脖子”的。他和一伙哥们儿,坐在花坛的沿子上,正比比画画地白话。一个夏天没见,“长脖子”长得人高马大的,足有一米八的个头,块大膘肥。他穿着黑的高领毛衣,外面套着海蓝色拉锁的翻领夹克。新理的头发抹着油,梳了一个大背头,看上去又精神又利落,可不是早先那个哼哧带喘病病歪歪的熊样了。围着他的人足有二十来个,全都穿得贼流。于思认出其中有三两个是街上的,其他的都不认识。大江也在里面,于思是在去年冬天,和“长脖子”去果窖批山里红的时候认识他的,他家就在果窖那边住。大江的妹妹叫小翠。有一次“长脖子”说小翠的奶头,像俩扣子似的那么点儿。“你咋知道呢?”于思问他。“我咋不知道?我熟悉她身上的所有地方。”“长脖子”笑着说。他们的手里都拿着家伙儿,棒子、镐把、二尺钩子,还有大煤钎子。于思知道他们的腰里,还别着火药枪、三棱刮刀和电工刀啥的。
“这回咱们得和刘瘸子见个真章!”“长脖子”吐了一口痰,撸着袖子说,“咱哥们儿不能老是让他压一头。让他牛逼,说啥他是镇街王!他是镇街王,咱们往哪摆呀?!”
于思听说“长脖子”和刘瘸子掰了,可不知道他俩咋闹到了这份儿上。看见于思,“长脖子”点了点头,咧开嘴乐了。“哪去?”他啐了一口唾沫问道。
“哪也不去。”于思答道。“那跟我们走吧。”“长脖子”说着扔过来一棵烟。
于思摆了摆手,还是接住了那棵烟。他用手指捏了捏那棵烟,看清楚是上海的“光荣”。他把烟叼在嘴里,舌头上觉出辛辣,赶紧又吐了出来。他看见那一伙儿人都在笑他,就把烟又叼在了嘴上。“长脖子”“啪”的一声打着了打火机把手伸到于思的跟前。于思凑上去,对着他的火抽了一口,烟头冒出红火,薄薄的蓝烟飘散开。他闻到一股香气,又吸了一口再吐出来。“你这叫抽的啥烟呀?”“长脖子”笑着说。于思从来没有注意过别人是咋抽烟的,就问道:“那你说该咋抽呀?”“你看着。”“长脖子”说着吸了一口烟,张大了嘴。于思看见烟正要从他的嘴里冒出来的时候,他猛地一吸,把烟吞了下去。他闭上嘴眯缝着眼睛,两道灰烟从他的鼻子眼里冒了出来。“得咽下去。”“长脖子”睁开眼说。于思也学着他的样子,深深地吸了一口,闭住嘴咽了下去。脖子里面像是挨了重重的一拳,呛得他剧烈地咳嗽起来,鼻涕眼泪一齐往下流,只觉得头晕脑涨,胸口憋得喘不上气来恶心得直想吐。“长脖子”说:“别张嘴,屏住气,往里吸,咽下去就好了。”于思不想再抽了,可又怕“长脖子”他们笑话他太嫩,就喘着粗气又吸了一口,他闭住嘴捏住鼻子,一口咽了下去。他觉得胸口胀了起来,有一股劲在往上顶。他张开鼻子眼,烟也从鼻子眼里冒出来。他一连抽了好几口,渐渐摸着了吸烟的窍门也习惯了烟的辛辣味儿。他被烟的香味熏着,晕晕乎乎的很舒服。烟在胸口里翻卷的时候,像水一样柔软,他觉得那块铅熔化了,心里不再那么疼了。从此以后他一觉着心里不痛快的时候,抽两口烟就能舒服点儿。
“咋样?挺得劲儿吧?”“长脖子”问道。“没啥事。”于思学着大人的样子,大大咧咧地弹了一下烟灰。“跟哥们儿走一趟。”
“上哪?”“医院后面的小树林子。”“干啥去?”
“干仗!”
“和谁干!”
“刘瘸子!”
“为啥?”“这小子太牛逼了,得拾掇拾掇他。”“行!跟他干!”于思痛痛快快地说。
“走吧!咱们。”“长脖子”冲众人挥了一下手,就朝通往医院的路走去。一伙儿人跟着他,大摇大摆地走上岔道。他们高兴得又说又笑,好像已经把刘瘸子打垮了。
他们还没有走进那片树林子,就听见里面有人说话。刚走到树林子边上,就看见里面影影绰绰的有不少人。越走越近,那伙儿人的喊声也听得越清楚。一个小子在喊:“这回,咱们一定得好好教训教训’长脖子‘这个王八犊子!”
“长脖子”一听就急了,大叫了起来:“刘瘸子,你爹在这呢,专为会你来了!”树林子的边上正在盖房子,堆满了砖头。一伙儿人走到砖堆跟前,一人抄起一块砖,跟着“长脖子”走进了树林子。林中的空地上站着一群人,也有二三十个,全都带着家伙儿,也都拿着砖头。于思一眼看见了刘瘸子,他挥舞着一根拐,冲着“长脖子”大声吼道:“你小子别找不自在,我是你爹!”
于思以前只是老听人说刘瘸子,可从来没见过他。他的左腿裤腿瘪着,用脚尖支着地。在人们的传说里刘瘸子又狠又毒,没诚想却长得柳红似白的,竟有几分女气。眉毛细细地打着弯,眼睛是标准的杏核眼。鼻梁又窄又直,薄薄的嘴唇轮廓清楚得像是用笔勾出来的。脸色红里透白,好像抹了油一样光滑。他穿着一身干干净净的蓝对襟棉袄,算盘子扣缝得很密,一排足有十几个。裤子是料子的,裤线烫得笔直。
刘瘸子家住在安平街,那一带都是平房区。他从小没爹没妈,跟着哥哥长大。他哥后来当兵去了,就没人管他了。他从小就偷东家摸西家,后来让人逮着打折了腿,坏得更邪乎了,不管是谁家的狗,抓着就宰了吃,不管谁家的鸡,抓着就把腿给拧折了。谁要是得罪了他一点,他就往人家的锅里拉屎撒尿。要不,就半夜里往人家屋里扔炮仗。那一条街上的人都怕他,想着法子往外搬。搬不走的就给他打溜须,逢年过节给他送礼上供。女人们用他吓唬孩子,只要一提他的名字,连孩子都不敢哭了。他渐渐地明白了兔子不吃窝边草的道理,碰上别的地方的流氓来闹事,他就领着一伙儿街流子,把他们打跑了。他的名声越来越响,周围的流氓都怕他。也有离得远的不服气,找着他来叫号,都让他给打服了。他倒比蹲坑的警察还管用,没人敢到安平街去闹事,安平街因为有了他而成了名符其实的安平街。据说,“黑牡丹”也去会过他,他撸起那条瘪着的裤腿,顺手从炉子里抓起一个煤球放在腿上,滋滋啦啦地冒出一股油烟和焦煳味儿。他面不改色,继续说说笑笑。“黑牡丹”当时就服了,伸出大拇指叫大哥。要不是刘瘸子有老婆,“黑牡丹”恨不能就嫁给他了。都说“刘瘸子”的老婆长得特漂亮,是出了名的大美人。他见过“黑牡丹”之后,撇了撇嘴说:“啥呀?!瘦得像根秫秸秆儿似的,好像没长着奶,也没屁股。”“长脖子”说,刘瘸子有票子。他每天夜里招着人在家里耍钱,找几个半大小子当保镖,谁也不敢赖账。他家里不准备开水,他老婆做小买卖渴了就得买他家的汽水,比外面的贵着好些。夏天还行,可以喝自来水,冬天的时候,他把炉子生得旺旺的,热得人口干舌燥。再把自来水一停,然后就卖苹果五块钱一个。赌红了眼的人,渴得不行,只有掏腰包。他连抽带赌,加上卖东西一宿就能赚十来张“大团结”。
两拨人边走边骂,离得越来越近,不知谁喊了一声“打!”两边的人同时飞出了砖头子,因为离得近,砖头子差不多都是横着飞来飞去。“长脖子”和他的几个哥们儿,眼珠子都红了,一只胳膊护着脑袋,一只手拎着家伙,有的嗷嗷叫着有的骂着,顶着对方的砖头子,冲了上去。两伙人打到了一起,这时就全看个人自己的本事了。刘瘸子的人里有一个长着连鬓胡子的,手里拿着一截铁轨,见人就往上抡。他的脑袋上也挨了一砖头,血一直流到胡子上。但他根本不在乎,就像疯了一样,指东打西指南打北。没多大会子的工夫,“长脖子”的人就被他撂倒了好几个。所有的人几乎都受伤了,有的被打破了头,有的屁股上被捅了一刀转眼之间,地上横七竖八地躺着好几个人。于思的肩膀上也挨了一棒子,当时没觉咋的,后来疼了好几个礼拜。他顾不上摸伤处,兴奋地跑来跑去,一边躲闪着一边抡着“长脖子”给他的铁管子。他感到一种从来没有过的痛快,嗷嗷大叫着忘记了小丹,也忘记了小秋和铁蛋儿。
正在这个时候,有人喊了一声:“当兵的来了!”于思抬头一看,满满两卡车解放军,胳膊上都套着“纠察队”的红袖箍儿,开到了树林子边上。两伙儿人像炸了窝一样,撒丫子四处乱窜。躺在地上的跑不了,就用手扒着草稞子爬。当兵的跳下车来,冲进树林子见人就抓。刘瘸子跑得比谁都快,一眨眼,就没影了大江跑得也不慢,没几步就钻出了树林子,跑上了马路,抢了一辆自行车,骑起来就跑,甩掉了追着他的三个解放军。
于思是跟着“长脖子”一起跑的,还没跑到树林子边上,后面就追上来三四个当兵的。于思见“长脖子”扔掉了手里的电工刀,就把自己的铁管也扔了。跑出几百米的时候,于思回了一下头,他看见那几个当兵的已经被他们甩掉了,只有一个小个子兵还紧紧地追着他们。他觉得心跳得厉害,胸口就好像要炸了一样腿怎么也迈不开步子。他对“长脖子”说:“我,快不行了!”“长脖子”说:“不行也得跑!”说着拽起他的胳膊,跌跌撞撞地继续往前跑。小个子兵还在后面跟着差着十几米就要追上来了。于思觉得一丁点儿劲儿都没了,就对“长脖子”说:“我不行了,我他妈实在跑不动了。”“长脖子”的脚步也慢了下来说:“我也岔气了!这时,小个子兵冲了上来,眼看着就要抓住他们了。”长脖子“突然停住了脚步,猛一转身,从裤兜里掏出一个瓶子,举起来对着小个子兵大叫:“这是硫酸瓶子!”小个子兵一怔,停住了脚步,喘着粗气看着“长脖子”。“长脖子”说:“你要是再追,咱们就一块儿玩儿完!”小个子兵愣在那,于思不知从哪来了一股劲,冲着他的胸口就撞了过去。小个子兵没提防,一下摔在了地上,捂住胸口在地上扭来扭去,不知是累的还是疼的,脸色煞白。于思也愣住了,他没想到自己有这么大的力气。他想走过去看看,“长脖子”一把拉住他说:“快跑!”
四
于思推开李家伦家门的时候,他刚睡醒中午觉。他正躺在床上,抽着烟望着天棚发呆。他只穿了一件衬衫,套了一件毛背心,衣服裤子都搭在椅子背上。他看见于思就问道:“你下午有事吗?”于思摇了摇头。李家伦立即说:“那你就跟我走一趟。”
“上哪?”于思本来正觉着没事可干,立刻兴奋起来。“监狱。”李家伦垂着眼皮,在地上找着自己的鞋。他把脚伸进去,坐了起来。于思吃了一惊,马上问道:“上那干啥去?”“看看徐先生。”李家伦拿起椅子上的裤子,套在腿上。于思松了一口气。他从来没有进过监狱,只听人说起过笆篱子怎么怎么样,很想去看看。就痛痛快快地说:“行!”徐盛被抓的事他也听说了,整个大学区的人都知道他的事,他是在八月十五那天被警察抓走的。那天,北方大学召开了全校教职员工大会,开来了一辆警车。工宣队在大会上宣布了徐盛的几大罪状,说他是里通外国分子、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道德败坏、破坏军婚的流氓坏分子。
徐盛犯的事,于思是听爸和妈说的。他从牛棚里被放出来之后,就在家里写字画画。他的古文好,全校除了罗老就数他了,爸说。早先于思也听李家伦说起过,当年徐盛考官费留学的时候,用古文写了一篇文章,然后又翻译成英文,同时又把一篇英文翻译成了古文,把主考官都给镇了。“文化大革命”以前,每逢十一、五一、新年和春节,在教师和演员的联欢会上,他都短不了即席作诗。他还会拉京胡唱戏,有一次,和中文系的一个女教师,上台合演了一出《坐宫》。那时候,“大文明”还在,他坐在台下直撇嘴,摇着头说:“那么大的一个教授,还上台唱戏!我真是瞧他不起。”这件事,留给于思的印象很深。当时,他就坐在“大文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