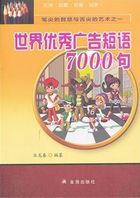清儿道:“公子,你不去陪着新人,却到这里来找清儿?”赵豫道:“公子的心不在那里,公子是随心而来。”清儿怔怔地望着赵豫,泪水不住地流落下来。低下头时,蓦然看到赵豫手上的伤口,心头一紧,道:“公子,你流血了,是谁伤了你?”赵豫看看自己的右手中指,伤口约有半寸长,虽然不深,血已凝结,但竟忘了包扎。清儿用丝巾替赵豫包扎伤口,赵豫一边将事情的经过告诉清儿。末了,赵豫凝视着清儿,道:“清儿,自今夜起,我终于明白了一件事。在我的心里,除了清儿,再也容不下第二个人。不管怎样,我要与清儿长相厮守。”清儿依偎在赵豫的怀里,这一切仿佛是在梦中,清儿不愿说话,怕一说话,梦就醒了,可是自己的心上人却如此真实地就在眼前。
赵豫和清儿都很高兴。赵豫道:“清儿,我们以远处那一座紫霄峰为誓,生生世世,永不分离。”两人翩翩下拜。赵豫又拉着清儿的手,道:“他日待我考取功名,定将名媒正妁,娶清儿为妻。”清儿道:“公子立此誓言,清儿已然知足,哪怕明日就死了,清儿此生亦了无遗憾。”赵豫把清儿拥入怀中,心疼地说道:“我欲与清儿共度此生,若见清儿死了,我也不会独活。”清儿含泪答应。夜深了,两人携手登舟,离了通灵岛。
回到幽云居时,杨绘早已离去,留下一张字条,道:“事急,先行。大恩不言谢,赵官人珍重。”中午赵夫人得知此事,颇有责备之意,但念及事情由杨家小娘子不情愿而起,亦未加追究。杨士焕亦知女儿心性,终究还是拗不过她,也是无可奈何,小住一日,便启程返回平江府不提。
天气一天暖似一天了,天空中飘起了小雨。赵豫已做好了赴京赶考的准备。
转眼间已至二月十五花朝节。山庄里一派喜庆忙碌的景象。祭拜过花神,大家便都提了竹篮,准备要到山中挑菜,即采摘野菜。女眷们正准备着临行物件,却见赵豫大步流星地从外间步入庭院,手持邸报,神采奕奕地对绮心道:“新闻,新闻!官军克复杭州,方腊西遁,东南可指日而平!”绮心扔下锄头,来抢邸报。
绮心思家心切,读着读着已是泪下潸然。众人皆感泣。绮心读罢,思忖片刻,对赵豫、清儿并一众仆人说道:“感戴赵公子、清儿妹妹及贵庄的恩德。家门遭难,绮心归心似箭,即刻便要告辞了。来日安顿家事,更当登门道谢!”众人亦说了些安慰的话语。绮心回房收拾行装,这边赵豫令人打点了十两金子并散碎银子相赠。绮心坚辞不受,只拿了些散碎银两,道:“绮心于府上已叨扰多日,心甚不安,更不应受领府上钱财。这些支应盘缠已绰绰有余,府上大恩来日再报。”赵豫道:“韩妹妹如此客气,倒叫我等不安了。你是敝庄贵客,又是清儿姐妹,更不应如此见外。”于是便使一仆人同行,将盘缠交与仆人以为路上支应。绮心原本推辞,但赵豫却说盘缠只给仆人支度,并非相赠资财,余下的须由仆人带回江宁等等,绮心只得欣然接受。绮心思乡情切,当日便辞了赵豫等人,与赵府仆人奔杭州而去。
送别了绮心,清儿闲了下来,便缝补缝补衣物,替赵豫收拾行装。这一日,赵豫到紫天阁与母亲说话。赵豫道:“近日朝廷颇有废三舍法,恢复科举之意,何去何从,孩儿当赴东京一窥究竟。孩儿走后最担心的就是娘亲,娘一人在家,无人照应。”赵夫人笑道:“家仆众多,豫儿只管放心前去,娘又不是老得动不了了,不必如此顾虑。”赵豫又道,“孩儿此去汴京,不知何时方能返还。”赵夫人微笑道:“不必记挂娘亲,男儿当以天下为怀。”赵豫点头。赵夫人又嘱咐道:“到了汴京,到小甜水巷咱家的老宅子看看。”赵夫人叹了口气,道,“娘的过去,娘一直不愿提起,如今豫儿长大了,有些事情,豫儿有必要知道。一定去看看,便知分晓。”赵豫想要问什么,又怕惹母亲伤心,便只是一一答应。赵夫人想了想,慈爱地笑道:“豫儿第一次出远门,生活起居娘总是放心不下。清儿这孩子勤快,又是在你身边使唤惯了的,你就带了去吧。”赵豫心下大喜,道:“孩儿正想跟娘提及此事,娘却自答应了。”赵夫人没奈何地笑笑说:“都道孩子是娘亲的心头肉,自己的孩儿心里想什么,做娘的难道会不知道么?娘知道你与清儿情投意合,改日娶了正房,把清儿纳作妾室亦是未尝不可。”赵豫不好说什么,只是陪着娘亲唠唠家常,赵夫人并嘱咐一些起居琐事。
翌日,赵豫一行启程北上。临行前,赵夫人传下话来,说昨夜睡眠不佳,一大早的就不送了。赵豫和清儿心里明白,赵夫人是怕伤心落泪才不来的。又想到这座伴随着自己成长,埋藏着诸多回忆的庄院,今日也要做一个暂别了,种种离愁别绪,一一涌上心头。赵豫扶清儿上车,自己则骑一匹灰鬃大马,一行人静悄悄地离了江宁。
赵豫一行过了江,沿官道向北,这一天来到滁州地界。有过路的樵夫说,过了前边密林就到滁州城了。赵豫对清儿道:“清儿,咱们今夜在滁州城里住上一宿,明日一早品一品滁菊茶,尝一尝甘露饼。”清儿笑着点点头,道:“眼下却是要过前边的密林,这道路两旁树高林密,林后颇有山石之险,若是行军打仗,在此设伏,可以占得地利之便。而若是平日里山贼草寇伏于路边,对那往来的行商而言,也是极大的威胁。”赵豫提了生铁棍,豪情满怀道:“清儿放心,便是二三十个草寇拦路,我赵豫也不放在眼里。”便催促家丁赶路。
正往前走的当儿,前面林子里传来人喊马嘶以及刀兵碰撞的声音。赵豫纳闷,难不成真有贼寇劫掠?待赶到时,只见一勇武青年,骑一匹乌鬃马,挑了最后几个山贼,正自仰头大笑。再看那青年时,只见其一身干练,着枣红色便装,高挑身材、脸庞微黑,使一杆三尖两刃刀。这青年并不要众山贼的命,受了伤的山贼在同伴的搀扶下连滚带爬逃命去了。
赵豫对清儿道:“真义士也!”那青年却喝问:“尔等可是江宁来的?”赵豫道:“在下江宁府赵豫,敢问衙内高姓大名。”没成想那青年二话不说,策马上前,挺起手中长刀便刺。赵豫看那刀头尚自滴血,转眼已至跟前,顺势便把头一仰,却是虚招。长刀的刀把子已然横扫着向自己小腹招呼过来。说时迟那时快,赵豫将手中铁棍向上一提,荡开了长刀。还没等缓过神来,刀头再次倏忽而至。赵豫凝神聚气,提棍一隔,“当”的一声巨响,只觉着虎口发麻,再看那三尖两刃刀时,已被荡开了去。那青年也是吃力不小,座下黑马轻嘶了一声。
一旁的清儿看到这突然的一幕,心下吃惊,这会儿却怒道:“此人忒也无理了!”赵豫心下却暗暗佩服,好快的刀法!再说这青年堪堪地看着自己的三板斧没能得手,双手却是热辣辣地发麻,佩服之情油然而生。所谓英雄惜英雄,心下对这位青衣小帽的少年公子已是暗生敬意。
赵豫喝问:“衙内力战山贼,本是英雄之举,却为何皂白不分,挡我去路?”那青年冷笑一声,道:“伤几个毛贼不足挂齿,公子才是真英雄,在下正要领教!”这样一说,倒是激起赵豫胸中豪气,“好”字还未说出口,青年已然拍马近前。赵豫心中暗忖:“好急的性子。”提起手中的铁棍去迎那青年。
这一架打将起来,直打得天昏地暗,草木低垂,尘沙飞舞。那一边长刀漫卷似细蛟腾浪千帆尽折;这一处大棍横飞如猛虎下山万众披靡。
众家丁看得魂飞魄散,清儿却瞧出了门道,渐渐地,敌我对阵早已变成了比武切磋,双方出招均是惺惺相惜,招数精纯却早已隐去了杀机。一顿饭的工夫,双方均已无心再战。那青年挂了长刀,拨马跳出圈外,拱手道:“赵公子果然英雄了得,天色已暗,腹中饥渴,在下早在城外备下酒菜,恭迎赵公子一行。”赵豫惊问:“阁下早知赵豫要途经此地?”青年道:“在下等候公子多时。”嘿嘿一笑,连忙又道:“对了,请恕在下无礼,未曾通报姓名。某姓姚,姚平仲便是我了。”“敢问阁下可是秦凤路都钤辖,人称‘小太尉’的姚平仲将军?”姚平仲答:“正是。”赵豫连忙滚鞍下马。姚平仲亦下马。赵豫拉着姚平仲的手道:“久闻将军大名,今日得见,足慰平生。”平仲笑道:“愧不敢当。”赵豫又道:“将军积年与夏人战,威震贼胆,国人莫不钦佩。”这时清儿亦过来见礼道:“小女子见过姚将军。”赵豫道:“这是赵某未过门的妻子。”话一出口,赵豫便觉造次了,这样的话还是头一回从自己口中说出,不觉耳根燥热,浑身不自在。清儿一听这话,也是脸颊飞红,躲一边去了。姚平仲哈哈大笑,道:“果然是郎才女貌,天作之合啊!”说罢翻身上马,为赵豫一行引路,往滁州城而去。
行不远时已见酒旗招展,赵豫道:“当年艺祖为周世宗平南唐,大军到得清流关时逡巡不前。这清流关北控江淮,南望长江,易守难攻。艺祖依韩王赵普计策浮水而下,一战而平清流关。青山依旧,英雄却已化归尘土。”姚平仲道:“我不懂得这些,听公子说来,此地倒是一处人文的所在。青山绿水,英雄辈出,甚好!今日某与公子一见如故,痛快得很,不如你我就在这清流关下结为兄弟如何?”赵豫大喜,道:“赵豫高攀,愿与姚将军结为异姓兄弟,生死相随,共扶社稷。”当下两人欣然下拜。姚平仲长赵豫五年,便为兄长。平仲道:“前面的酒家,为兄已经包下,这会儿恐怕你嫂子已经使人做好了热腾腾的饭菜,正等着咱们呢。”平仲心驰神往,径自在前引路,来到酒旗飘处。
晚风习习,灯火掩映下,帘卷朱楼,一位红粉佳人款款而出,不是别个,正是曾与赵豫拜堂成亲的杨绘。赵豫吃惊不小。平仲笑道:“贤弟毋须惊异,且听你嫂子说道。”于是杨绘、清儿、平仲、赵豫共围一桌坐下,杨绘吩咐酒家把酒上菜,自己则娓娓道来:“家父乃是京兆府长安人氏,早年曾判两浙路越州余姚事,家母即越州人。家父后迁知秦州。小女子即是在秦州与平仲相识,两小无猜。怎奈家父不喜武人。后自家父除受平江府后,我与平仲虽万里阻隔,仍私相往来,两情相悦,早已约定终身。”赵豫点头道:“愚弟若是知道哥哥嫂嫂此番情义,定不会枉结姻亲,却损了兄嫂的名节。”平仲哈哈大笑,道:“习武之人不以为意,贤弟休要放在心上。”杨绘又道:“实不相瞒,家母乃明教中人,小女子自小亦深受濡染。此次朝廷演武江南,我与平仲意相龃龉,平仲知我心意,便不愿领军南下。奈何其名声在外,西军此来,怎能无此大将,便只能故作缓行,殿为后军,押送粮草辎重而来。”“军中之事,身不由已,不提也罢。”平仲道,“因你嫂子的缘故,两浙之战,为兄能不战则不战,如此粉黛江南,一路游山玩水,不亦快哉?听你嫂子说起贤弟令名,便想会上一会,今日相见,果然名不虚传。”“兄嫂抬举,愧不敢当。”赵豫笑道,“对了,说起来清儿与嫂子竟是同乡,同为长安人氏。”“果真如此?”杨绘看着清儿,兴奋地问道。清儿微笑着点点头。平仲举杯道:“我亦为关陇之人,我三人可举杯一饮。”清儿向酒杯抿了一口,道:“奴婢忝与将军及小娘子同列。”平仲哈哈大笑,道:“哪里话,弟妹过谦了,今后在兄嫂面前再不得如此谦逊。今日当罚饮一杯!”见清儿略有难色,杨绘嗔道:“人家小姑娘家岂似你这等五大三粗之人能饮酒的?”四人皆笑。赵豫对平仲道:“清儿不胜酒力,便由愚弟代饮此杯。”说罢一饮而尽。平仲大声叫好。赵豫又对杨绘道:“乍一看时,嫂嫂与清儿倒有几分神似,怪道是同乡之人。此皆缘份,今日便由愚弟代清儿敬酒,嫂嫂当饮一杯。”杨绘二话不说,笑着将酒倒满,一饮而尽。赵豫叹道:“真乃女中豪杰!”平仲又问清儿:“不知弟妹何以居住江南呢?”清儿答道:“家父家母早亡,无缘得谋其面。清儿早年随婆婆流落东京,后随赵夫人南下江宁。”平仲闻言喟叹,道:“为兄亦无父无母,自小跟随从父,由其抚养成人。”沉默片刻,又道:“弟妹随意,为兄干了这杯。”说罢举杯一饮而尽。四人气味相投,坦诚直面,无话不谈,酒足饭饱之后便一同进城。平仲道:“为兄的已为贤弟订下城中最好的客栈醉香楼。贤弟可与家人同往。本欲与贤弟促膝长谈,奈何军务在身,为兄须与你嫂嫂回馆驿处置,就此别过,后会有期!”于是四人两厢依依道别。
赵豫等人向路人打听醉香楼的所在,果然是名声在外的大客栈,到得醉香楼,一应豪华便利,一行人很快便安顿下来。时辰尚早、月色颇好,赵豫便携着清儿在城里清静之处品茶赏月,谈着儿时的往事,近期的变故,互诉衷肠,感情上是越发地无间。清儿道:“公子须知月有圆缺,人有离合,便是古时司马相如与卓文君那样的恩爱夫妻,老来时候亦免不了受那《白头吟》的凄苦。只愿这赴京城的路途再远些,当垆卖酒的日子再长些,清儿的美梦再能做得久些。”赵豫握紧清儿的手,道:“我只知执子之手,与子携老,便有再多的不尽人意之处,清儿只需等待两三年,待收复幽云之志达成,我便辞官不做,你我回到江宁,侍奉母亲,归隐林泉,不问俗事。到那时候,又哪儿来的卓王孙,哪儿来的《白头吟》呢?”清儿微笑着,若有所思地点点头。赵豫继续说道:“清儿,咱俩原是两小无猜,我便是清儿哥哥似的人,清儿本该叫我一声哥哥。便是将来过了门,如此叫来亦是无妨,总比那‘公子’二字来得亲切。此后清儿便唤哥哥无妨。”清儿高兴,点头道:“哥哥,清儿便是明天就死了,心里也是高兴的。”赵豫笑道:“没来由地说个‘死’字,若是我姚兄听闻,又要罚酒三杯了。”两人聊到很晚方回客房休息。
由于清儿自小便是赵豫的使唤丫环,故而不避男女之嫌,同居一室。赵豫夜半听到清儿梦噫,大喊“莫要伤我公子!”赵豫心下感动,许久不见声响,也便睡去了。清早来摸清儿的额头,方觉烫手。这可把赵豫心疼得不行。清儿已醒,强打精神向赵豫微笑。赵豫轻声斥责道:“什么时候觉得不舒服的,也不告诉哥哥。”清儿道:“昨晚已经稍感不适,原本以为一觉醒来便没事了,是不想让哥哥担心才……”赵豫扶清儿躺下,将被子盖盖严实,并吩咐下人赵福去请郎中。
望着爱人病得憔悴的脸庞,赵豫想到了清儿昨夜那个“死”字,心下“咯噔”一声,一时怔住了。清儿微笑道:“只是略感眩晕心悸,哥哥莫要担心。”不多时,大夫即至,为清儿把了脉象,开了方子,道:“嫂夫人必是受了惊吓,外加感遇风寒,其实并无大碍。若能得一味长白山参以行滋补,便能即速痊愈了,官人不必担心。”这老郎中眉飞色舞地说道,“《神农本草经》云,人参主补五脏,安精神,定魂魄,止惊悸,除邪气。”郎中拈须想了想,却道,“然,长白山之神草又岂是寻常铺子能买得到的?”赵豫问:“城中哪家药铺有售?”郎中提笔写了“钟楼巷仁济堂”递与赵豫,又开了一般方子。赵豫谢过大夫不提。
赵豫心道:“如此名贵的药材我便多问几家,总是无妨。”于是沿路问去,竟没有一家药铺有售。这一家掌柜道:“长白参啊?但凡黄精神草之物,怕滁州城中亦所剩无多咯。”“此话怎讲?”“客官有所不知,今日一早便有大主顾上门抓药,单要人参。”掌柜的答道。“他要这许多人参做甚?”“那人凶恶,我等岂敢多问呀?总之主顾愿意付钱,我等做生意的是乐得把货卖给他啊。至于用做什么,如果遇着像客官您这样和善的人啊,倒是可以问一问。那人要是不肯说时,小人们也就少管闲事便了。”赵豫点头不语。离了这家铺子,赵豫三步并作两步,来到郎中所指的仁济堂。端的是一家大药铺,烫金的招牌,宽敞的店面,各式草药琳琅满目。赵豫问道:“小二,你这里可有长白山人参?”小二正算帐,头也不抬,只答理道:“卖完了,但凡是人参都卖掉了。”赵豫也不知哪里来的无名之火,左手一把纠着小二的衣襟,这店小二就像只小鸡似地被拎了起来。赵豫喝道:“你这是店大欺客不是?若有人参便拿将出来,若是胆敢囤积居奇,小爷今日就敢拆了你家铺子。”右手摸了一块大银,往柜上一拍,道:“便是再高的价钱爷爷还是出得起的!”这一来可惊动了掌柜的。只见一个胖敦敦的中年人赶忙趋步过来圆场道:“客官息怒、客官息怒啊。”待看那锭银子时,却是已经深深嵌入了木头里。这掌柜的不觉倒吸一口凉气,忙道:“客官息怒,不是小店不肯卖与客官人参啊,小店的人参确实一大早都被人给买走了呀!”赵豫喝问:“那买参的长什么模样?”掌柜道:“大脸庞、络腮胡子、头发如钢针,手臂如铁杵,看着不像中土人氏,恶得很啊!”赵豫把店小二放下,向掌柜的作个揖道:“适才多有得罪。”扭头便要出门。掌柜的忙道:“客官你的银子!”赵豫一怔,果然银子是忘了拿了,笑道:“你这掌柜的倒是老实!”掌柜的赶忙陪笑道:“诚信乃是本店立店之本嘛!冒昧问一句,客官所买人参为何?”赵豫道:“实不相瞒,内子急症,气血虚弱,需要长白山参补养调剂。”掌柜道:“好一个有情有义的汉子,这样吧,人参嘛我倒是私存了一支,乃是备作不时之需,救急之用的。客官若是为了救治夫人,只管拿去便是。”赵豫赶忙又拿出一大锭银子,道:“掌柜的如此仗义,在下感激不尽。”掌柜的忙道:“客官已有银子在此,不用这许多。”赵豫笑笑道:“只管拿去便是”。掌柜的到里间取出人参,道:“客官也许不知,此乃高丽国出产的人参,温而不燥,实属上品啊!”赵豫道:“此参比那长白山参如何?”掌柜的呵呵笑道:“客官啊,这么说吧,以长白山为界,这人参呢,生长在长白山以西的便叫长白山人参,这生长在高丽国一边的呢就叫做‘高丽人参’,其实啊,都是一样的物事。”赵豫闻此大喜,别了掌柜的便往回赶。赵豫心道:“好歹叫我买到一支人参,清儿终是有福之人,很快就能好起来了。不过那神秘的买参人究竟却是何方神圣?买断人参又是有何用意呢?”看到前边有一家小药店,赵豫决定再去探一个究竟。不料未进店门却先听到口角之声。赵豫入内一瞧,原来是一个伶牙俐齿的丫环,再一听,原来也是为了买人参的事来。那丫环道:“掌柜大老板,你就卖一支人参给我吧,没有好的,次的也行,再不济时,什么须须末末,凡是人参上掉下来的东西都中用啊。”那掌柜道:“小娘子,都说多少遍了,今日一早,人参都被人买走了,哪里还有什么存货啊,你便要些须须末末的也不济事啊。”赵豫对那掌柜的道:“掌柜的,你若是有那人参,便卖与她几支何妨。”那掌柜的不耐烦道:“客官啊,我都说多少回了,别说几支,就是一支也没有。没有人参,难不成我还能生得出来呀,没有,就是没有!”赵豫也不去跟他急,却问那丫环道:“小娘子索买人参却是为何?”那丫环道:“为我家公子续命之用。甚急!”“如此说来,你家公子是危在旦夕咯?”那丫环彬彬有礼地答道:“这位官人,实不相瞒,我家公子无故遭人暗算,此刻命如风烛。而此处离家甚远,无法可想,只能买参续命而已。殊不知那天煞的恶徒,却要将我家公子往死路上赶,买断了城里所有的人参;更有这些奸恶商人唯利是图、助纣为虐,非旦不救人于水火,倒要恶言相向、落井下石。这世态之炎凉,如此亦可见一斑了。”赵豫暗忖:“照这姑娘的言谈举止,当不是一般人家的丫头。不管怎样,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而这位神秘公子似乎与今日的人参买断事件有着直接的联系,不如也借此机会去看个究竟。没了人参,是苦了清儿,回去时,我当尽心竭力照顾清儿便是。”想到这里,赵豫笑道:“他便没有人参,又如何卖与你呢?小娘子莫急,在下先前觅得人参一支,救人要紧,便请小娘子在前引路吧。”那丫环看到赵豫手里的人参,果然大喜,便领着赵豫往见他家公子去。
穿街过巷,来到一处僻静的所在。原来滁州城里却有如此幽静的馆舍,倒胜似住那街边的酒肆客栈许多。那丫环推门请赵豫入内。屋内一个大汉道:“小娘子回来了。”说罢瞅了瞅赵豫。那丫环笑笑说:“这是我请来的大夫。公子安好?”那大汉恭敬地答道:“仍是时而苦寒,时而燥热,身子甚为虚弱。”这时只听到里间传来一丝微弱的声音,道:“小妹回来了么?”赵豫心道:“这丫环来头果然不小。那大汉对她如此恭敬,而与此间主人又以兄妹相称。”小妹对那公子道:“大哥,我为你带回了高丽人参,你吃了就没事了啊!等你好一些,咱回到了东京,爹爹会找最好的大夫医治你。”那公子哼了两声,便不再说什么。赵豫皱了皱眉头道:“你大哥似是中了寒毒,此毒非同一般,我听我娘说起过,似乎是一种叫黑水冰蚕的毒物所致。此蚕似蚕而非蚕,生长于关外苦寒之地。以其所吐之丝与北地硫磺混合捣碎,并以烈酒浸泡,如此深埋于寒冰之下七七四十九日,此毒乃成。”小妹大喜道:“公子既谙此毒,亦必有破解之法咯?”赵豫道:“在下不谙用毒解毒之术,只是曾听母亲说起过,今日目睹症状,偶然想起罢了。”小妹叹口气,道:“是啊,天下间哪有这般十全十美的事,今日嬛嬛得遇公子,公子高义,赐予延命之参,若再奢望公子还会解毒之术,怕是老天也不会答应了。”嬛嬛对那壮汉道:“张兄弟,你把这高丽参拿下去,煎了水给公子服用。”那大汉恭敬地应了一声,接了人参便下去了。嬛嬛从床头包袱里拿出一大锭金子,对赵豫道:“公子,大恩不言谢,些许资财聊表心意,务请公子收下。”赵豫起身道:“赵某今日只为救人以急,又岂是贪图回报?再说一支人参本就不值什么。”嬛妹道:“公子也是姓赵?”赵豫道:“敝姓赵,单名一个豫字,此行乃是从江宁赴汴京赶考去的。小娘子适才一个‘也’字,难道小娘子也姓赵吗?”“哦,不是不是,我姓王,我娘亲姓赵,我叫王嬛嬛,我大哥也姓王,叫王桓。”嬛嬛解释道。赵豫听罢笑着说:“他是你大哥,你既姓王,他自然也姓王;小娘子适才又说,他叫王环,而小娘子自己叫王环环,难道你们还有弟弟妹妹叫王三环不成?”赵豫说罢哈哈大笑,王环环亦开怀大笑,道:“也许吧,如果家里添了弟弟妹妹,那叫王三环也未尝不可啊。”笑罢,嬛嬛道:“对了,赵公子的人参亦是为了治病救人的吧,眼下我们用了却如何是好?”赵豫道:“不妨事,内子只是偶感风寒,身子虚弱,用其他的方子补养补养,想必亦无大碍。”“哦,原来赵公子此去东京是与嫂夫人同行。”嬛嬛道。赵豫笑问:“这位公子当真是你大哥啊?”嬛嬛笑道:“难不成公子还不信了,他真是我大哥,亲亲的大哥,我大哥叫王桓,我叫王嬛嬛。”“行了行了,我信我信,”赵豫道,“对了王姑娘。”“叫我嬛嬛好了。”“嬛嬛姑娘。”“你这人也迂腐了去,是嬛嬛。”赵豫无奈笑道:“嬛嬛,你大哥为何受伤,受何人所伤,对方为何出此阴招,必要置其于死地呢?”“可能是看我家有钱吧。”嬛嬛道。“难不成你家竟能富比石崇么?”赵豫笑问。“石崇嘛,倒未必有我家富有呢。嬛嬛是我的小名,我叫多富,富可敌国的富。拿我家的金山去填石崇家的池塘恐怕也是能够填得满的吧。”嬛嬛没精打彩地说。赵豫笑笑,没再说什么。
嬛嬛道:“赵公子,我们明日便要启程回东京了,只有尽快回到东京,我大哥才能有救。不知赵公子可愿一同北上呢?”赵豫道:“嬛嬛热情相邀,赵豫本来不该推辞,无奈内子身体不适,不宜走动,赵豫便想在这滁州城里多住几日,再赴东京不迟。”嬛嬛道:“也好。冒昧问一句,不知赵公子一行住宿哪家客栈?”“城西的醉香楼。”嬛嬛又问:“离此不远,一会儿公子走时嬛嬛可以相送一程。”赵豫摆摆手道:“不用了,如此客气时,倒叫赵豫浑身地不自在呢。”辞让几句,赵豫便即起身辞行。
单说赵豫一人离开馆舍,忽抬眼间,看到有灰色人影晃动,定睛看时,那灰衣人已从前方街道拐角处隐去,赵豫毫不迟疑,提气便追。灰衣人在前,左躲右闪,轻似腾兔,快如飞鼠。赵豫暗暗赞叹:“好功夫!”如此一人在前,一人紧追,在滁州城的大街小巷间,双方你追我藏,玩起了猫捉老鼠的游戏。追了有一盏茶的功夫,那人倒有些体力不支了,眼看赵豫就要追上。可就在这时,赵豫猛然发觉有数点银光朝自己面门飞来,暗叫一声“不好”,往旁里一让,让过了数枚银针。可就这么一闪避的功夫,灰衣人已然消失得无影无踪。
赵豫心下颇有些自责:“赵豫啊赵豫,追一个体身欠安的人都能追丢了。若是对方状态正佳时,你又岂得全身而退?”赵豫抱着一股子失落的心情,继续在小街小巷中搜寻,以期有新的发现。忽然,一声男子的惨叫将其吸引了过去。不细听还真听不到,这声响似是从隔墙院落里发出的。看到有落脚之物,赵豫小心地翻越围墙,进了两进院落,爬到了屋檐边上,越过女墙的一角,看到了院中的景象。这一看,赵豫惊喜,院子里站着的灰衣人正是自己适才穷追不舍之人,如今却得来全不费功夫。灰衣人的面巾仍旧没有取下,显然是不愿以真面目示人,听说话声音竟是个女子。而一旁站着的大汉,大头、络腮胡、虎背熊腰,定是药店掌柜描述的买药人无疑了。一旁有位老者伏在地上一动不动,显然是死了,而一个官服穿戴的人物僵直地站立一旁,将头扭向一边,显然是不愿意正眼看视敌人。只听那灰衣人说道:“知州大人,你的军器监死很壮烈啊,你也想步其后尘么。如何,是要命呢,还是要《神火密令》,你自己选择吧。”那知州哼了一声,道:“金狗妄想,我宋人皆抱为国赴死之决心,你便取得《神火密令》,也难越我宋人众志成城!更何况要取得《神火密令》,还得越过我这一关呐,嘿嘿。”那灰衣人听罢倒不生气,笑道:“要过知州大人这一关还不容易?只怕大人要死得壮烈,我却要让大人死得龌龊罢了。”赵豫心道:“灰衣人称对方为知州,那这位官爷定是滁州知州陆舆民无疑了。倒是听人说起过,这陆大人是个耿直的倔老头。金人恐怕从他的嘴里是得不到什么好处去。”果然,陆舆民冷笑道:“大丈夫只求无愧于天地,就算你的卑鄙伎俩瞒得过世人的眼睛,却瞒不过我大宋历代先皇在天之灵。不就是一死么?来吧,我陆舆民要是哼一声,便不算是好汉!”“好!”那灰衣人道:“我明天便去将赵桓杀了,还要叫人看到是你杀的;然后叫人将赵多富污了,便说是……”“住口!”陆舆民大骂道:“金狗!想要觊觎我大宋江山,一刀一枪杀过来便是,做这等龌龊的勾当,算得什么好汉。”那灰衣人却笑道:“陆大人此言差矣,首先,我并不是什么好汉,本姑娘就算是阴险狠辣,那也是妇人心使然;其次,以上所说这些,世人都将知道是你陆大人干的。滁州知州陆舆民北结契丹,图谋不轨,事情败露便以灭口之心加害当朝太子并柔福帝姬……”“苍天可鉴啊!”陆舆民撕心裂肺地吼道,“历代先皇、陆家列祖列宗在上,我陆舆民一生刚正清廉,鞠躬尽瘁以为社稷,陆舆民上无愧于苍天,下无愧于黎庶啊,哈哈哈!”笑罢,竟一头撞向台阶。赵豫原本钦佩陆舆民气节,心下便欲救人,只是想从金人的谈吐中听得一些情报,便一直候着。可没成想陆舆民竟如此刚烈,此时救人已是来不及了。赵豫气血上涌,纵身一跃落到陆舆民跟前,将其抱起,轻唤了一声:“陆大人。”那陆舆民已是奄奄一息。“在下宋人赵豫,陆大人高风亮节,青史可鉴。”陆舆民微微笑道:“有劳赵公子为老夫正名!”说罢示意赵豫凑耳近前。陆舆民轻声道:“赵公子愿为社稷效死力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