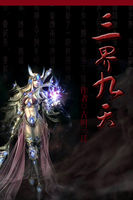1.马桑
死者马桑的身份很快得到确认。尸体已经严重烧焦,提取不到有效的DNA材质,马桑的衣物也已经烧成灰烬。警方避开DNA检验程序,以美容厅提供的电话记录和安志勇的供词构成证据链,证明马桑的身份。如果安志勇不肯配合,闭上那张臭嘴死不吭声,死者身份的确认将是一个巨大的难题。
在公安局里我见到了马桑的父亲马应当。马家也确实悲惨,一听就是一出特大苦戏。马桑的母亲和一个姐姐都已死亡,马桑再一死,全家就只剩下一个孤苦伶仃的老人。老人一直在乡下守着几块薄地种菜,种好的菜批给菜贩,菜贩撅下来的烂叶老菜帮子自己吃。这几天他来到佴城,白天住在一家小旅馆(住宿费由警方支付),晚上去夜市乞讨。我在夜市上找到他,请他随便吃些什么,并询问马桑的一些情况。他并没因为我是被告律师而拒绝我,尽他所能予以配合,我问什么他就认真作答,态度诚恳,瞅准时机向我哭穷。他叫我领导。不管是谁,他都喜欢以“领导”相称,即使不准确,总比“同志”受用。
“领导,我家马桑妹子是苦水里泡大的,活到二十七八,一天福都还没享,就这么一下子被姓安的王八蛋搞死了,呜呜,搞死了呀……”他一把鼻涕一把泪。
我问他怎么想到要报案。我看得出来,马桑在外谋生,和他的联系并不多,大不了隔一段时间寄一笔钱回去,他们之间应该不会常有电话联系,书信往来更是上世纪的传说。马桑失踪才半个月,怎么就引起了马应当的注意?
对于这个问题,马应当也是很谨慎,想了想才说他们父女时不时会通一通电话。我问是他给她打,还是她打给他。他又想了好一阵才说:“她打给我。”
“你家没座机也没手机,她打到哪里?”
“……打到隔壁三黑家的杂货店,那里面有一台电话机嘛。”
“呃,过几天我去查查这个三黑家的电话记录。”
“我记错了,”他很快就纠正自己,“是有人打电话告诉我马桑失踪几天了。我问他怎么办,他说报警啊。我说不能乱报警,他说不报的话,过了时限就报不响了。”
我知道是美容厅的人指导他这么做,问他哪天报的警,他记不清楚。一般来说,因家人失踪而报警的人,对日期都记得非常牢靠,但他记不清楚。美容厅的老板怕承担罪责,但手下妹子失踪,不报也是不行,他们打电话要马应当报案,想想也是在情理之中。但我也得来些经验,案件中合情合理的地方,往往掩藏着大问题。
我也不多问,次日找陈二帮着查一查。这事不费吹灰之力,陈二很快反馈消息,马应当是十月十二日打电话报的案。这和抓篓湖附近农民捞出尸块、报警是同一天。当时我想,这是一种巧合——也许,这仅仅是一种巧合。我不想捉着马应当继续问下去,面对他,询问就是讯问。被问时,他一直战战兢兢,比罪犯更像罪犯。
忙了一天,不想去家里热饭,在街边叫一盘炒粉,忽然想到夜宝,给他打个电话,说我请你吃五块钱一盘的炒粉,你来不来?这近乎威胁,要是我说搞了一大锅沙鳖请他吃,他可以得体地拒绝,但他拒绝一盘炒粉,就是狗眼看人低。他很快地赶到我这里,开着东风日产,那车现在又加满了油。
他走过来,贴着我坐。“怎么了哥?什么事?”
“马桑死掉的事,你不会不知道吧?”
“人又不是我杀的。”
“这个我相信,呃,不是你。”我拍拍他脑袋,在他面前我得摆出老大哥的威仪。不是我装逼,而是有些傻逼只吃这一套。又说:“安志勇既然叫外卖,那么,他的电话肯定是打到你们总台上的吧?”
他点点头。“总台”是符启明将城南性产业重新组合以后,设置的一个外卖总号,2147547,谐音是“尔要试妻吾是妻”——城南的嫖客们应该对此记忆颇深。“那天我也在总台守线,接到安志勇打来的电话,按照顺序,应该转给金圆美容厅做,但是老詹打给了心雨。”
“心雨”就是马桑所在的那家店子。我问夜宝,老詹为什么要这样做?他说鬼知道哩。我问这样乱了秩序的情况多不多,他说几乎没有,除非是顾客点名要找哪个妹子。但这情况很少,要是点名的话,电话往往是打给妹子本人。
那天,安志勇选择了“随机”。安志勇总是选择随机,他的记忆中并没有保留任何妹子,也许,随机对他来说就意味着邂逅。说到这里,夜宝忽又想起什么,告诉我:“有几个妹子都主动打过招呼,说要是安志勇打电话叫人,她们愿意上门。但几个妹子都这么说,叫谁都不合适,公平起见,还是随机。”
我想,要是符启明年终开的表彰会有“优秀嫖客”这一奖项,安志勇会是有力的竞争者,那些妹子都会投他的票。我赶紧提醒自己,集中注意力,干正经事。又问:“老詹怎么知道电话是安志勇打来的?”
“安志勇打来电话,我一边记一边问他,暮山村121号是吧?老詹听出是安志勇,走了过来。”夜宝吸溜着狭长的绿豆粉皮,问我,“哥,你又去派出所干活了?”
“现在我帮安志勇辩护。”
“他杀了马桑,老詹也要扯进去?他不叫马桑去,死的就会是另一个妹子。”
我本想说,也许就不会死。但我说:“鬼知道哩。”
王宝琴天天上班,她们的工资跟效益挂钩。她朋友不多,主要是综合医院的同事。刚来时,她和以前在春光灿烂夜总会的妹子时不时聚一起说说话,后来慢慢淡了。有天晚上吃饭,王宝琴告诉我她又和从前的姐妹见了一面。小芙突然打来电话,约她到江畔花园吃烧烤。她问我记不记得小芙。
“怎会不记得呢?小芙怎么突然想到叫你?过生日?”
“打电话时她也那么说,但我知道今天不是。她是十二月份生的。她骗我我也去,好久没有见到她们了。去了以后,有两个我认得,一个叫苦瓜,一个叫金玫,还有一个不认得。她其实也不是想见我,酒一喝就说起那个女孩,马桑,你应该听说过。”
我点点头,不动声色地问怎么了。
“马桑我不认识,但她们一说,这妹子造孽啊。她本来就有病,家里穷,传不下什么财宝,只传了她一身怪病。她家的女人,二十几岁就会犯病,浑身没有力气,肌肉开始萎缩,感个小冒就会住一两个月的院,三十来岁就会死。”
“一家都是这样?”
“不是说了嘛,她家女的才有这病,传女不传男,活见鬼了!她妈死得早,她有个姐姐二十一岁开始得病,前几年死了。马桑二十五岁还没开始犯病,以为自己可能命好一点,摆脱那种病。今年年初,她老是抽筋,一只手拿东西,一不小心就往外掉,还流斜口水,一查并不是面瘫……”
“重症肌无力?卢伽雷氏症?闭锁综合征?”我脑袋里浮现出一系列患有这些怪病的伟大人物,他们与命运的抗争是永恒的励志传奇。我见过马桑的照片,那是一个鲜活的女孩,我没法将她和那些绝症联系在一起。
“具体的,小芙也说不清楚。小芙和马桑关系最好。小芙贪小便宜,不招人喜欢,但她对马桑很好。小芙身体不好,马桑有绝症,小芙一直都照顾她。现在马桑死掉啦,小芙很伤心。我从没见过她这么伤心,就像死了妹妹……”
“呃,确实是死了妹妹。”我打断她,问,“那么说,马桑姐姐不是车撞死的?”
“怎么了?你听别人说过?病死的撞死的都一样惨嘛。”王宝琴不能肯定。
我分明记得,马应当跟我不是这么说的。那天,他说到家事老泪纵横,那个惨啊,让我觉得他一字一句都是控诉命运不公,造物弄人,没想到这里面还有假话。他说他大女儿马敏是车撞死的,大货车。马应当为什么要骗我?为什么要隐瞒大女儿的死亡原因?我相信,这不会是他本人故意为之,是有人教他这么说。想到这里我吓了一跳。
回过神,我又问她:“小芙还说了马桑的什么事?”
“她发现自己也有遗传的那种病,很绝望,以前自杀过一次,但是没死。”
“能不能联系一下小芙?我有话问她。”我向她摊牌,正在当安志勇的辩护律师,有些情况要向小芙打听。王宝琴听我这么一说,脸色一变,说:“你怎么能帮杀人犯辩护?要是这个狗东西不死,小芙知道是你帮他说话……那怎么行嘛。”
“辩护不是帮坏人说话。你作为一个律师的老婆,怎么好意思讲出这种浑话!”我唬住她,要她帮我约小芙出来问些情况。王宝琴被我一脸认真的模样吓了一跳,想了想,还是拨了小芙的电话。
系统声音不紧不慢地说,你所拨打的用户不在服务区。
2.破茧而出
安志勇纵已招供,警方对待死者身份不敢掉以轻心,要做成铁案。功夫不负有心人,老梁从烧焦的尸体中找到一筒骨髓。安志勇当天用的火候没到,这筒骨髓没有完全炭化,可以抽取DNA样本,拿去和马应当比对成功,死者确实是马桑,铁板钉了钉。
同样的一段时间里,我始终没找到小芙,她手机总也打不通。我叫王宝琴找个时间去小芙住的地方,以及心雨美容厅,仍然找不到人。别的妹子告诉她,小芙已经离开佴城,到省城找事做去了。我当然不甘心,要老婆找找当天吃饭时同来的那三个妹子。马桑的事,她们多少也知道一些。其中一个叫苦瓜的,如果我没记错,曾在符启明的星光派里见过,当时她在干端盘倒水的活。听说苦瓜已经去美容厅干活,虽属意料之中,我仍不免感慨。但我相信当初见到时她那副淳朴的表情,找到她,应该问得出一些情况。
那天王宝琴回到家里,我还来不及问她,她就连说怪事。
“怎么了?”
“苦瓜妹子也不在那里干了,说是回老家嫁人。前几天还一起吃饭,都没听说她有男朋友,怎么突然就嫁掉了?而金玫,忽然变了个人,和她说到马桑,她说她也不晓得太多情况——不比我多。还有那个妹子,林俊芬,她干脆就说跟马桑还没碰上几面,说不上十句话。”
我听得出来,王宝琴刚才去美容厅找人,就像钻进了一场破电视剧,所有的人全被编剧瞎编排,要她们失忆就集体失忆,理由都不给一个。我却并不奇怪。王宝琴一头雾水,此时我心里却模糊地想到一个人。
符启明打来电话,告诉我他即将回来了。我哦了一声。他告诉我最近颇有斩获,一帧有关超新星爆发的图片获得国内天文摄影深空类金奖;而他在喜马拉雅拍摄而成的一组星迹图,命名为《心在高原——光与影的神迹》,入选南美洲星空摄影双年展,并有望竞逐“天与地”组别金奖。他告诉我,那是天文摄影的顶级赛事,相当于电影界的奥斯卡或者文学界的诺贝尔。我又哦了一声,对于这种拿人家屁股当脸的说法,我不愿意太当回事。
“你怎么了?”
“没什么,只是为你感到高兴。你只要想干好的事,就像被西门庆盯上的妹子,没有能侥幸跑脱的。”
“数月不见,你讲话也是功力大增,我竟然听不出是夸是骂。呃,我马上要在星空漫步网做一个专访,不多聊,有空看看这个网,网址百度一下。回来时喝酒。”
他先是去了广东领取国内奖项,回佴城停留了几天,主要是办出国手续,之后去了美国,再转道南美几个国家,参加星空摄影双年展的巡回展出,到处接受采访,不是帅哥,也谋杀了记者手中不少菲林。中央十三频道上播出他得奖的消息,不过并未大肆报道,只是以新闻快讯的方式,寥寥几句话摆平了他的辉煌业迹。他身着礼服,手握奖杯,在颁奖仪式上发表感言。新闻没有播出符启明说的获奖感言,但我想他肯定操一口纯正的佴城方言,因为纯正所以牛逼,却让翻译伤透了脑筋。翻译是个巨胖的女人,脸都憋红了。
王宝琴看了颇有感慨,说:“喏,你一辈子也碰不到一次这么露脸的机会了。”
“一般人都碰不到。你以为符启明这么好用的脑袋,是随便一对夫妻随便生得出来的?”
9.26命案的侦破工作已经宣告结束,案卷移交司法机关,开庭时间应该不远了,我围绕着案子加紧做准备。这期间,我脑袋里慢慢形成一个思路,不是辩护思路,完全是破案。若我这思路能被证明,安志勇和马桑的身份有可能完全倒转。
但是,我只是这么一想,都觉得有些离谱。
符启明载誉归来,一到佴城,市电视台那档文艺专栏的编导守着他,专门为他搞了一期节目。他群发了短信,告诉我们播出日期。王宝琴现在算得上符启明的粉丝,接到短信,和别人换了班,那晚上守着市台看符启明的出现。
他已经有了受访经验,和主持人侃侃而谈,应答自如,一脸表情也像影视明星般流畅。他先是说起由西南到西北诸省份的游历,旅程中难忘的事情,然后又说到多年拍天文摄影积累的心得。主持人夸他是个有感召力的人,总想唤起别人的兴趣。访谈进入尾声,主持人准备一些常规的问题叫他作答,以便凑够时间。问题都很无聊:对你影响最大的一本书是什么?你最想去的地方是哪里?可不可以问你一个私人一点的问题:你有老婆孩子吗?
“……你最尊敬的人是谁?”
他不再对答如流,沉默了好一会儿,然后开腔:“你可能想不到,我最尊敬的人,并不虚无缥缈,他就是我身边的一个朋友。一个很普通的朋友。我有一段做警察的经历,是辅警。那时候认识一个兄弟,他一直令我印象深刻。”
“为什么?”
“我也没法说得清楚,说得清楚,可能也没这么深刻了。”他表情变得用力,想组织精准的语言,“我这个朋友,其实他没有任何突出的能力,放在人堆里,谁也不会注意。但是我知道,他有一种平静,一种很罕见的淡定……这个朋友,不会因为你是百万富翁就鄙视你,也不会因为你一无所有就高看你一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