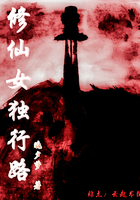闷葫芦一言不发,谨慎地用灵力包裹住灵牌,摄来细看。灵牌泛着乌光,与他们几个的无二,确是外门弟子之物。
“此处大概是某位师兄的临时住所。”七人查过一遍,屋内干干净净,吃穿用度的东西不少,看样子是有人居住。
“还是再查一遍为上。”云琯心里凉凉的,感觉屋子十分阴寒。虽说修士时常隐匿气息,可总会留下些许痕迹,哪里会一点人气都感觉不到。
郑凌言等人也觉得古怪。进入这窝棚内,外面那种阴森之气有增无减,四面灰色的墙壁似乎透着森森恶意。
白晓蝶累坏了,见几人都在身旁,悄悄放松了心神。手臂杵在桌子上,她无意间瞄到桌子下方有一个暗格。打开来看,其内有几十个精致的玉盒。玉盒上面没有任何禁制,稍稍一碰便启开了。里面,竟是一株株的灵草。
鬼雾草,冥莲花,魂清草,曼陀花,鸡冠草,水笼草……白晓蝶眼花缭乱地看着这些千年火候的灵草,激动的小脸通红,直唤大家来看。
“白晓蝶,别碰这些!”郑凌言叫道。
“你们看,你们快看看啊!”白晓蝶双眼迷离,将玉盒一股脑搬了出来,灵力一挥,将它们齐刷刷地打开,晾在诸人眼前。
“不……”云琯眼前一暗,身子一轻。再抬头间,太阳穴酸麻的只想睡去。揉揉脸颊,打个大大的呵欠,睡眼惺忪地四下望去。
这是哪里,她这是在做什么?之前的事情全然想不起来,混沌的如同一锅粥,一想脑袋便疼得厉害。
“这是在,在自己家里?那我为什么浮在空中,前面挡住视线的,又是谁?”
云琯捏了捏自己的手臂,痛得很,不是在做梦。可她真格地飘在空气中,眼前就是她熟悉无比的温馨美好的家,家里还是如往昔那般一尘不染,老娘子还是跟前时一样围着围裙勤劳地拖地。
往昔?前时!
云琯甩甩浆糊一样的脑袋,不知时间过去了多久,她又如何会有这种感叹。
老娘子在哭?老娘子在哭!
云琯望着老妈正拖着地板,突然双膝跪在地上痛哭出声。老妈哭得腰都弯了下来,捂着嘴急急奔入她的房间,抱住她的相片,无声地流着眼泪,渐渐小声哭了出来,把相片贴在胸口,哭得撕心裂肺。
“妈妈,我在这里,别哭了妈妈。”云琯心口剧烈的疼痛,老妈的眼泪滴在她的心口犹如烈焰,令她难过的要死。
“你不能过去!”身前挡住她去路的男子回过头来,冷冷地道,“你的任务没有完成,这一世,你永远都不能回去!”
“为什么?”云琯看不清那人的脸,可她真的很有撕人的冲动。“我何时接过你的任务?为何不能回家?”
“你是我周公选中的人,没有那么多为什么。”男子回过身去,再不理踩。
杀了他,杀了他!杀了他,你便可以回家!云琯气愤地握紧双拳,心中蓦地划过一个念头。
这个念头愈来愈浓烈,在她脑海中大声地叫嚣,越叫越急。云琯全身都紧绷起来,竭尽全力克制住自己,只怕一个忍不住,就要上前将那人生生撕碎。
“云琯,云琯,”老妈悲戚的哭声如同催命符一般,令她的手臂不由自主地抬起,直直点向男子的百会穴。
嘭。
眼看就要一指戳破那人的生死大穴。云琯的头上忽地挨了一记重击,咚地一下陷入了黑暗。
碧玉扔下树枝,无视离云琯一步远、直直挺立的刘中书,用阴气裹住她平放到一旁的大石上。
待碧玉转身回来,其余那六人还在神思迷离地晃悠着,两两对峙,口中都在各自呓语,说的话根本不着边际。
“凭你们也想打劫我?”刘中书的声音,听上去分外悲怆,“老子从小,最恨打劫!如今已是元后大修士,居然还有人不长眼睛撞上来!你们看老子好欺负是不是?老子虽然为人低调,可也不是软柿子!炼气期有人打劫,筑基期有人打劫,结丹期有人打劫,元婴期了,老子在宗门好好地修炼到元后才出门,竟然又遇到打劫!天道这般玩老子,老子就先让你们玩完好了!”
嘭。一根树枝敲在头上。刘中书大手伸向其他几人的方向,无力的倒了下去。
“你放下我的孩儿,我留你一条生路!我把我的储物袋都给你,你把孩儿还给我!她是我与师兄的血脉,是我千辛万苦凝聚的骨肉!求你了,放过我的孩儿!”郑凌言一头长发扬起,面容凄绝,双掌雷力涌动。
嘭。倒下去的时候,她的眼角滑下一滴眼泪。多少年不曾哭过了,郑凌言想着,闭上了眼睛。
“师弟,宗内安排我做掌门,你竟对我暗下毒手,害我停滞结丹百年内,无法进阶!你自己趁机自荐席位,做了掌门!你可知那掌门之位,我根本不在意!你如此不顾兄弟情义,实在令人齿寒!今日我已成婴,你我一决高下,就此断了你我之情义!”施阳泽大喊,百鬼幡被他用力抓在手中,手指关节铮铮泛白。
嘭。
那边的白晓蝶正好扑了过来,险些扑在碧玉身上。碧玉连忙躲开。
“我喜欢元师兄,喜欢了他几百年。你不喜欢他,你去劝劝他对你死了心可好?我也能有一丝的机会。答应我,好吗?”白晓蝶咕哝着,嘭地伏在了地上。
“我自从修出剑意,便走上了剑之一道。从未回头!今日你为魂师,我为剑师,天下第一的名头便在你我二人之间。无论胜败,我与你惺惺相惜,愿结为至交!”闷葫芦并指成剑,在身前比出一式,没等碧玉过来,纵身扑倒喃喃自语的巩承昊身上。
巩承昊高喊着,“师妹,不要跟他走。你若跟他走,我就杀了他”,使劲抱住闷葫芦,用力地想要把他揉进自己怀里。
闷葫芦推着他,并指成剑在他肩膀上戳了戳。还未等爬起,嘭嘭地挨了棍子,耷下头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