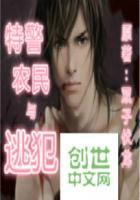第十八回搓破的窗户纸,看不见的迷雾
陈林建的手在颤抖,他在极力的克制住自己,现在绝不是杀李蒙的最好时机,他要活着,活着看李蒙死。
李蒙感叹道:“女人就是女人,有时候天真得要命,她既已知道你的身份,就知道我绝不会杀你。但她生怕你受了苦,为了让你少受苦,只有她自己委屈点。”李蒙没有敢太张扬,他怕真惹怒了陈林建,到时候鱼死网破,对谁都没有好处。
李蒙站起身,他该说的已经说了,该做的也已经做了,现在已经没有留下来的必要。
“明日我就带你去见那群人,他们会很好的对待你。我现在要你做的就是做一个废人,彻彻底底的废人。”
李蒙打开了门,一股强风吹乱了陈林建的发,也吹乱了他的心。
“小翠呢?她也是你们的人?”
李蒙道:“她是一个女人,很普通的女人。”
一个很普通的女人,看惯了冷眼,受尽了委屈,想要找一颗大树依靠,这本就是很平常的事。
门已关上,他端起酒壶,默默的喝着酒,喝着苦涩。
天已放晴,昨夜的风丝毫没有在人们心头留下痕迹,地上有几片被风刮落的碎瓦,一双脚把碎瓦踏得更碎。
几个大汉拦住了这个人,表情严肃,仿佛他们本就是不会笑的。
小米抬起了头洁白而华丽的衣裳在阳光下闪着光,把她整个人都照得清秀,漂亮。
小米皱眉道:“你们是什么人?”
大汉依然没有任何表情:“杨府的人。”
小米道:“杨府?”
杨府,杨坚的府邸,大将军府。
府内一个人正端着茶细细的品味着,茶和女人一样,都需要去细细品味,不懂得喝茶的人,也不懂得品女人。
他的眼睛敏锐而温柔,看见女扮男装的小米,他的笑更加迷人。
小米不客气道:“你找我干什么?”
杨坚道:“我找你来做我的客人。”
“我不需要你找我做什么客人,我不是你的客人。”小米的话和她的鼻子一样坚挺,倔强。
杨坚笑了笑,放下茶杯,在小米面前恭敬的行了个礼:“你是陈林建的朋友,当然也是我的朋友,我请朋友来做客是很应该的。”
他的行为谦虚有礼,不仅不生气,反而更加客气。
小米面上一红,激动道:“他在哪里?”
杨坚知道她是在说陈林建,故意逗她,道:“你说的是谁?”
小米道:“当然是陈林建。”
杨坚笑道:“你倒是蛮关心他的。”
小米道:“我关心他是因为他是我的朋友。”
杨坚疑惑道:“没有其他什么特别的原因?”
小米不解道:“什么特别的原因?”
杨坚仿佛很开心,立即道:“当然不会有什么特别的原因,他是你的朋友,也是我的朋友。他现在过的还可以,他要我好好的保护你。”
小米不屑道:“保护我,你?”
杨坚道:“我不可以保护你?”
小米手摸向了背上的弓,一个凌厉的动作,半空中一只悠游自在飞的鸟儿就已落在了地上。小米道:“我不需要你保护。”
杨坚眼睛都看呆了,许久才拍手道:“好,好身手。”
小米在大堂内,堂内的阳光不如屋外,可她却能一下子射下一只飞翔的鸟,这种身手在杨坚军中已经找不到了。
“我走了。”小米话已说出,人就已迈出几步。
杨坚慌忙抢上去,拦住她,道:“公子就这样走了,我怎么向陈林建交代,况且你出去也是找不到他的。”
小米沉思着,他说的也不无道理。
杨坚看事情又了好转,道:“既来之则安之,我马上就要离开这里,府中的家丁还要公子照看。”
小米好奇的看着这个陌生人。
阳光照射在这个与世隔绝的山林中,只有少数的鸟儿能停留在这里休息。山林中有几间看起来还算结实的木屋,其中一间最大的就是带头人的居所,也是所有人集结的地方。
带头人是一个三十来岁的人,他总是喜欢待在没有阳光的地方,白皙的皮肤好像本来就是照不得太阳的。他的手指纤细、修长、白皙如玉,这应该是一双女人的手。
但他确确实实是一个男人,他这双好看的手,不知杀过多少人。
若是有人问他的手为什么这么好看,他一定会告诉你,因为用人的生命滋养过的手,总是很好看的。
他手上玩弄着一把七寸长的小刀,刀柄漆黑,刀刃雪亮,没有会去小觑这把刀的威力,只要他能看见的地方,他都有法子把刀子插进对方的喉咙。
他这辈子只失过一次手。
那是他还年轻的时候,那个人要比他高大,比他苍老。那人穿着一件红色的披风,在巍峨的山崖上,好像世间已经在他脚下。
当他的刀刺向那个人的时候,他只看见那个人的微笑,那种居高临下,威风自信的笑容。
那人只是用手在胸前一划,小刀就在那人的手中二指之间夹着。
那一天是个很平淡的黄昏,却改变了他的一生。
他是前朝旧臣的儿子,他父亲手下有很多想要复国的能人异士。但他生性孤傲,且年轻气盛,但遇到那个人之后,他完全改变了。
那个人告诉他:“想要超过我,就必须超过你自己,没有任何一种武功高得过权利。”
那一天后,十几年来,他努力经营着这个小小的组织,因为他相信总有一天他能超越那个人。
他一直坚信。
一个四十几岁,衣杉褴褛,手里紧紧握住一个酒壶,酒壶是灰色的,和他的衣服一样灰。
他站在带头人的后面,摇摇晃晃,好像一个不小心就会摔倒。
带头人冷冷道:“大哥,你喝的太多了。”
“大哥?”他好像听到了世上最好听的笑话,他在笑,笑的却很沉闷,“你才是大哥,我只是你的跟班,从前是,以后也是。”
带头人的嘴里苦涩,想说什么,但又说不出口。
他们本是同胞兄弟,大哥是个生性自由浪荡的人,无拘无束。带头人从前也是一样的,他们从前的感情很好。但自从带头人接管了这个组织后,兄弟的感情一日不如一日。
带头人离开的时候,脑中反复响起儿时的欢声笑语,他的大哥年长他十岁,大哥的风流倜傥一直是他追求的目标。
现在他真的变了吗?
一个孩子蹦蹦跳跳的跑到那个醉汉的跟前,道:“大伯,你去跟我玩一会儿吧。”
醉汉摸摸他的头,就像儿时摸弟弟一样,那个时候他的弟弟也是这样缠着他。
醉汉道:“你去找你父亲吧,他好像很有时间。”
小孩撇撇嘴,一脸的不情愿:“我父亲笑都不会笑,有什么意思。”
小孩永远都记得,他的母亲都是留着泪,泪水好像从没有干过。无论他的父亲是怎样的了不起,他都瞧不起。
带头人绝不是个好父亲,更不是个好丈夫。
直到他的母亲死后,他没有和父亲说过一句话,他倒希望醉汉就是他的父亲,虽然醉汉整天只知道喝酒,但起码会笑。
醉汉道:“听说今天要来一个客人。”
小孩道:“哦?是什么样的客人。”
醉汉道:“是个很无聊的客人,但如果你去逗他,他也许也会变得很有趣。”
小孩又蹦蹦跳跳的走了,醉汉的眼角似乎有泪光,一个有很多心事的人才会借酒消愁,虽然他知道喝酒并不能解决任何问题,但他还是每天都醉着,希望永远都不要醒过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