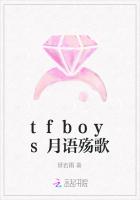李鸿章从曾国藩那里争取到主帅之职,这并不稀奇。他本来就是曾国藩谋划此事的主要助手,顺水推舟即可遂愿。但令人惊奇的是,他像变戏法似的一下子变出一支淮军来。
当时,从合肥一带招幕的淮军新兵在同治元年(1862)一月十五日以后才陆续赶到安庆,二十四日建旗立营,一个月零十二天后即登轮开拔。但即使这样,朝廷还嫌太慢,气得李鸿章大叫:“不是可以咄嗟办好的!”看看这批半像土匪、半像痞子的褴褛之众,看着他们又傻又惊地在安庆城外逛街,真叫湘军老兵好笑好气;土得叫人倒胃口的乡巴佬也能打仗?曾国藩也满腹狐疑,并深以为忧地说,“淮军纪律未娴、战阵未熟,恐怕不能够满足吴人云霓之望。”曾对该军有“不整不严”之评。
但出人意料的是,这支军队不经训练即可投入战斗。观察者只注意其外表,却未注意其内在。他们绝大部分是久经沙场的老兵油子,是淮河平原上与太平军、捻军步骑精锐长年死缠蛮搅打拉锯战的角色,是团练中的佼佼者。李比曾更了解他们。他们的土是土豪土顽的土,他们的野是野蛮野兽的野,他们在狠命杀伤对手、精心保存自己的土兵素质上,并不亚于湘军,李称他们“勇烈冠时”。他们大部分来自合肥西乡,那里是淮军属下铭军、盛军、树军、鼎军的故乡,其好战好劫之性令人吃惊,当太平军来时,他们齐攻太平军,当太平军走后,各部自相残杀。以周盛传为例,在淮军建军前他率部已作战296次,死伤数千,他兄弟六人死去四人。李后来感叹说:在上海招募这样的兵太难,他们比半是大烟鬼、半是可怜虫的上海清军要强得多。曾国藩说他们“野气未除”,其实正是其长;李鸿章对此甚为得意:“敝部淮勇能战而多土气。”
他们中间也有豪杰人物,后来涌现出一批海内驰名的淮军名将。他们使李鸿章青史留名,李鸿章也使他们留名青史。李鸿章就曾喜不自胜地说:“合肥的英俊多数跟随我。”其中有他称之为才识品行为合肥“后进之冠”、曾国藩称之为“皖北人才”的新科进士刘秉璋;有从小与刘秉璋一块偷了家里东西去北京游玩,以随机应变、善战好谋闻名的亡命之徒举人潘鼎新;有一个以勇著称、另一个以谋见长的张树珊、张树声兄弟;有外貌白皙清秀、气度不凡的吴长庆。还有刘铭传——浑号六麻子,十八岁就杀了一个欺负他父亲的大土豪,长得短小精悍,好色爱酒,惯贩私盐,打起仗来骁勇异常。
其实,李鸿章要把合肥团兵都请来是不可能的,一开始召之即来的人数并不多,只是到后来才陆陆续续多起来,并越来越服膺这个同乡。起始之际,有的答应去而未成行,有的走到半路或到了安庆又恋乡回返。李鸿章急中生智的应急法是“乞”,即向湘军各部乞兵乞将。但此事并不轻松,湘军诸老曾像打发要饭的乞丐那样不肯让出自己的人马。李则活赛老牛筋,死缠硬磨,并几百几百地了讨到一批批老兵。李带到上海的兵将五千五百人中,他自称湘军占二千,若仔细核实的话或许更多;稍后增至十三营,内有八营从湘军调来,故上海人叫它们为湘军,史家记之为“淮军初起半楚勇”。李的本事在于化湘军为淮军,而这支军队不久便统统变成了他的淮军。
像洋务奇才郭嵩焘,被公认是难以延请者,李能使他屈就苏松粮道之职,并专门放一艘轮船去接这位怪人来沪。李鸿章所以特别推崇郭嵩焘,除了他俩是丁未科同年、政治见解相似外,还由于郭嵩焘能够起到密切曾、李关系的作用。曾国藩与郭嵩焘既是亲密朋友,又是儿女姻亲,曾国藩四女纪纯许配给郭的长子刚基。郭嵩焘起初不愿屈就丁未同年的司道属员,后经李鸿章的恳切请求、曾国荃的再三劝驾,才赴沪接任苏松粮道。按清制,郭嵩焘不能在儿女姻亲曾国藩两江总督辖区任职,例应回避。同治元年(1862)十月李鸿章以江苏军务正殷、需才孔亟为由,奏准郭嵩焘勿庸回避,即以苏松粮道襄办军务。随后又函告曾国藩:“筠仙到沪后,众望交孚,其才识远过凡庸,运、藩二篆均可见委,惟至亲避嫌,鸿章以襄办营务入告,似尚大方。拟仍令兼管捐厘总局,以资历练。”不到半年,李鸿章就函请曾国藩奏保郭嵩焘为两淮盐运使,还拟荐举他兼任江苏按察使。来沪前,李一眼看出二十五岁的落魄书生周馥才识宏远、沈毅有为,能胜巨任,立即聘请这位年青的失意者入幕办文案,参与机要。果然,周馥后来成为李的重要助手,四十年如一日,李辞世之日,周馥还为他送终。周馥语及自己穷途遇到李赏识之事,把李比作周公:吐握余风久不传,穷途何意得公怜!李对其收揽的人才确含浓重的感情色彩。幕客陈琦在上海病死,李对其家属十余口照顾甚周。从曾国藩处借来的爱将韩正国战死,李表现出的情绪是朝夕悲怆,给部下留下了深刻印象。
最令史家吃惊的是程学启之例。程为李手下第一员大将,淮军早期以程战功最著,在程被太平军击毙前,淮军中没有人能越过他坐在李之下的第二把交椅。这个矮个子的文盲将军原是太平军将领,李邀他同去上海创业时,程心情压抑,初时不肯答应,但李的三寸不烂之舌勾起他的辛酸与野心后,他突然悟彻道:“宁为鸡口,不为牛后。上海固然是死地,然今朝湘军门户之见特别严,大丈夫仰人鼻息还不如一死。”程遂抱必死之心赴沪。说起死,程在投降湘军时就曾想到过自杀。当叛徒的日子难熬,曾国荃曾叫程率归顺的太平军在壁垒深沟外筑营,叫程部首当其冲地拼命作战。送军米时用大木头在吊桥上推出来,推毕收起吊桥与大木头;曾国荃总怕他反叛,认为只有把程杀了,才能一劳永逸地免去麻烦。程虽幸免一死,却免不了受排挤。程为曾家拚死卖命,陷安庆时首先占据最险要的关隘,首先登上城墙,打开城门,可功高赏薄,只升到参将,皆因曾家嫌他出身不光彩。但李鸿章却对他很赏识,便趁机与程拉同乡关系,并对他说:“湖南人鸡犬升天,客籍人颇难出头。”一席话就把程拉了过来。至于程顶着降将的帽子,李又巧言为他解忧:“江南人爱降将张国梁,你要去,又是一个张国梁!”
程学启遂改换了门庭,上海、苏南成为他用武之地。到该年末,清方官将都承认:就军事才能而言,程应占湘淮两军的魁首。他的恩主李鸿章也对自己的伯乐之识极为自矜,是他把像叫化子一样在湘军中讨饭吃的程学启提拔上来,并一鸣惊人的。李称程多谋善战,用兵如神;称程“冠绝诸军”,“为十余年来罕见之将”;称程统率的原是太平军的开字营兵丁,精悍而有纪律。郭嵩焘对湘军将领一向颇多微词,但他亲睹程部战阵并与程交往后也甚赞其人,赞叹程部每战屹如山立的军容。郭曾在上海与程论兵,称后者“尤有卓见”,并在日记里写道:“(程)刚厉有威严,淡于嗜欲,行军整肃,有古名将风,足为湘淮诸军之冠。”上海人说程“有战必捷”,显有夸大,但善战是肯定的。
程学启于同治三年(1864)年三月十一日死于破伤风。其间淮军的硬仗几乎均由他唱大轴。李在沪甚爱同他叙谈,认为:“同程学启论兵事,总有进步与得益。”而当程的噩耗传来时,李曾大呼:“左臂膀断了!”而曾家兄弟在对待程学启一事上,早就感到懊悔了,曾国藩就曾说:“部下诸将没有一个比得上他。”因而从同治元年(1862)八月起,曾氏兄弟就一再向李鸿章讨程学启回湘军,但李鸿章却以“这是明公的恩赐……感谢我公为国储材”,“明公赠将予我,我不能完壁归还明公了。”以此婉拒。
李鸿章对程学启的宠信,表明李不仅对安徽老乡能一视同仁,进而对当过太平军的、历来受歧视的人也能施以恩惠。李的集团由此壮大起来。李虽然对太平军痛恨切齿,杀起太平军来不比曾国藩手软,但他敢用降将降兵,起到了意想不到的效果。进军上海和苏南的太平军将领中安徽人占一半,其中不少人后来都被李拉了过去。
李鸿章在上海搭班子拉圈子时,其待人之宽厚之举也确实令部下心折。李不重门户、不重出身。在他的淮系核心分子二十六人中,只有五个人是有功名的。而且李鸿章对其下属百般庇护,给官、给权、给钱,使其部下有恃无恐,形同放纵。一次,刘铭传部兵丁把奉贤县令杨溥殴毙了,当曾国藩责问此事时,李回答道:对部下“鸿章从不稍假词色”。而刘秉璋鞭笞道员,道员对李言之:“大清二百余年,无鞭挞道员之理”时,李却强词夺理地说:“身在军中,当从军法。”李甚至还公言,对部下“一切小过,悉宽纵勿问”;闯大祸,“其咎与怨,皆鸿章一人承担”。李还在行辕内布置一淮北家乡土炕,常与部将在炕上拉家常。上海人都晓得,李对安徽人“乡谊最厚”。直到晚年,只要乡人来求他,总能得到点好处。与曾国藩的“驭下须严”相比,做李的部将无疑要舒服些。
这支从故乡、从湘军那儿“乞讨”来的军队,这批骄横的将领,李鸿章都能控制得住吗?应当说,李基本上羁魔有术,稳坐主公交椅,无人可取而代之。李早在十几年前就结识了好多淮上好汉,在那时与刘秉璋已结为师弟关系。刘秉璋曾拜潘鼎新之父潘小安为师,李顺藤一拉就拉到一帮子人。在李家父子办团练时,李鸿章得以广交乡勇豪杰,即使他在多年潦倒中,也不忘与他们保持联系,所以湘军攻陷安庆后,刘铭传等主动到安庆来找李接洽。李苦心竭虑地用宗族、乡情、邻里、师生、亲属等人际关系所编造的这张关系网无形而有力,在淮军官兵集中的合肥西乡具有深入人心的束缚作用。李动员自己的家人前来相助:在广东任粮道的兄长、老大李瀚章助购军需,三十六岁的弟弟、老三李鹤章来沪统率亲兵。二十六岁的老六李昭庆,陪同来沪参与戎机,有手不释卷的儒将之风,才干不比李鸿章差到那里。李鸿章很喜欢他,以其子经方为己出。两个妹夫张绍棠、贾同启也来沪助办军事,张绍棠升到提督。至于像李的内兄赵继元,恃势揽权后当上了两江军需局总办。
在摆布下属和本集团成员,使之听命于己或奉己为宗主方面,李堪称伎俩高超。满足其所需是一方面,而使其畏惧也不可或缺。李对当年安徽巡抚福济教他的秘诀牢记不忘:“时时以不肖之心待人,”决不能使手下诸将和睦,预防部下协谋不利于己。但李比福济还技高一招,福济做得过分了,造成主要将领相互猜忌以致失败;李则做得恰到好处,既能操纵,又可促其奋战。李纵横捭阖,决不会让任何一个跟随者强大到可以对自己的宗主地位提出挑战。各部下只许拥有对本部官兵的统治权,绝无相互统辖权。
同治元年(1862)一月二十一日,湘军自上海购来的一艘轮船抵至安庆,但曾国藩舍不得把该船交给李用作运兵,即使圣旨谕令轮运,曾也不松口。一个月后,上海官绅雇用的七艘轮船驶至安庆,而此时李的先头部队一千五百余人已开出安庆东关,只得又赶紧去把他们叫回来。然而,要不要全军坐轮船去上海成了湘军总部争吵不休的急切议题,好多老将进言:“不熟悉夷情,五千人马上洋轮冒险太悬太悬!”李差一点因此不能成行。
二月二十八日夜,曾国藩与李鸿章苦苦商议到天亮仍拿不定主意。但上海在召唤李鸿章,使他横下心决定孤注一掷。三月七日,众将官在提心吊胆下,率领着二千一百余人于上午七时许登上了三艘轮船,他们全是从湘军处借来的,带队者为程学启、韩正国、周良才。此时李鸿章人藏诡计:先让借来的湘军冲头阵,自己第二天再启航。轮船九时许起锚,起锚前曾国藩心里还是舍不得自己的家当,亲自到一艘艘轮船上去看望官兵们。也许他得到了李鸿章面许程学启下江甫当张国梁的情报,所以特地拍着程学启的肩膀勉励道:“江南人夸张国梁不绝口,你去江南,又是一个张国梁。我等着听你克复苏州的消息!”
李鸿章是在曾国藩训导、提携下发迹的,但曾国藩对李鸿章能否胜任援沪重托仍然心存疑虑,既担心李鸿章因缺乏阅历而摆不正“练兵学战”与“吏治洋务”的位置,又害怕李鸿章因思想个性而莽撞胡为。因此,在李鸿章离开安庆之前,曾国藩“临别赠言,谆谆以练兵学战为性命根本,吏治洋务皆置后图。”他知道在封建的中国“有军则有权”的道理,告诫李鸿章要把军事放在首位,在他看来,只有练就精兵,学会作战,才能站稳脚跟,飞黄腾达,否则将一事无成,甚至有丧失生命的危险。他还看出李鸿章心高气盛,急躁,傲慢,任性,这些致命弱点如不改正,后患无穷。因而曾国藩“以深沉二字”相劝,其他好友也纷纷提出忠告。李续宜“以从容二字”规之,沈葆桢、李桓“又以勿急相戒”。李鸿章深受教益,在给李桓的复信中表示:“手谕诲爱谆切,感佩无量。鸿章素性激直,从事师友贤豪间,皆深知其戆而曲谅之。自兹以往,不欲蹈习官样,又未便率性而行。”对于师友们的劝诫,“当奉为枕中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