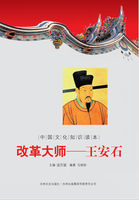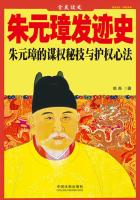按照清朝的制度,革职的官员不得专折上奏权,凡皇帝的谕旨皆由大帅传知。因而每次听到提督、总兵喊:“听圣旨”,曾国藩叩头大拜时的难堪,不仅让他失去了自尊,也让以师事曾国藩的塔齐布等颇不自在。但曾国藩对此却一筹莫展。原来,康熙皇帝发明的这项“专利”,是专为勾通上下之情之举,即让最亲近的人专写奏折,由皇帝亲自批阅,再交上奏人执行。可谓单线联系,是连接最高层中枢神经的“特权”。而到了雍正时,能奏折的官员更多了,除了总督、巡抚外,道府中的个别人也特许奏事。因而被剥夺专折奏事,则是最大的惩罚。更重要的是,臣情无法上达,皇帝自然很难了解下边人的苦衷,不能专折,只能“会奏”,即同地位身份相等的人一同上奏,但须意见一致,而且奏什么,大家都知道,因而也就没有什么秘密可言。更何况,皇帝下发谕旨属公文性质,由军机处“廷寄”,仍由巡抚、提督传谕。因此,曾国藩对皇帝如此“折磨”他,真是有苦难言。在当时,专折奏事虽不如老祖宗时那样灵要,但最普通的东西一旦失去,也觉重要,更何况这还是一件“秘密武器”。
李元度深知失去专折奏事权将意味着什么。他为曾国藩的前途忧虑,也为自己的命运担忧。
一日夜晚,李元度将一份《革职待罪臣曾国藩乞请专奏以速戎机事》的奏疏呈给了心绪纷乱的曾国藩。但曾见后却大为不悦,因为革职后专折奏请本属“犯法”之事,加之咸丰帝此时猜忌很多,上奏的结果肯定会凶多吉少。他以为成功的可能要小于加罪的结果。
李元度说:“设无此项权利,他人沸沸扬扬,日达圣上,而我终不发一语,是人为刀斧,我为鱼肉,是非无以辩白。”
“此中利害,我岂能不知。只是军中情形复杂,不逊朝中。当此国家多难之时,做正人难,做正人君子更难,欲做愤然不欲之官难上加难。”
但李元度一再坚持,并以受死赴难相请,曾国藩只好听天由命。
后李元度又将原折一改再改,并以军情变化万端,随时奏报圣上为主旨。写完后,密封上达。几日后,朝廷即下谕特许曾国藩单衔专奏。这不仅是皇帝打破常规之举,也是曾国藩获得的“异数”之一。
李元度为曾国藩争取专奏权后,曾对他更加信任不移。两人卧同室、游同舟、饭同食,形影不离。而似奏折信缄之类,也大多出自李元度一人之手。此后,曾国藩九江之败,南昌之困,“元度无不相从艰危中,多以勖助。”而曾国藩的多次寻死觅活,也“皆以元度防救得复”。
太平天国翼王石达开自咸丰五年(1855)十一月十九日出安庆,坐镇九江后,使太平军战局转危为安,后又三度反攻,消灭了号称无敌的湘军水师,并将湘、鄂、皖三省联军一一击溃。六年二月十七日秦日纲又攻克武昌,致使曾国藩苦战半年打下的城镇得而复失,湘军精锐,溃不成军。曾国藩自杀不死,黯然逃到南昌,又一次饱尝了冷讽热嘲、奚落讪笑之苦。连他自己也说:“乙卯(咸丰五年)九江败后,赧颜走入江西……丙辰(六年),被困南昌,官绅人人目笑存之。”
他又说,这一次惨败,是他的平生四大惭(耻辱)之一。所谓六年丙辰被困南昌之役,他也是败给翼王石达开的,而那时的情形要比此次更惨。曾国藩诚然中兴名臣,但是在用兵破敌方面,比之勇武绝伦、胸中有十万甲兵的石达开差得远了。将新建湘军武力葬送无余,是他一生中最痛苦的经验,也是他平生所受到的最大的教训。
不过曾国藩还真没忘了他的这位师爷。咸丰四年(1854),他以收复湘潭功,保升李元度为知县,加内阁中书衔。在半壁山、田家镇诸多会战中,李元度又因立功卓著,被保升同知,赏戴花翎。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咸丰四年底,曾国藩率湘军水师入鄱阳湖,在湖口为太平军所阻。太平军得悉湘军在外江,大船势孤,便出小船迅速包围了曾国藩的坐营,同时放火烧船,船借风势,直入曾国藩营垒。湘军水师当时尚无三板船,无法抵抗,因而几十艘船顷刻化为灰烬。次日,太平军又将所获船只改装成官军模样,据湖口上游诱使湘军跟进,至湖口又断敌归路。随后,太平军又展开了猛攻,湘军水师不支,守备王荣等部死伤甚多。曾国藩的坐船也被团团围住,无望中,他再次投水自杀。李元度见状舍身相救,拚死力终将曾国藩抱过了江,使曾国藩再一次幸免于难。可以说,李元度此次与曾国藩确有救命之恩。
曾国藩惊魂未定地到了南昌后,开始整顿水陆两军,总结自三月以来岳州、靖港、湖口三次大败的原因。当时跟随曾国藩的幕僚已不多,一是因为曾国藩连遭失败,一些人对他失去了信心,另谋他途。二是因为曾国藩不被清廷重视,跟着他前程堪忧。三是南昌更加危急,弄不好会同曾国藩同归于尽。望着如此冷清的场面,曾国藩心中空落落的,很不是滋味。他让众人指陈三次失败的原因,但大家都面面相觑,不敢乱讲话。
曾国藩一向看重李元度,他又有救命之恩,便亲点名号说:“次青,你大胆请言!”
李元度为人仗义,见曾国藩几次寻死觅活,总不得胜,心里也很着急。眼见这样下去,自己的前途也委实堪忧。于是他鼓足勇气,语未尽,已惊三座:
“恩公东下之师,气势锐甚。然自三月至今,凡经三次大挫折,初挫于岳州,继挫于靖港,今又挫于九江湖口。幸而屡蹶复振,未坏大局。然依在下之见,非失于恩公不知兵,而失于知兵。”
李元度的话,如芒刺在背,一针见血。众将领谁也不敢望一眼曾国藩的表情,只是默不作声地坐在那儿。空气骤然紧张起来。
曾国藩倒还沉得住气。他又说:
“次青请细道之,吾愿闻其详。”
李元度也不再犹豫,说:“岳州之败,师未集而因大风阻于洞庭湖,敌察我困,大股围入,其败可谓天意,于理于势都是如此的结局。靖港之败就不然。一惑于困丁之清,临阵变成谋,夕令朝改,是策略之失。九江湖口之败,问题就更大了。三板大船入湖,敌断归路,变出不测,以大船攻敌小船,无异猛虎拔牙,虚威无用。并且,师出不为退路着想,乃行军大急。犯此,则不能不败。”
李元度的话虽然当众揭了曾国藩的疮疤,但无疑是一剂良药,众将领不由地频频点头,已忘记了曾国藩此刻什么样了。
曾国藩善于听人之言,博采众长,以为己用,他的心胸是宽广的。此刻见李元度一针见血地指出了三次失败的原因,也颇觉叹服。于是他接着说:
“次青的话句句在理。望吾将士共当戒之。”他一生嗜棋如命,此时,话锋一转,以棋喻战:
大抵用兵之道,形同两人对弈,弈术高低备于棋谱,而临局走子,对方未必按棋谱走路,以符合我布下的阵。又如射箭,射经主要讲的是身正,但身正也未必都所命中。因为胜负都在变化万端之中。国藩不才,东下之师,胜败之情,也如临局发矢,优劣其见。孙子曰:“军争为利,军争为危,利危相倚,岂有常域!”次青的话我当铭记。
从此,曾国藩遇子讲一个“退”字,即不做绝人之路之事,凡子更多留几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