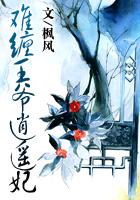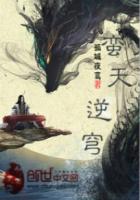“赵大人想说什么,大可开门见山讲。”提及洛神戏,沈月然像心脏漏了一拍,面色微带不愠。
“既然这样,微臣就坦诚来说。娘娘素有贤名,恰如从前的樊姬同文德皇后一样。可纵然娘娘洁身自好,在这后庭中出淤泥而不染。却难保他人不往娘娘身上泼脏水。”尽管见得不多,但沈月然对沈鸢然并非全然的姐弟之情,只是当局者迷罢了,“楼惠妃为何放了这么多折子戏本不挑,光选这出洛神?里头的人物、情节就连微臣这样的外臣都忍不住朝娘娘和侯爷身上套,何况旁人了?”
沈月然的护甲按在木质扶手上,登时出现两个清晰的凹陷,“微臣相信,娘娘和侯爷只是姐弟之情。但只是微臣信,娘娘信就好吗?娘娘得让陛下信,让后宫众人信,更得让群臣百姓信服。”
“不管是真是假,楼惠妃都铁了心,想让您和侯爷背上违背人伦,惑乱宫闱的罪名。既打击娘娘您,又能连累沈国公府,这样一来,她就能顺势而上,取而代之。”
“你说得确实头头是道,字字有理。那本宫想请教大人,本宫该如何摆脱这个困境?”沈月然收住情绪,松开按着扶手的右手,左右交叠放在裙上的金凤。
“这自然好办。”赵爰清看着沈月然,缓缓道,“让她在成功构陷娘娘前,先被构陷,一旦身陷囹圄,自身难保,当然没有精力来做构陷娘娘的事。”
“赵大人的法子好。可本宫向来不喜这些心机手段,明枪暗斗。”沈月然温柔一笑,恍若隔年,“楼家本是望族,源洲王叛变时,楼国公果然弃暗投明,深得陛下赏识,如今更是源洲第一大族。惠妃是楼国公的嫡长女,身份尊贵,轻易撼动不得。且惠妃做事,向来谨慎,想你也难捉住她的大错处。赵大人这番美意,本宫怕是要辜负了。”
沈月然话锋一转,“此外,还有一事本宫不明,惠妃同大人相识不久,并无结怨,相反的,本宫从乞巧宴上能看出,惠妃还是较为看重大人,不知大人为何一心想着除掉惠妃?”
“娘娘有所顾虑,都是情有可原。”沈月然的性子和上辈子一样,不喜斗争,只想安安分分地做好皇后,过完半生,“有件事微臣一直瞒着娘娘。乞巧宴晚上,侯爷被惠妃算计,误用了催、情、药,被惠妃的人引进一间宫殿。而那宫殿,恰巧是微臣暂时住的。”
“你说的可是真的?”沈月然平静的表情渐渐碎裂。
“在那后头没多时,沁夫人就带了陛下来。”赵爰清手腕上新添了一枚粉玉镯子,“微臣起初也困惑,想了许久,才琢磨出,惠妃之所以选了微臣,左不过几个缘由。首先,微臣虽只是酿酒局的女官,却是大荣皇帝亲自下旨派来的,要是闹到前朝。言官往大处说,可以给侯爷安个败坏邦交之名。二来,后宫私通本就为大罪。娘娘既是后宫之主,又身为嫡长姐,侯爷以身犯法,娘娘难辞其咎。”
“微臣之所以想帮娘娘,一则是还娘娘恩情,二则是为自身考虑。楼惠妃试图陷害侯爷与微臣不成,心中定然怀恨,说不清在哪准备着,想再次构陷微臣。为求自保,微臣不得不先发制人。”
“当然,娘娘金贵,不能因腌渍之事脏了手。”赵爰清道,“这些都是微臣一人所为,哪怕事情败露。陛下面前,微臣都不会透露一星半点。娘娘只需静静看着,坐收渔翁之利便好。”
沈月然像不信她,眼神中仍带打量。
“微臣明白,娘娘现在还不能不相信微臣。但日久见人心,娘娘早晚会知道的。”赵爰清看向沈月然手里的折子,“娘娘只需准了微臣这份折子,后续事务,微臣会自行安排,绝不牵扯娘娘半分。”
齐彦铭近来心情好,他和赵爰清的关系不知觉中改善颇多。晌午时分,酿造局还送了酒来。尽管是按规矩做事,但齐彦铭硬是自恋地相信,这酒是阿清专程酿的。
离晚膳犹剩半个时辰,齐彦铭有些焦虑。生怕哪个闹事的,半路请赵爰清去宫里用膳,将他的好事黄了。
快近饭点,内监还未来报告消息,齐彦铭不住猜测,是否是皇后留她用晚膳。登时坐不住了,恨不能到椒房殿捉她回来。可想起自己先前说的话,又硬生生坐回去。直到蹲守在椒房殿外的内监来报,说赵大人已经从椒房殿出来,估计在半道上了,这才松了气。
宫女收拾好桌子,摆上碗筷、凉菜,齐彦铭想到门口候着,又觉得不妥,不安地呆在原座。
内监被他一遍遍地打发去探查。
“大人已经到了御花园。”
“过了议政殿,大约只剩一盏茶功夫。”
“陛下,大人的轿子已经停在门外。”
轿子平稳落在地上,以木替她掀开轿帘,赵爰清看了看上阳宫外的蓝天,沉声道,“你在外头候着就好,不用跟我进去。”
“是。”
陆忠候了多时,忙替她开门,恭敬道,“大人,陛下在里面等着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