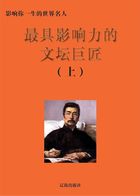张滴滴正想解释她不是那个张春花,村口又来了几个衣着稍微体面的人,其中留着小胡须的中年男人急急的过来拉开抱着张春花的老妇人。
“娘,跟我回去,你在这儿跟这个疯子磨蹭什么。”中年男子就是张春花的亲生父亲张树,他拉老妇人的时候,眼睛都不曾在张春花的身上停留一秒。
“你个丧良心的,你跟你那死鬼老爹一样,忘恩负义,春花怎么就是疯子了,你不过就是听了她娘舅老爷说她克你罢了,这样的混话你都信,这些年这孩子吃的苦,遭得罪还少么。”
老妇人狠心一跺脚,踩在张树的脚指头上,痛得张树抱着脚哇哇大叫。
后面几个跟来的男人上前来扶住张树,穿着长衫的黑瘦男人上前一步,狭小的眼睛在张春花身上扫视了一圈后,眼神诡异的微微点头。
黑瘦男人回身装作关切的样子拍了拍张树的肩,“张树啊,你可千万不能让这丫头回去啊,她身上煞气太重了,恐怕死鸡死鸭事小,而你是户主,要是你也·····”
黑瘦男人故意收了声,侧身一看,哪还有张春花的影子,就连张树的娘也不知道走哪儿去了。
刚才一群人都被黑瘦男人讲话吸引了,也没注意到张春花和张树的娘什么时候走的。
张树朝着地上啐了一口唾沫,挥动了一下拳头,“娘的,那死丫头要是今天敢进屋,老子就要打断她的腿。”
一群人朝着村里走去,村子西边有一座最大的白墙瓦房,柏树板子装订的大门,漆上浓重的黑色,铆着狮口铜环的门栓此时却被院子里挂红叠彩的氛围搞得有点滑稽。
满是酒香的院子里,村民们正在酒席间大块朵颐,听着简易戏台上崔寄芙唱的最新的花鼓戏。
账房先生算好了今天收的彩礼后就去内堂找正在那儿休息的张员外。
原本还嬉笑酒酣的院子里突然沉寂下来,张员外探头一看,竟然是他那老不死的老婆和他最嫌弃的傻孙女回来了。
账房先生见张员外脸色铁青,攥着手里的账本眼神示意让立在门口的长工去将人赶走。
张滴滴仰头看着门楣上的扁额,勾唇冷冷的嗤笑了一声,微微有些苍白的嘴唇轻启:“正孝至德。”
李氏似乎也被她身上的寒气震慑住了,微微斜着身体不解的看看张春花的小脸,自己的大孙女居然认识字。
“春花,我们走吧”李氏有些怯懦的拉着张春花的袖子。
“奶,你没看大家都盯着我们么,就这么走了岂不是就成了笑话了。”张春花反手拉住李氏,眼神定定的径直走到戏台旁。
“小哥,借你的铜锣一用。”张春花挽起破烂的袖口,露出纤细却布满旧伤的手臂,直接从年轻男子手里取过铜锣来拎在手上,径直走上了戏台。
院子里的那男男女女都吃惊的看着这个消失了大半个月的张家疯女,几个村妇相互耳语,有的男人抓了一大把瓜子在手里,吐着瓜子壳等着看张春花这个疯子出洋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