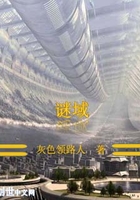我没料到前面有人,正和瘦先生说这话,一回头便撞进了一个人的怀里。
冬天因为天气干燥寒冷,本来鼻子就已经冻得红彤彤了,再给这么一撞,差点就当场鼻血横飞命绝于此了。
究竟是谁这么不长眼,壮得跟一堵墙似的?
我揉着撞得生疼的鼻子抬头一看,眼前的人竟然是应该和钱雅蜜一起在美国过圣诞节的彭奈。
彭奈今天没戴口罩,头上戴了顶黑色的宽沿帽子,正是今年流行的款式。
我惊诧的望向他那******不变的冰山脸,一时间说不出半个字来。
彭奈一把搂住我的肩膀让我转过去,对那位一路上都喋喋不休的瘦先生说:“抱歉,我女朋友跟我置气跑出来相亲,耽误了您的时间和精力,是我的不对,我这就回去教育她,保证她以后不敢出来沾花惹草了。”
瘦先生一愣,讷讷的重复:“女朋友?”
我张大了嘴巴望向彭奈,彭奈一脸淡定自若,搂在我肩膀上的手却愈加的紧。
他煞有介事的说:“是啊,她就是我女朋友。你是不是觉得我这么优秀的人看不上她这样又傻又笨的?别担心,我收服了一个她,你们这些单身的就少一点被迫害的危险。”
今天的彭奈太诡异了,平时惜字如金的他竟然一连串说了这么多话,把这位老实的瘦先生说得一愣一愣的。
瘦先生也是知趣的人,说了句“陆小姐,既然你有男朋友就不要出来扰乱相亲市场了”后就冲彭奈颔了颔首之后潇洒的走了,昏黄的路灯下就只剩下我和彭奈两个人了。
路灯的晦暗光线将我们的影子拉得好长,看上去像两根细长的竹竿。
彭奈摘下了温和的面具,露出原本冷漠的一张脸,对我冷哼道:“陆清晨你可真有本事,这就邀请陌生男人回家了么?”
我搓了搓自己冻红的手怒道:“你别胡说八道行不行,谁邀请他回家了?他想看《情深深雨蒙蒙》,我上去给他拿影碟。”
“是么?”
彭奈向前跨了一步,脸也朝我凑近了些。
“那你说说看,谁允许你跟别的男人相亲的?陆清晨你就那么饥/渴吗?”
饥渴?他竟然用这个词来形容我!
我现在就跟一只炮仗似的一点就着,听他这么说我就来气,瞪了他一眼道:“你又不是我的谁,管这么宽干嘛?”
彭奈忽然低声笑起来,眼睛里却是冰凉的,他在我耳边小声说:“我不是你的谁?你可别忘了,你那晚睡的人是我而不是谢思达。既然睡了,你就得负责。”
我浑身猛地一颤,抖着嗓子说:“对不起,这责任我负不起。”
我想起昨晚钱雅蜜的那段娱乐新闻,忽然觉得气不打一处来。
你分明有美女相伴,干嘛还要来这里招惹我这么个大龄剩女?
彭奈凝眸看着我,命令道:“上楼收拾东西去,今晚就给我搬回去。”
我又不是他养的一只猫一条狗,说起来他还得叫我一声姐姐,凭什么这样跟我说话!
我气得牙痒痒,梗着脖子说:“彭奈,你之前不是很讨厌我吗?我不住你家了不找你了可减少了你不少麻烦,你应该放鞭炮庆祝才对,好不容易解脱了现在又要往火坑里跳算怎么回事?”
彭奈一把钳住我的肩膀,一口的白牙磨得咯咯作响。
他说:“陆清晨,我既然答应了你要把这场戏演下去就不会临时退场,你也别想逃。”
我大着胆子抬头望向他的眼睛,嗤笑道:“你是不是扮演谢思达演上瘾了,连他的女朋友也要顺带给睡了?你能********,我总不能假装那天晚上什么都没发生或者只是被狗咬了一口吧?”
我以为彭奈会大发雷霆拂袖而去,谁知他只是瞪了我一眼,然后深深叹了口气说:“那你就当被狗咬了吧。”
我默不作声,嘴唇被自己的门牙咬得生疼。
彭奈拉了我的手往楼上走去,我拼命挣脱,奈何这家伙因为平时健身的关系力气出奇的大,我挣了半天也只是浮游撼树。
“干嘛呀?你不会也想借《情深深雨蒙蒙》的影碟吧?彭奈你丫的可别后悔,我陆清晨虽然不是个随便的人,但随便起来可不是人。”
彭奈顿住步子,回头意味深长的看了我一眼,而后打横将我抱起,往楼上快速走去。
“喂!你放开我!滚去找你的钱雅蜜去!”
我挣扎着用腿去踢他,可他却丝毫不为所动,反而加快了脚下的步子。
我租的小单间在七楼,因为是老房子所以没有电梯。
一个多月以前曾把王怡然累得只有进气没有出气,发誓再也不来这里了。
而我们的彭大神,跟吃了一整盒盖中盖似的,抱着一百多斤的我一口气上七楼,嘿,不费劲儿。
彭奈将我在门前放下,伸手抢过我的背包掏钥匙,我想抢回来,奈何他太高,我踮着脚就算踮成了芭蕾舞演员也够不到。
我气得大叫:“彭奈,你是流氓还是土匪,有你这么办事的吗?”
彭奈已经找出钥匙打开了房门,他停下来低头看着我,弯了弯唇角说:“流氓。”
我一愣,刚意识到他这是在回答我刚才的问题,就觉得眼前一暗,一道黑影骤然靠近过来。
我抬起眼,他的唇已经压了上来。
我下意识的往后退,后背却抵到了冰凉的门框上,铬得我生疼。彭奈长臂一捞把我捞回去,一边吻着我一边用脚带上了房门。
两个小时后,我躺在床上看白晃晃光秃秃的天花板,心里默念:世界如此美妙,我却如此的孬,这样不好,不好……
我也不知道事情是怎么发生到这一步的,反正它就是在我们俩谁也没喝酒的情况下莫名其妙的发生了。
我抓着床单欲哭无泪,谴责自己定力太差被美色所迷惑,没控制住自己导致悲剧重演。
上次我还能说自己是喝醉酒把他当成了谢思达,那么这次又该怎么解释呢?我想了半个钟头依然没能得出结论,最后只能颓然的翻了个身闭上眼睛。
彭奈似乎对我的这个不到二十个平方的小单间很不满意,当然,他对我的单人床更不满意。
因为床太小,我们只能侧卧着,他用指尖划过我暴露在空气里的后背,用他那把醇厚的好嗓子问我:“舒服吗?”
我肩膀抖了抖,脸不由自主的一红,恨不能找个地洞钻进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