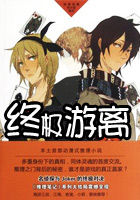“精神,你勾脸都那么漂亮。最近唱的这几出,牛皋、张飞、李逵、焦赞、鲁智深……乍看都是黑脸汉子,细看谱式各个不同,怪有意思的。”
“那当然啊,勾脸学问大着呢,‘红忠紫孝黑正粉老,水白奸邪油白狂傲,黄狠灰贪蓝勇绿暴,神佛精灵金银普照’,你看牛皋这个黑蝴蝶脸,跟张飞都是笑眉笑眼,但是比张飞更亲切更喜庆,”竹青凑到樱草面前,耸动眉眼,做了几个表情,“是吧?招人喜欢吧?”
“嗯,喜欢!眼角破开的这一块是什么花样?”
“是个蝙蝠形的笑纹。牛皋是一员福将,所以有蝠纹。”
“是不是还有一出戏叫《牛皋招亲》,藕塘关大胜,娶了文武双全的戚赛玉的故事?”
“就是《飞虎梦》,我师父编的戏,还没给我说呢,等我学会了就贴。”
樱草嘻嘻笑起来:“只在戏台上贴吗,戏台下头,什么时候贴?”
竹青捧着揩面用的草纸,转头看着樱草。他今年已经十九,自然到了招亲的时候,但是刚刚拜师入门,乃是一个伶人学戏唱戏的最好年华,暂时无暇顾及亲事。再说,他心里头,其实一直已经有一个人,只是这些年来,眼见着她与自己最亲密的师哥心心相印,他连吐露的机会都没有。眼下,这个人就坐在自己身前,茫然不觉地冲他笑着,还故意逗他:
“你这牛皋呀,最后不知是谁的福将?”
他一时心潮交涌,都有些维持不住自己的笑颜。他将草纸按在脸上,使劲搓了搓,缓一口气,方说:
“还能是谁的,一直都是你的福将。”
“哈哈哈,真的吗?”
“真的,”竹青把那件平金红蟒紧紧抱在怀里,朝着门外走去,“我一生都是你的福将!”
夕阳下的场院里,天青只穿一条扎脚布裤,赤裸着上身,挥起斧头将一段段树桩劈成柴块,汗水自他头上、脸上飞溅起来,肌肉虬结的肩背被阳光勾出闪耀的金边。妃红坐在灶间煮饭,一边拉着风箱,一边微眯着眼睛,含笑凝望他的身影。
栗大爷背着一只竹筐回来,见此情形,笑得满脸皱纹都绽出花儿来:“你这小伙儿太能干了!力气大,手脚又麻利儿,可帮了大忙了!你媳妇也是把好手儿!长得也那么立整儿,天生一对儿啊!”
“她不是我媳妇……”
“噢,还没成亲啊?”栗大爷露出一脸心知肚明的表情,笑眯眯地不再问下去。天青觉得很难解释,笑了笑,继续抡起斧头干活,没再说什么。妃红听见两人对话,也微微笑着,瞟一眼天青,不做声。
转眼已是中秋佳节,山里的天色,分外澄明,到了晚上,满天都是深浓而透亮的蓝,上面镶着一轮巨大的圆月,蟾宫玉兔,清晰可辨,月光如银,遍洒河山。栗大爷取出一坛自酿的米酒,和天青两人坐在院中对饮。
“要不是有日本鬼子这档子事,能在这儿多陪您些日子,也是神仙生活。我自小在北平长大,这么清静壮阔的山林,还从没见识过,可惜现下却是陷在鬼子手里。”天青感叹道。他素来不会饮酒,碍于栗大爷盛情,也小小呷了两口,顿时涌上满脸的红。
“你们文化人,给我说说这日本鬼子是怎么回事?凭什么就来打咱们呢?听说奉天城里满满的都是东北军,怎么就打不过鬼子呢?”
“我也不懂啊,大爷。我还是外地的。不过日本人真是禽兽不如,我一个老老实实的小师弟,什么都没做,活活被他们杀死了,尸首都捡不回来,一想起这事,我就……”天青狠狠饮干一杯酒,“可惜我只是个唱戏的,持刀杀敌那都是假的,真想拎着刀冲到鬼子堆里去砍杀一场,给我师弟报仇!”
“皇天有眼,他们会遭报应!”栗大爷也干了一杯,“我也舍不得你们走啊。你这年轻人,太招人稀罕了,住多久我都乐意。往后日子太平了,还能过来看我不?北平在哪疙瘩儿,远不?唉我的日子也不多了,估摸着就快去见老婆子了……”
“大爷,您是我们的救命恩人,等到鬼子滚蛋了,准来看您。您这地界儿我记住了。来,祝您健康长寿。”天青给栗大爷斟满酒,两人又一起干了一杯。晚风清凉,天青却觉得全身燥热,满头是汗,将夹袄和小褂的衣襟全都解开,用力扇着:“大爷您这酒力真劲!”
“呵呵,没事儿,这酒是自家酿的,不上头,再喝!再喝!……”
时至午夜,天青和栗大爷都喝得醉醺醺的,各自回了草房。妃红一直倚坐在天青的炕头上,只穿了一件贴身小衣,一边梳理着满头鬈发,一边瞄着院子里的爷儿俩。见天青歪歪倒倒地回来,赶紧放下梳子迎上去,搀他上炕,为他脱下夹袄,盖好被子。天青不肯躺下,在炕上挪了几步,跪到窗前推开窗子,仰望天上的月亮。
“我从没见过这么大这么圆的月亮,像画儿一样。”
“是啊,像画儿一样。”妃红回身倒了一盆热水,投着面巾,笑吟吟地看着天青。
“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见着北平的月亮。”天青说。
他的脸还是红红的,眼睛不似平时那么明亮,笼罩着一层淡淡的迷茫。这些天没有剃头,额前鬓角,都已被黑亮的发丝遮盖,下巴周围,一片隐隐的青色须根。浓而直的剑眉,笔挺的鼻梁,轮廓分明的唇,在月光映射下,分外清晰,投着笔墨勾勒一般的阴影。他专注地仰头望着月亮,轻轻哼起一段曲子:
常言道,人离乡间,似蛟龙离了沧海,
似猛虎离了山冈,似凤凰飞至在乌鸦群班。
昔日里有一位绝粮孔子,他也曾把麒麟叹。
况且圣人遭磨难,何况我韩愈谪边关……
妃红着了迷地听着,一时都忘了手中面巾,任它浮沉在水盆之中。这个男人!处处都让人这样动心……纵然已经与他同台那么多次,纵然看过他所有的戏每天都听着他唱,此时随口哼唱这么几句戏文,那嗓子,那音韵,那纯正的吐字归腔,深沉浓郁的情致,仍然让她听得头皮都发麻。窗边的天青,意识到屋子里的异样静寂,忽然停了口,茫然问道:
“怎么?”
妃红舒出一口长气:“你唱得可真好。咱们唱戏的,各行当都是自小儿立下的范儿,没法改,武生能唱个《二进宫》都是顶天的事儿了,你怎么连《雪拥蓝关》都能来?就算在老生行里,能来这戏的也没几位。”
天青笑了笑:“我来不了,只是跟着师父久了,听会一点。这是我玄青师哥的戏,暂且还没学,师父说等他火候到了,就传他。”
妃红深深凝视着他:“说句掏心窝子的话:我觉得他,绝不能有你唱得挂味儿。”
天青叹了口气,又转向窗外:“那是不敢。不过,师父说得没错,有些戏,得活到一定年纪,有了一定阅历,懂了戏情戏理,才能唱出戏里的真玩意儿。这段戏文,我从小哼到大,却只是在近些年来,人生遭际非比寻常,才愈来愈能领会到内里的情致……师父说,盼着我们永远不懂这样的戏,但是人这一辈子,就是一场磨难,生老病死,离合悲欢,谁能幸免?……”
他怅然停顿片刻,又接着哼下去:
……唉呀,难挨,难挨,
生死有命,富贵在天,发配到潮阳,路有八千……
如此悲凉的唱词,他哼着哼着,嘴角竟然微微弯起,有了一点笑意。
“这怎么,唱着唱着还笑场了?”妃红打趣道。
天青眼中,带着梦一般的迷离神情,微笑起来:
“这段戏啊,小时候樱草让我教她唱,我不教,结果她过来扳着我的脸,说:我笑一个给你看,你就教我,好不好……”
妃红瞧着他,轻声道:
“你真的很喜欢她,是吧?你没一刻忘了她。”
天青的笑容消逝了,仿佛头抬不动了似的,额头抵在窗框上。
妃红提起水壶,向已经凉了的水盆里加些热水,慢慢搅动,“喜欢女孩子,没什么不好啊。为什么要藏着,我还寻思,”她瞄他一眼,“靳老板一向光明磊落,事无不可对人言呢。”
天青仍将头抵在窗框上,闭紧了眼睛,脑子里微微轰鸣。不知是因为连日的奔波还是生死之间挣扎的困境,或者是夜色,或者是酒力,或者是因为妃红言语中饱含的理解,还有带着一点母性关爱的温柔,他忽然觉得自己前所未有的软弱,那些事,那些话,不愿提起,又不想否认,自己一直深埋着压抑着的心潮,全都重新奔涌起来……一点酸,一点痛,一点涩,一点苦,在他胸中交织翻腾。
“她……她嫁人了。”
妃红许久没说话,哗啦,哗啦,慢慢绞着面巾。水声停了,衣衫微响,妃红爬上炕来,伏到天青身边,轻轻捧起他的脸,用热面巾擦着,柔声说:
“天青,你师妹没能跟你,不怪她,更不怪你,只是她没福气。你这样的好男人,值得世上最好的女人。”
她的眼波在月光中闪闪发亮,盯住天青眼睛,手里热气腾腾的面巾,像一下下温柔的抚摸,轻轻擦过他的额,他的眉,他的眼,他的脸颊,他的鼻梁,他的嘴唇,他的下巴……
天青的视线自窗外转回来,直视着她。他从未这样直接地与她面面相觑,此刻,近身咫尺,呼吸相闻,他没有推拒,没有挣扎,只是这样静静看着她,眼中那从未有过的激荡神情,身上强烈的男子气息,让妃红心中狂跳,满腔热浪无法遏制,霎时间全身都有些颤抖。多少日的情怀暗涌,千百里的生死奔波,等待的就是这一刻呀,她缓缓凑身上去,一只手轻抚他的脸,另一只手,将那条面巾,顺着脖颈,擦向他敞开的衣襟之下,赤裸的胸膛……
天青仿佛大梦初醒一般,一把抓住妃红的手腕。抓得这样突然,这样紧,疼得她倒吸一口气,手中面巾掉在炕上。
“天青……”妃红轻轻低下头,咬住了嘴唇,“你嫌弃我?”
“不是……”
妃红的睫毛扑闪一下,“我不是最好的女人,我没有你的师妹好……”她抬起眼帘望住天青,“我知道我配不上你,我就是个江湖女,可是……”两颗泪珠自她眼中涌出,“我喜欢你,我爱你,我心里……有你!”
天青静静凝视着她,停了一会儿,松开手,拾起面巾,为她擦去腮边的泪。妃红仰起脸来,泪花中带着一点妩媚的笑意,深深望进他眼睛里去:
“……天青,我一搭班就喜欢上你了,你是我从没遇着过的好人,和你在一起,比什么都让人安心。我们都是同命人,我会对你好,天青,你答应我,好不好?我们一起回去,一起唱戏,一起好好过日子,我给你生大胖小子……”
她的声音,越来越低,越来越细,和整个人一样,柔若无骨,温软如丝。她顺着他的手臂,水波一样滑进他的怀里,紧紧抱住他的身子,将脸贴上他健硕的胸膛。她听得到一声声的心跳,疾烈、刚猛,直击她的耳鼓,烧燃她的心,她热切地仰起头,吻上他的脖颈,唇间温柔的呼吸,轻轻荡漾在他的耳畔:
“天青,你要了我吧!”
天青仿佛置身于一个熊熊燃烧的火炉,里外四周,全是一片茫茫烈焰,烧得他唇焦口燥,目眩神迷。眼前的妃红,那一向以来娇艳迫人得令他都不敢面对的筱师姐,此刻带着满腔情热投身在他怀抱,隔着薄薄的贴身小衣,他清楚感受到那火热的躯体,柔软的肌肤,曲线凹凸的前胸紧紧贴在他身上,温润的唇吻雨点般落在他颈间……天涯孤客,生死苦旅,她陪了他这一路风霜,千依百顺宛转逢迎,甚至明知道他心中另有所属,仍然不管不顾地表白情意:
“天青,你要了我吧!”
有那么一瞬间,他真的控制不住自己了,一个男人的本能,让他想抱住她,接受她,和她一起投身到那暴风烈火中去……但是这纷乱烈焰中,总有一个血淋淋的伤口闪动,那是他心头,始终不能痊愈的一记创痕,一个空茫茫无法弥补的黑洞,他的喜怒哀乐,没法子跳过它,人生前路,永不能逾越它……眼前再多情爱,也替代不了记忆中那个明朗的笑脸,时时刻刻,都有那双清澈的黑眼睛浮现在他面前,脆亮的声音,至今回荡在他耳畔:
“天青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