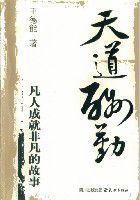关于黄河流域,尤其是黄土高原的水土保持,黄万里从来都持积极态度,但他所依据的是实事求是的分析和论证,他认为“水土保持对于上游地区农业完全必要,也可能大体上做到。但,因黄土层在风沙堆积的过程中陆续降雨被形成了许多长垂直孔洞,可以高达几十米。一遇大雨,这些孔洞同时被雨水充满。临近河岸的黄土层一片一片地剥落下来,形成直壁。所以平面或斜面上的表土及溪沟水可以保持,但大片黄土仍会落入河道里。这是地质部地下水二队的考察结果,有报告可查知”。黄万里论证道:“当水流经过河床,一定会挟带一定量的泥沙同行。许多实验都证实输沙率0略和流率0的平方成正比:
除非流尽河干,即0=0,河中必有泥流,即00。故凡河床质为泥沙的河道都非清水的河流,泥沙一定会输向下游。”对于国人普遍关注的黄河断流,黄万里一样苦心焦虑。他在同笔者交谈时说:“这是民族的灾难!这是大灾难的预警!”关于断流的原因,黄万里认为从1962年起,上游修了几个大水库,仅龙羊峡库容量就达200多亿立方米,中下游水库几十个,水土保持工程几十个,它们的蓄水量和灌溉用水量将各用去300多亿立方米的水,黄河原来的平均年流量580亿立方米,当然自1972年起会全部用光而造成断流。懂得黄河流域内水量是这样分布的,则就该自1962年开始修建上游水库时,加引青藏高原丰富的西南水源。再引雅鲁藏布江水而怒江而澜沧江而金沙江而雅砻江而黄河龙羊峡而河口镇、潼关,这就是黄万里精心构想的西水人河。若平均引1000米7秒,每年即为315亿立方米的水,黄河流域全线将得到充分水流,从1962年起兴工,1972年就会有显著成绩。如是,黄河决无断流之灾《(黄河的重大问题及其对策)的意见》,黄万里,1999年10月13日黄万里如此钟情的西水东调、黄河分流之后,是一种什么景象呢?黄万里深情款款地向往道:“人们必然能建成精致的分流闸和分流渠道(“我们为什么只是筑大坝、修水库呢?”笔者插话),这是黄河分流策的根据。在一段时期分流淤灌后,黄河槽身自然峻深,再无须加高堤防来防洪了,于是河治。人们欢迎更多的泥沙下来(“更多的泥沙下来这样水土保持工作应改由农业部说好不好?”“那就下来多少算多少吧!”),领导,下游会自然地淤灌增肥,并造出更多的耕地,人们将额手称道:黄河乃是世界第一大利河!”黄万里年事已高,他在70岁到90岁之间曾经动过几次切癌手术,分别是结肠癌、胃癌、前列腺癌,另有胆结石、淋巴疾病。他说:“我有福气,我有夫人的照顾,每次进手术室之前,夫人目送我,我知道我还会活着出来!”黄万里不知老之将至吗?不,他知道。1976年,有一颗牙齿离他而去,那种离体感觉作为生命的一部分,多少有些苍凉地告诉他,他老了。时年65岁,作《牙落惊老》调寄渔家傲:
牙落始惊身已老,形衰不役心犹矫。
欲治黄河赍志早,空负抱,制鳌有策知音渺。
王景千年擅工巧,长才自古能伸少。
细考其谋何所造,行洼道,分流回注於沙皎。
黄万里一如既往,只是把生命的紧迫感,在他70岁至90岁的多病岁月、垂暮之年里,完全无私地献给了中国的江河事业。就在笔者采访他时,他几次老泪横流重复着说:“他们没有听我一句话!”黄万里的可贵正是在没有听他一句话的近半个世纪的漫长岁月里,继续说着自己该说的话。1979年治黄大会后,他又重写了《论分流淤灌策治理黄河》,1985年6月清华大学印行。文中指明,分流淤灌是治理黄河的唯一可行之法,全文以严密的科学方法逐节论证推理、节节关连、渐次深人,最后归于分流淤灌的唯一性和可行性。黄万里并申明:只要谁能发现其中一条悖理,则全策皆非。黄万里这样做,除了他一贯的严谨以外另有深意:向全国水利学者挑战,分题探讨,集中辩论,以期在科学与民主的氛围中明确治河方略而利国利民。可惜的是“无人应战,只有来函赞许的人”(《治河咏怀》怎么办呢?黄万里还是只能上书:“于是我于1985年8月8日呈文国务院总理,要求给我90分钟时间向总理和当事诸公解说分流治黄是唯一可行的策略,同时也解决了河北缺水和部分黄淮海平原经济发展的问题,并且指明:东线南水北调方案不可行,引黄河水济青岛不可行,及建云贵川湘鄂赣各省电站。结果都发给了下层机构参考,黄河水利委员会让我报告了半天。另外,发交科学院研究这个问题,这一研究至少五年,而若按我的建议分流治黄并淤灌淮海平原,每年将获益几十亿元。只是这样,没法进行南水北调了,那怎么可以呢?显然,这个问题落到了王顾左右而言它,的结局,于是笔者有赴美讲学之行。”从此之后,黄万里便在美国做寓公了吗?非也,他怎么离得开江河呢?他回国了,继续上书,杳无音信,再上书,直至心颤手颤,反反复复进医院切除癌肿之后,一息尚存仍然大声疾呼,河啊河,水啊水!一个人的命运若与流水相缠结,那就只有渗透和浸泡其中而不可能分离了。被践踏的梦想将要成为种子,而迟迟未到的光荣却已寄托给水利万物而不争了。
仅仅是笔者采访中先后阅读过的黄万里的论文及上书材料就有:
《长江三峡高规永不可修的简释》续1992年9月,《关于长江三峡修建高坝可行性问题》1997年6月,《治河方略概说》2000年4月,《(黄河的重大问题及其对策)的意见》1999年10月13日,《对于治理黄河与长江的意见》并附六册有关分流治水意见及媒体文章呈国务院2000年4月,《对于黄委(黄河治理开发纲要)的意见》1996年6月,《论江河淮海综合治理》1999年4月,《治水吟草》1991年6月黄万里送我的一册《治水吟草》,是先生80岁时自选自编自序自己装订成册的诗词集,封面上是他用颤抖的手写下的颤抖的题字:徐刚老弟指正。其中诗词从1957年的《百花齐放颂》,到1991年《题与施嘉炀花前合影》近100首,文采风流、襟抱磊落,读者如我每每感从中。其间最可寻味的是诗人黄万里的人格魅力,他的晡与泪及携太太白头偕老而“容伫望,鹊桥来路,一刻有空闲,便思量千度”的缠绵深情。集中另有一首题为:“送万里火葬,代内作,甲寅腊月。”读题时甚为惊讶,及至见到小跋才恍然大悟。1974年冬至,黄万里63岁,时客三门峡,当是一边劳动改造一边调查研究时。想不到“甲寅冬至妻、子异地同日梦我遇祸,同日来信”,黄万里“因念陶渊明有自挽之诗”,一时兴起便代妻子作此诗。调寄兰陵王,“人生如寄如戏,聊以哭泣博嘻笑云耳。”其中有:“送卿去,卿去我归何处?”“卿去,谁最苦?念庭犬丧家、梁燕无主,归来触物增凄楚……痴孙犹问卿何顾?倚户斜阳暮。卿去,尚还否?叹繁华尘世,留似朝露……”每一次去黄宅采访,黄太太都会沏好香茶,得知我曾在巴黎流寓三载后,便又加上一杯咖啡及小点心。我叫她“师母”,她耳背有时听得见有时听不见。她总是轻轻地走进客厅,给黄万里先生准备好药片,有好几种药,并端水看他服下,然后轻轻离去。黄万里总是笑眯眯地看着她的背影,有阳光从窗户里洒在他的脸上,洋溢着幸福与满足。
一个没有成功也没有倒下的男人身后,总有一个女人站着,信夫?因而,无望的等待有时是属于两个人的。
笔者最后一次采访黄万里是2001年3月12日上午。
他不允,“客为上”。沉重地说先生要我坐右边的沙发,说“右手是上座”,我坚辞。
完自己的生平,他长叹一声:“梦也会老啊?”但,那梦还在。
黄万里还是说黄河,黄河河道有没有相对稳定的时候?有,以《水经》和《水经注》的记载判断,魏晋南北朝的河道相对稳定。为什么西汉时期黄河多次改道,而在东汉以后至魏晋南北朝下延隋唐,黄河能有难得的长期安流,史籍上甚至出现了千年无患论?黄万里认为,此一历史时期的黄河现象发人深思。
何来安流?功归其谁?先生介绍说,从古到今影响最大的一种意见认为,应归功于王景治河有方。王景治河成功的关键在于“十里立一水门”,明代徐有贞,清代魏源、刘鹗,近人李仪祉,西人李约瑟均持此见。
王景,字仲通。永平十二年(公元69年)夏天,王景和王吴共同主持治河,“筑堤自荥阳东至千乘海口”,以数十万之众修黄河大堤千余里,还整治了汴渠渠道,新建了汴渠闸门,同时“商度地势,凿山阜、破砥碛、直截沟涧,防遏冲要、疏决壅积”(《后汉书王景传》全部工程到次年四月结束,治河工程约一年。由于史料缺失,对王景“十里立一水门”之说有各种解释,总的来说一年之内把黄河下游一千里长堤的遥、缕四道土堤和许多水门都修造完成,是过于理想化了。谭其骧先生则认为,东汉末年黄巾起义以后,北方大批游牧民族南下,汉民族势力逐步后退,以农为本的汉族人口的急剧衰退和以畜牧为生的羌胡人口的迅速增长,反映在土地利用上,当然是耕地的相应减缩,牧场的相应扩展。黄河中游土地利用情况的这一改变,结果就使下游的洪水量和泥沙量也大为减少。因而,谭其骧先生认为此乃“东汉一代”和“魏晋十六国”时,“黄河之所以能够安流无事的真正原因所在”(《学术月刊》1962年第二期八黄万里认为王景治河功不可没,斯时河道的人海距离短,比降陡,河水流速与输沙能力大。加之河南岸有泰山余脉阻挡,北面则是溢高之后的秦汉故道,河水流经处较为低洼,使下游河道相对稳定。而东汉以降直到魏晋南北朝时期,黄河下游可以分流、泄水,削减洪峰的分支仍有汴水、济水、襥水、漯水等不少分支,及水泽湖泊与旧的河道。它们的作用实际上就是分流、排沙。可是,论家涉及较少的社会原因,其实更值得后人从中钩沉细末,看看能不能发微知著?东汉末年以后,黄河下游刀兵不断长期战乱,当时社会动荡不宁,政权频繁更迭,人口大量死亡。可以推想的是当洪水来临,在若干区段内呈现的是任其自由泛滥的状态,黄河泥沙不是仅仅淤积在河槽里,而是流淤在更广泛的地区,因而延缓了河床的抬升。元人余阙曾论及东汉以后的河道:“河至德、棣,支分为八。河北已绝之渎,淫潦时尽归沮洳,同趋人海。”(《河渠纪闻》)清人康基田追溯魏晋寻人问沙时也说:“平原以北,大河故道犹存,地区洼下,皆沮洳之区。至大水之年,经流虽归千乘,而溢出之水散漫于冀、定数州。”这就是黄河在历史上曾经安流的近1000年间,主要因为社会原因在无为而治时,很有可能出现过的分流排沙,漫溢安澜。
“哪有比历史这位先生更高明的呢?”黄万里说。
“50年来,我们的水利思路始终不变:筑高坝、修大库。劳民伤财的教训从不记取,黄河无罪,罪过在人!”先生接着又是一声长叹,“我老了,愿后来者思之!慎之!行之!”有最新消息说:“黄河全流域符合一、二类水质标准的河段仅有8,属于三、四、五类水质标准的高达91,整个黄河流域的污水处理率也是8。”(《南方周末》2002年)
我们到底富了还是穷了?我们到底要钱还是要命?黄河啊!母亲河!什么样的慨叹能留得住时光之箭?
什么样的人生可以不用成功和失败来衡量?
想起了罗素的自白:“三种简单但又极为强烈的激情支配着我的一生:对爱的渴望、对知识的追求和对人类苦难的不堪忍受的悲哀。”从黄万里先生的寓所回到我的通州农舍,黄河与老去的梦以及江河大坝,大坝上的中国交织在思绪中,一时无从下笔,只是反反复复地在灯下寻找着一个步履瞒跚的背影,黄河万里独行客,涛声依旧,长江。可是在长江源区的唐古拉山,姜古迪如冰川,以及苍茫的荒野草甸上,时光仿佛是冻结的、静止的。神圣无需喧哗,沉默包容一切。圣洁到冰冷,庄严到沉重,当冰川融水点点滴滴淌下时,一条大江诞生了。初始流出是如此细小,接纳百川的是从江源开始的宽阔而绵长的襟抱,然后才是涛声引领之下的曲折与落差。于是沉雄博大、不畏险阻、创生万物的神奇,便澎湃在中华民族的血脉中了,亘久的古老,亘久的年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