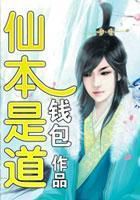话说嘉兴府客店内,有人闹事,揪着掌柜的乱打。圣天子赶将那人劝开,问他的姓名。那人道:“在下是安徽人氏,姓鲍名龙,不知二位尊姓大名?何方人氏?”天子道:“某乃姓高,名天赐。这是某的继子,姓周,名日青,直隶北京人氏。阁下既是安徽,到此有何贵干?”鲍龙道:“在下本在安徽军营内当个什长,只因有个表弟居住此地,广有家财。因念军营太苦,欲想投奔到此,筹办盘川,想往广东另谋进身。不料表弟被人攀害,坐入县牢。家中皆女眷,不便居住,是以住在这店内。哪知这掌柜与小二如此欺人。”天子见他出话豪爽,说道:
“他们小人类多如此,足下不必与他较量。且请到某房中,聊饮二杯。”说着,就将鲍龙邀入自己房内,复叫小二暖了一壶酒来,将嘉兴肉多切两盘。小二此时被一闹,也无法想,只得又切了一大盘嘉兴肉,放在桌上,与他三人饮酒。
天子见鲍龙毫不推辞,举杯就饮。你斟我酌,早将一壶酒饮完,复又喊添酒。天子问道:“鲍兄说令表弟为人攀害,但不知究为何事,何妨说明?如可援手,也好大家设法。四海之内皆兄弟也,岂可坐视其害?”鲍龙道:“高兄有所不知。舍表弟姓郭,双名礼文,乃是贸易之人,就在这府衙前大牌坊口开个钱米铺。他是个生意人,自然各事省俭。店中有个王怀,乃是多年的伙伴,所有账目全在他手里。每年到年终,除薪水外,表弟必多送他数十千文,以作酬劳。在表弟意见已是加丰,哪知这王怀还说太少。明地里不好与他讲论,暗地就在账上东扯西欠,不到半年工夫,净欠八百数十千。这日,被我表弟查出。其初因他是旧友,或者一时讹错,也未可知,不过问他一声,请他弥补。不料他知已露了马脚,就把心偏过来,嘴里答应照赔,到了一月之后,又空二三百元。我表弟见他如此,知他有意作弊,就将他生意辞去。他不说自己对不起东家,反因此怀恨。却好隔壁有座小客店,不知那日无意落下火种,到了二更以后,忽然火着起来,顷刻间,将客店房屋烧了干净。当时,表弟等人从梦中惊醒,自己店面还保护不及,哪里还有工夫去救人家呢。这小客店的店东不怪他不谨慎,反说我表弟见火不救,次日带领妻小到店中吵闹。表弟本来懦弱,见他如此闹法,也是出于无奈,从来只有个宽让窄的,因道:‘你不必这样胡闹,我这里送你二十两银子,你到别处租些房屋,再做生意去罢。’这小客店的人,见有了钱,也无话说。不知怎样,被这王怀知道,他就去寻小客店内店主的老子,说:‘郭礼文有这样家财,你不讹诈他去讹诈谁?二十两银子只能算个零数,我这里有个好讼师,请他代你做张状词,包管到县里一告就准,不得一千,就得八百。’那老头子是个穷人,被他一番唆使,就答应照办。王怀当时寻了这里一个出名讼棍,叫汤必中,却是文教中的败类。说明得了钱财,三人瓜分,就捏词嫁祸,写了一张状词,说我表弟放火害人,恃财为恶。到了告期,那小客店的老头子就去投告。其初嘉兴县吴太爷还清楚,看了一遍,就摔了下来,说:‘郭礼文既然有钱,断不肯做这事,显见有意诬害。’那知汤必忠又做了第三张状词,说:‘郭礼文因自己有钱,怕小客店设在间壁,人类不齐,恐怕偷窃他店中物件,故此用毒计,放火烧了。不然,何以郭礼文情虚,肯给纹银二十两,令他迁让?’这个禀帖告进去,那些差役人等,皆知郭礼文有钱,在县官面前加意进了些谗言,说得县官批准提讯。到了提讯的这日,我表弟胆又小,见公堂上那等威武,格外说不出话来。县官因此疑惑,竟致弄假成真,将他收入监牢,要遵律治罪。在下前月到此,因他家别天亲友料理这事,故尔具了一禀,想代他翻案。奈至今日,还未批出。你二公想想,这不是不白之冤么?在下不是碍着表弟在监内,怕事情闹大,更属难办,早将这王怀打死。天下哪有这样坏心术的人!”天子听他说了这番话,又见他英雄纠纠,倒是个热肠汉子,说道:“老兄不必焦虑,明日等某到县里,代你表弟伸冤。我看你如此仗义,断不是个无能之辈。从前曾习过武艺,有何本领,何妨略示一二。”鲍龙道:“不怕二位见笑,我鲍龙论武艺两字,还不在人下。只因性情执拗,不肯卑屈于人,所以在军营一向仍是当个什长。那些武艺平常的,会巴结会奉承,反在我之上。就是一层,到了临阵交锋时节,就显分高下了。”天子听说,也是代他负气,道:“我道京外文官是这等气岸,那知武营中也是如此,岂不可恼?我看后面有一方空地,现在无事,何不略使拳棒,以消永夜?某虽不甚娴熟,也还略知一二。”鲍龙谈得投机,也不推辞。
三人就出了房门,来至院落,将袖子卷起,先使了一起腿,然后开了个门户,依着那醉八仙的架势,一路打去。在先还看见身体手脚,到了随后的时节,哪里见有人影,如同黑团子一般,只见上下乱滚,吁吁风响。天子此时赞不绝口,道:“有此长才,困于下位,真令英雄无用武之地了。”一路打完毕了,将身子望上一纵,复行向地下一落,手脚归了原处,神色一点不变,说道:“见笑大方。”天子道:“有此手段,已是可敬,岂有见笑之理?但不知老兄愿进京么?”鲍龙道:“怎么不愿?只因无门可投,故尔不作此想。若早有人荐引,也等不及今日了。”天子道:“既如此说,明日先将你表弟事理清。高某与军机大臣陈宏谋是师生,将你托他位置,断无不行之理,大小落个官职,较此似觉强多了。”鲍龙大喜道:“若得你老提拔,那就感恩不尽了。”三人复由外面进来,谈论了一会,然后各回房安歇。一夜无话。
次日早间,天子起来,梳洗已毕,先到鲍龙房内,见他已经出去,心下想道:“我同他约定一齐到嘉兴县去,何故他一人先走了?”只得复又出来,回到自己房中。日青已叫人将点心做好。两人用毕,见鲍龙已走进来,天子问道:“方才前去奉访,见老兄已不在哪里,如此绝早,到何处公干?”鲍龙道:“昨因你老说,同在下今日赴县里结这事,惟恐衙门内须使费用,故到舍亲处,将你老的话说与家姑母、表弟媳知道。他们感激万分,嘱在下先行叩谢,俟表弟出狱后,再行前来趋叩。”天子道:“说哪里话来,大丈夫在世,当以救困扶危为是。况此又为地方除害,一举两得,有何不可?我们就在此同去罢。”鲍龙答应。
三人一齐出了客寓,行不多远,到了嘉兴县衙门,只见头门外挂着一扇牌,是“公出”二字,因向鲍龙说道:“来得不巧。县官出门去了,也不知上省,也不知是因案下乡勘验。鲍兄何不打听打听?”鲍龙道:“既是县官公出,此刻就便进去,也是无用,还是让我打听明白,究竟到哪里去了,几时回来。”说毕,请天子、日青两人在外面稍等,他便自己寻着那承行的书办,问道:“县太爷往哪里去了?”书办道:“进省公干。昨日奉到抚台公事,调署钱塘首县,因此地交代难办,暂时不能离任,所以进省,将这话回明上宪。”鲍龙道:“钱塘县难道没有县官么?何以要调他前去?”那书办道:“你还不知道呢。现在当今皇上南巡,见有贪官污吏,轻则革职,重则治罪。这钱塘县因是断案糊涂,却值圣上在杭游玩,下了旨意,将钱塘县革职,着抚台另委干员署理。我们这位太爷,声名还好,所以将他调署首县。大约两三日后,也就可回来了。”鲍龙打听清楚,转身出来,详细说了一遍。天子知是龚温如接着圣旨,依旨照办。当时也未提起,说道:“我们只好再等一两天,等县官回来,再来便了。但我在京,闻此处有座苏小小坟在这城内,不知鲍兄可曾去过么?”鲍龙道:“晓却晓得,并非专为游玩而去。只因在下由本籍到此,曾从那坟前经过,故尔知道。二位如欲去游玩,鲍某引路便了。”天子听了大喜,就约他同去游玩,鲍龙答应。
三人信步而来,约有三四里光景,已到前面。只见远远的一派树木将坟墓绕住,坟前一块石碑,石碑上写“苏小小墓”四字。天子向日青说道:“可见人生无论男女、贫贱、富贵,总要立志,然后那忠孝节义上才可各尽其道。你看苏小小不过当年一个名妓,一朝立志,便千古流传,迄今成为佳话。我看那些贪财爱命的人,只顾目前快活,不问后来的声名,被人恨,被人骂,到了听不见的时节,遗臭万年,岂不被这妓女所笑?”鲍龙在旁说道:“你老所见不差。只是当今之世,被苏小小笑的人多着呢。但为妓女,不如他也就罢了。最恨那一班须眉男子、在位官员,也学那妾妇之道,逢迎谄媚,以博上宪欢悦,岂不为苏小小羞死?”两人正在坟前谈论,早又闹出一件事来。不知后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