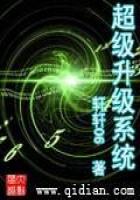自从戊戌政变,光绪帝被幽禁在瀛台以来,这还是第一次被慈禧召来,参加议决军国大事。这个三十岁刚出头的皇帝,比前几年已经变得更加苍白和清瘦了。他神情憔悴,面如死灰。到了仪鸾殿外,他首先下了龙舆,用那恍惚忧郁的眼神,望了望槛内外跪伏的大臣,便默默地跪在殿前的丹墀上,和诸王大臣们一道恭迎慈禧的圣驾。
又过了一会儿,慈禧才到来了。她的龙凤辇由四名清秀的年轻太监抬着,一直抬到仪鸾殿正中殿门前才落定。她微微扬起头,板着面孔,两眼平视,看也不看跪在旁边的光绪帝,便由李莲英、崔玉桂两位总管扶掖着,从跪满一地的王公大臣们面前缓缓穿过,登上了大殿正中的宝座。
慈禧升坐之后,光绪才站起身来。他全身微微地颤抖着,就像是一株风中的羽茅草,迈着沉重的步伐,走进殿门,先向慈禧请了安,然后坐在慈禧右首的龙座上,垂下眼帘,极力用一种漠然的表情,掩饰着他内心深处的痛苦、恐惧和不安。
慈禧坐定后,接受了群臣的朝拜,便厉声说道:“近接有关臣僚禀奏,英夷无礼,竟敢图谋用兵舰运兵来犯,妄图胁我归政;法夷领事也公然发来通牒,索我大沽炮台。如此狂悖已极,我朝断难宽容!我意已决,如各国使馆再不撤走,立即宣战,着武卫军、虎神营、神机营,配合十万义和拳民,围攻使馆,讨伐诸夷。汝等大臣务应同心效力,以报答朝廷二百余年深恩厚泽和覆戴之德。”说完,又问光绪:“皇上意见如何?”
光绪帝沉默了半晌,才颤声答道:“外臣所奏,不知根据实在否?外国如有无礼要求,当然不宜迁就,可着总理大臣与各国使节耐心交涉,据理力争,自然可以公正解决。惟使馆不能攻,乱民不足恃,战衅不可启,此事关系至大,还望老佛爷圣裁。”
慈禧听了,脸色阴沉,甚不快意;又问庆王奕劻、大学士荣禄等有何启奏。奕劻、荣禄见慈禧神情严重,面有愠色,也都低下头,不敢浪对。
这时,突然听到槛外一声高呼:“臣袁昶有话上奏!”声震屋瓦,惊得众大臣都变了脸色。接着,殿门外便走进一位大臣来,面色赤黑,体格胖伟,他便是太常寺卿袁昶。他进殿跪拜后,就仰头大声奏道:“各国增兵前来,确是事实,但都是为了保护各国使臣和侨民之安全,并未闻有胁迫归政之意。只要我朝能制止暴乱,持平调处教民纠纷,使各国使节、侨民之身家性命确有保障,则各国便失去了派兵前来的借口,然后再从容与各国交涉,何愁夷兵不退?自古两国交兵不斩来使;毁法乱民,不可纵容。事关大局,还望老佛爷和皇上明察。”
端王载漪跪在慈禧近旁。他是新立皇储大阿哥的亲父,一心只想早日推倒光绪,扶他儿子登上皇帝的宝座。如今挡在他前进道路上的最大障碍,就是那些支持光绪的洋人。他恨透了一切洋人和各国的使节。义和团激烈仇洋排外的行动使他心花怒放,如获至宝。因此,他是诸王大臣中最支持义和团的一个。他一心想利用这股号称数十万的拳民来杀尽洋人,赶走各国使节,同时也压倒荣禄手中的武卫军,作为拥戴他儿子爬上皇座的一股巨大的力量。刚才光绪帝说“乱民不足恃”时,他就已经忍不住了,现在又听到袁昶的一番议论,更加勃然大怒,手指袁昶怒喝道:“汝等这些话全是汉奸言论。义和团扶清灭洋,都是忠勇义民,汝等竟要剿除,真是汉奸卖国失人心第一法!”
袁昶也不畏惧,凛然反驳道:“忠心为国,何谓汉奸?杀人放火何谓义民?难道硬要纵容乱民为少数人之私利火中取栗,玩火自焚,祸国殃民,给国家带来大难,使百姓陷身水火,才是爱国么?”
载漪气得跳起身来,指着袁昶喝骂道:“袁昶通夷,如此二毛子,还不推出去斩了!”
一时皇上变色,殿中大乱,庆王奕劻忙上前劝说,用自己的身体护住袁昶,才让他退出殿外。
慈禧敲了敲御座,厉声道:“汝等不必多言了。此次战衅,全由夷人挑起。我意已决,可着许景澄即持战表往谕各国使臣,限他们于二十四时之内,一律出京;由荣禄派兵护送,不许伤害一人;否则,如拒不出京,触怒义民,动起手来,可就怪不得朝廷了。”
许景澄心中有话,不敢明奏,又不敢不接战表,正在犹豫,慈禧又敲着桌子,催促道:“许景澄还不快去!”
许景澄膝行上前,领过了战表,满面愁容,正欲起身出殿,光绪帝见事急燃眉,也顾不得礼仪了,急忙走下御座,拉住许景澄的手,颤声说道:“向各国宣战,攻打使馆,此事史无先例,关系极大,汝且慢走,还需妥善商议才好!”
慈禧见了,更加拍着御座扶手,大声喝斥道:“皇帝快放手,莫误了大事!”
光绪见奕劻、荣禄等都装聋作哑,噤若寒蝉;载漪、载勋等又凶横跋扈,怒目相视;许景澄、袁昶等则泪流满面,束手无策;全体王公大臣都是眼观鼻、鼻观心,屏息吞声,不敢置一词。他知道大势如此,已经无法阻拦了,只得放开许景澄的手,默默地回到御座上去,从此直到整个朝仪结束,都再没有讲一句话儿。
接着,慈禧又命庄亲王载勋、大学士刚毅提督义和团;下诏褒奖义和团为义民,拨内帑银十万两,月赐太仓粟千斛,在虎坊桥湖广会馆发放,供给各路拳团;发给枪支,准备攻打各国使馆。
第二天午后,董福祥的武卫后军,载漪统领的虎神营和神机营旗兵,加上载勋、刚毅提督的义和拳勇号称十万之众,便开始向东交民巷一带的各国使馆,发起了总攻。
刚毅与赵舒翘亲自坐在正阳门城头上饮酒督战。天开始黑下来了。阴暗的天空中,闪烁着一片血样的红光。听到东交民巷一带四面枪声如麻,杀声动地,刚毅面有得色,举起酒杯,对赵舒翘道:“大司寇,此番老佛爷圣意已定,加上天助神团,破使馆,灭洋人,从此天下当太平矣!”
赵舒翘原是刚毅一手提拔之人,如今身为刑部尚书,官居一品,全靠刚毅提携,所以他遇事总是谄事刚毅。这次,他同刚毅到涿州去视察,就亲眼看到烧杀动乱的情景。他明知少数头目,以邪术骗人,并不足恃,但是,当他见刚毅十分信重那些拳民时,也就马上跟着改变了态度,违心附和,回朝后也盛赞义和拳的忠勇。此刻,他见刚毅沾沾自喜,忙站起身来,举杯祝酒道:“自康有为等倡乱悖逆以来,喜事之徒,云合而响应,国事日乱。幸我公砥柱中流,起而芟夷之,朝廷始转危为安。今夷人猖獗,逼我神京,我公又首保义民,入京灭洋。如非太后圣明,我公大德高才,何克臻此?古有社稷之臣,如公可谓无愧矣!”
刚毅听了,欣然大喜,举杯一饮而尽,一面伸手拍着赵舒翘肥厚的肩膀,仰头大笑道:“展如知我!展如知我!”
这时,使馆附近,枪声渐稀。刚毅站起身来,向东交民巷那边眺望,只见无数拳勇正在溃退下来,准备吃晚饭。他把酒杯一丢,带了几个亲兵戈什,下楼去查看。下了城楼,迎面就碰见了义和团的总头领、大师兄张德成。刚毅指着城门洞里那些死伤的义和拳民,问张德成道:“公等在涿州时,皆言如何神妙,今日为何不见灵验,死伤这些弟兄?”
张德成抹了一把额上的汗水,拍拍胸脯,笑道:“相爷不知道,这哪里是死伤,这些兄弟都是太劳累了,睡着了,等一下,待我们作起法来,取出枪子,念动咒语,呼其小名,他们就都会醒来的。”
刚毅将信将疑,走到一个僵卧的拳民身旁。那拳民不过二十来岁,胸口有两处枪伤,大量的鲜血已经染红了他胸前系着的绘有八卦的兜肚。刚毅用足尖轻轻触动了一下,那人全身都已僵硬,显然已经死去多时。刚毅怀疑地望了望张德成。张德成脸色一变,皱了皱眉头,对他身旁两个年轻的拳勇说道:“搜一搜他的口袋!”
两个年轻的拳勇,将那尸体翻过来翻过去搬动了一番,搜出了几样物件:一枚赤金戒指和一包洋人们吸用的吕宋雪茄。
张德成便冷笑一声,转向刚毅道:“这就难怪了。我们义和拳是替天行道的神助拳,教规本是极严的。像这样或抢人财物,或奸淫妇女,或使用洋货,犯了天条的人,法术哪能保护他?他们丢了性命也就是罪有应得,自讨的了。”说着,他看了看刚毅的脸色,又哑然笑道:“相爷不必挂心,尽管回府去安歇。等到今夜子时三刻,一阳初转之时,我等请来关圣帝君、纯阳老祖诸神下界,再调来金钟罩、红灯照等,管教他洋人尽灭,明日就可大获全胜了。”
刚毅听了,也增强了信心,又好言慰勉了一番,才和赵舒翘、张德成等告别,坐了轿子,带了亲兵戈什,径自转回府去。
这时已是起更天气,夜色沉沉。刚毅坐在轿内,一路行来,但见两旁街道屋宇,许多都被烧毁,断瓦颓垣,十分凄惨。有些幸免于难的店铺住房,也都门窗紧闭,挂着红巾,贴着符箓,全无一点灯光,好像无人居住的死宅一般。街上没有行人,只有一队队武卫军、虎神营旗兵喧哗过市,杀气腾腾,正忙着趁火打劫,做一些杀人放火,打家劫舍的勾当;还有一群群义和团民,捧香持烛,沿街传呼,向东南方跪拜,敬请尊神。
回到府邸,进了大门,早有家人惊慌失措地前来报告说,拳民们正捉了三少爷和彩凤在大堂上拜坛请神,审判二毛子,夫人太太们都在后堂着急,只盼老爷快快回来解救。
刚毅听了,心中也有几分慌张。他下了轿,带了众亲兵戈什,转入大堂看时,只见大堂上灯火辉煌,香烟弥漫,堂上堂下果然挤满了百余名拳勇,全都是十六七岁至二十岁上下的后生子,头上都缠着黄布头巾,胸前都系着绘有八卦和太极图的黄布兜肚,手中拿着大刀、长矛、三叉、九子鞭等各种兵器,一个个横眉怒目,凶神一般。堂前插着一面巨大的三角形犬牙镶边的杏黄旗,上面写着“奉旨义和神团”六个墨黑的大字。左右又各有一面长方形的旗幡,分别写着“扶清灭洋”和“替天行道”等字样。神坛上供着关圣帝君、洪钧老祖、骊山老母以及杨戬、哪吒、孙悟空、樊梨花、穆桂英等各种神位。一位年约四十余岁,紫酱脸,满面生着肉疙瘩的山东大汉——大师兄斜坐在神坛旁的太师椅上,正在审讯他的儿子志敬和彩凤。这大师兄神色严厉,明明看见刚毅带着亲兵进来,也不起身,不理不睬,好像没有看见似的,继续进行他的审问。志敬、彩凤早已吓得浑身颤抖,披头散发,衣冠凌乱,伏在地上,不敢仰视。
刚毅在堂前站立了一会儿。他虽然心中恼怒,却又不敢发作,想了一想,只好把亲兵们留在堂前,只身步上堂去,一直走到神坛前,向那大师兄拱手道:“大师兄请了!”
那大师兄也不答礼,仍旧端坐不动,垂下眼皮,喝道:“祖师爷神灵在上,刚毅速跪!”
刚毅本是大学士、军机大臣,威威赫赫,一品当朝的相国,平时在下属臣民面前是何等的威风!可是,今天在他自己笃信的神教面前,却不得不恭恭敬敬地屈服了。他正了正冠服,拈了香,焚了表,先在神坛前毕恭毕敬地拜了几拜,那大师兄才起身让坐道:“相爷在上,小人失敬了。只因令郎十分无礼,竟敢在神坛后调戏小夫人,亵渎神灵,被弟兄们捉住了,还从他身上搜出不少洋人的妖物。因此,众家兄弟十分气恼,正在开坛审问,相爷来了正好,请相爷一同处理。”
刚毅听了,不禁老脸羞红,又气又恨,恨的是志敬、彩凤这两个孽障,屡教不改,又背着他干出了这样的丑事;气的是这些义和团太不讲情面了,抓住这件丑事,如此张扬,实在有碍于他的官威。但他害怕众拳勇,又不敢稍露不满之色,只好敷衍道:“小子无礼,亵渎神灵,理当重惩,但看在老夫敬神重团的份上,还望大师兄和众位兄弟,祝告上苍,请求神赦,今后保证加强教诲,决不令彼等重犯。”说着,又回头吩咐家人,赶快传话进去,准备酒饭,款待众位义勇。
刚府众女眷本来都呆坐在后堂中,一个个吓得魂不附体,不知如何是好。现在听说老爷回来了,要准备酒饭相待,知道事情已经有了眉目,大家悬着的心才都落了下来,吩咐厨房人夫,准备酒饭去了。
那大师兄见晚饭有了着落,又知道刚毅是老佛爷钦命的义和团统率,顶头上司,不好过分伤了他的脸皮,才亲自拿了一叠黄表,就烛火上点了,放到坛前焚烧,口中念念有词道:“请请,志心归命礼,奉请龙王三太子,马朝师,马继朝师,天光老师,地光老师,日光老师,月光老师,长棍老师,短棍老师,要请神仙纯阳老祖下界,审明二毛子凭纸灰为信,辨明忠奸。急急如律令”。神咒念完,只见有几片纸灰,被那火焰卷起,随风而上,大师兄便合掌对刚毅笑道:“好好好,神意已示,世兄有救了!”又回过头来对地下跪着的志敬、彩凤喝道:“两个孽畜,祖师爷看在相爷敬重神团的份上,饶了你俩的狗命,还不快快退去!”那志敬、彩凤死里逃生,也顾不得许多,赶紧叩头谢恩狼狈而去。
刚毅见神事已毕,忙命摆上酒筵,大堂上顿时热闹起来,众拳勇狼吞虎咽,一直闹腾到三更过后,才拿起旗幡,举起刀枪,一哄而去,到东交民巷攻打使馆去了。
众拳勇走后,刚毅又气又累,本想把志敬、彩凤叫来,狠狠训斥一番,但闹腾了一天,精神已经不济了。他叹了一口气,只得让家人搀扶着,独自到书房中去歇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