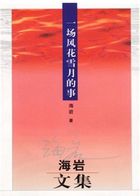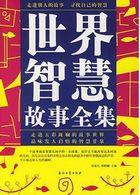这时候覃日格也赶过来了,他一把就将老婆抱进了内房。还让那些老婆子们好生看管,叫她们寸步不离,说如果再去丢人现眼老子就拿你们是问。杨再复便不敢靠近了。这时候,只见老梯玛覃望岳又化了一碗净水,他一边念叨一边蘸水画起了符,然后慢慢地朝着那房里轻轻洒去……水雾漫天漫地的飞舞起来,就像一层大雾罩子,瞬息之间就罩住了一切……而那个疯女人,这时也便渐渐地安静了下来,睡了过去。
高手!高手!
杨再复不能不佩服老梯玛覃望岳法术的高强了,但他心想即使再高强的法术也挡不过子弹,子弹才是这个世上最有杀伤力的武器!但是对于特工来说,有时候,武功甚至比武器更为管用,当彼此短兵相接的时候,谁的身手更敏捷谁就会赢得主动权,因此生死大都操纵在一瞬乃至一闪念之间!所以那时候杨再复依然没有把这个老梯玛放在眼里,虽然他也很佩服老梯玛,崇敬老梯玛,但那只不过是英雄惺惺相惜的一种心态而已。
他知道自己与这个老梯玛并非真正的朋友!他们依旧是敌人,你死我活的敌人!
但是那种心态却把他害苦了。那时他只差使自己失去了最基本最理智的判断——他以为这个老梯玛并不可怕。他还不知道对方的深浅。
大家如此折腾了一天,灵堂差不多已经布置停当了,各项事物都已安排得井然有序。向家大院已是一片萧瑟,一片肃穆。而傍晚的时候,院子里升起了几堆篝火。篝火熊熊地燃烧起来,噼啪有声。火在笑,客来到。这个时候路远的亲戚朋友也都陆陆续续地赶到了。梯玛们就围着篝火开始轮流唱起了“撒尔嗬”——跳丧歌。牛皮大鼓于是敲了起来,牛角号于是吹了起来,乡民们便举着燃烧的油枞火把,踩着“叮咚”的节拍,一边跳一边跟着梯玛们唱开了:
人死饭甑开,
众人围拢来。
屋前一堆火,
打起丧鼓跳起来。
向族长走得好自在,
已经来到了阴阳界。
大伙赶来送一程呵,
哦呢,跳起撒忧尔嗬哩——
就这样,那一群人便围着这熊熊燃烧的火堆,时儿相对击掌,时儿绕背穿肘,时儿踮脚打旋,时儿扭肩擦背,或手之舞之,或足之蹈之,如醉如痴,似癫似狂。围观者也便附和起来了,于是你溜边,他含胸,我屈膝,一齐发出了雷鸣般的吆喝之声:“撒尔嗬,撒尔嗬!”而那头,那手,那脚,那肩,那臀,也便在大幅的扭曲中掀起了一阵阵旋风。看上去,那动作原始而古朴,那声腔粗犷而高亢,那声调抑扬而顿挫,整个场面哪还有一点哀伤的影子呢?根本就不像在送亡灵,仿佛只是对死亡的另一类歌唱。
杨再复这就闭上眼睛了,他开始浮想联翩。因为每当他面对故乡樱花缤纷的时候,他首先联想到的便是生命的脆弱与短暂,他首先萌生的便是消极悲观的怨世之情!可是这个民族呢,他们即便面对的是死亡、是危险,也是这么的淡定,这么的超然,这么的坦荡而无畏啊!这是一种境界,一种自由无量、天人合一的境界!无疑,这个事死如事生的民族,他们已将死亡看成了新生的开始!他们又是多么的乐观、多么的浪漫、多么的豪迈呵!难怪那些上了苏淞战场的土兵将士,当年即便面对倭寇的枪林弹雨,也敢勇往直前、视死如归了。那个时候,杨再复便感到自己的心灵再次受到了创伤,同时也受到了一次前所未有的洗礼!因为在他看来,死亡原本就是一种新生、一种复活、一种涅槃!那个时候,他也便加深了自己对他们日本武士道精神的理解——那是挽歌而不是悲歌!只因那些人全都用的是土家语在唱,一开始他一句也听不懂,就只好请朱先生来给自己当翻译了,想以此感受这个隆重无比、豪放无比的丧葬气氛。可他即便虚心好学,也始终无法融入到这种氛围中去了,因此他便无法感受到那灵魂的飞升与飞跃、逍遥与自在了……但他的心灵这时还是被完全地震慑住了——他只觉得,这个民族已将瞬间化为了永恒,已将悲痛化为了力量!而且更让他不可想象的是,最后一个重要的环节居然是敬白虎——那一仪式,那一情景,简直比敬奉祖先的时候都还要神圣!
那个时候,只听得老梯玛覃望岳正在领唱:
开天有八方,
开地有四方,
开疆辟土有向王,
巴人后裔守稼穑,
哦呢,跳起撒忧尔嗬哩——
就这样唱了几天几夜,最后他们又唱起了“十梦白虎”。杨再复就再一次被震慑了,也再一次被激怒了。因为这个民族,已将白虎放在了顶礼膜拜的高度——跟天一样高的高度。他心想,如果这只白虎不除,那么自己就将永远无法摧毁这个民族的内核——白虎精神了!
他觉得这只白虎简直太可怕太可怕了。
因而他发现,那白虎既是自己的一个噩梦,也将是自己的一个劫数!因而那些天里,他几乎夜夜都梦见自己被白虎追赶,被白虎撕咬,被白虎吞噬……他精神恍惚,他痛苦不堪。一时间,他也便萌生了一种前所未有的伤感与绝望。他想如果自己想要尽早地结束这一噩梦,惟一的办法就是,尽早地拉向大恒下水!那时候他见向大恒进了房间,也便悄悄地跟了进去。但见四周无人,他也便附耳悄声地说道:
“你家的怪事太多了,我动了法术一看,发现这事都坏在一个人身上!”
“谁?”向大恒翻了一下白眼,问。
“我不好说得!”杨再复故弄玄虚,又卖起了关子。“我说得好就好,要是说得不好啊,你还不怪我一脑壳的包?”
“你只管说,我不怪你!”
“都是那个老梯玛在作怪!”说完,他便开始偷窥向大恒的表情了,看是否还有机可趁。
“是吗?这怎么可能呢?他可是我们的老梯玛呀!不可!”向大恒断然否决了。
“可是你,你怎么不反过来想一想呢?”杨再复继续怂恿道,“你讲他姓覃又不姓向,他老覃家出了事,又能不转嫁到外人身上吗?”见向大恒犹豫,他又说:“哼,就为了他老覃家不断后,他们不是把灾祸全都转嫁到你们向家头上来了吗?你再看你姐、你阿巴,还有你自己,不都出了大事吗?这是为什么呀?不正说明他们想要去保那个被白虎叼走的孩子吗?对于他们覃家人来说,你们向家人毕竟只是外人呀!”
这火就点起来了,向大恒的心里就恨恨的,牙根痒痒的了,他恨不能自己立马变成一只白虎,去吃了那些不共戴天的仇人呢!可是在鼓了一阵闷气之后,他又像个猪尿包似的忽地漏气了,“这、这又如何是好?”
“我倒有一个一劳永逸的办法,只是不好说得!”杨再复又开始故弄玄虚,故作神秘。
“你说!只要是为我好,为我向家好,我什么都听你的!我全不怪你!一切后果我自负!”
“只怕你不敢啊,我说了也是白说!”
杨再复依旧在卖关子,他还想吊一下向大恒的胃口呢。因为他知道自己越是故作神秘,就越能让向大恒落入自己设计好的圈套中。而且他坚信猎人也有打盹和麻痹大意的时候。
果不其然,向大恒这时就像蒙受了极大的侮辱,一脸就绽成猪肝色了,乌紫紫的。他说:“我、我难道你还不相信么?”
“我相信!但你想过杀死白虎没有?”杨再复附耳下来,小心翼翼地说。
“杀……杀死白虎?”向大恒忽地怔住了,他张大着嘴巴,竟嗫嚅着半天说不出话来。
“老梯玛不是说过么?”杨再复又怂恿起来,“他说白虎为害人间就得去赶!其实赶的意思不就是去杀么?这个你怎么就不明白呢?”
“可老梯玛只叫去赶,没叫去杀呀!”向大恒吓得一脸铁青的,又连连摇头,感到十分地恐惧。他毕竟还没长那个狗胆!
“哎呀,其实赶和杀不就是一码事吗?”杨再复恨铁不成钢似的冷笑道,“古话不是说,无毒不丈夫吗?要想成大事者,就不可不使点手段!再说,如果你真的想当未来的族长,你就得做出一件惊人之举!哼,瞻前顾后,萎缩不前,优柔寡断,终究成不了大事!最终只能成为一个窝囊废!一只狗熊!”
“唉,你说的简直比唱的还好听!你想我也做得了族长吗?我做不了的!”向大恒不禁摇起了头来。“有我大哥在,他才是做族长的最好人选,我没有那个资格!即便想也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白想!”
怂包!杨再复在心里骂道。其实他也知道,向大恒是不好说得自己只是二房——那个汉族女人——那个青楼女子所生!毕竟他大哥如今还健在。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所以他便假装失望地道:“看来,我是白说了!”说完,他便拂袖而去。不再理他。
没承想沉默了一夜之后,向大恒居然找上门来了。他见四周无人,也便附耳悄声地对杨再复道:
“我也想过了,即使我们敢去杀白虎,又能成功么?把握太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