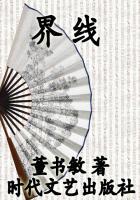这时候,白虎一口就叼住了先放下地的那只小虎崽。而覃月格放下地的那只小虎崽,这时依旧还在地上爬着,哼哼唧唧的,摇摇摆摆的,好不容易才爬到了母亲身边。然后它又回头望了一眼,一副依依不舍的样子。啊啊,多么可爱的小虎崽呀,它也晓得知恩图报哩。覃月格的嘴角一咧,泪水又差点涌了出来。那一刻,小虎崽又多么地舍不得走啊!可是它母亲来接它了,它又不能不走了。再说它们是野性的,是属于大山的,山野才是它们的世界,森林才是它们的乐园,因而它们所需要的,正是自由自在地生长、嬉戏和玩耍。这似乎又与人类大大的不同。因为人类有着太多的桎梏,太多的礼法,太多的束缚,它们适应不了。它们的法则是:弱肉强食,适者生存!所以,月格只能在心底里说:
“你们还是走吧走吧!离人类越远越好!免得再遭人类的伤害!”
这时候白虎掉转头走开了。那只小虎崽也跟着母亲走开了。一前一后,如影随形。可它们刚走了没几步,那只小虎崽就停下来了,它有些走不动了。白虎也只好停了下来,继续耐心地等待着。如是三次,每次都只走了十多丈远,又不得不停下来了。见速度太慢,白虎就轻轻地吼了一声。声音是从鼻孔发出来的,嗡嗡嘤嘤的,显得有些不满。像是在催促。覃月格就犹豫了一下,再也看不下去了,她觉得它们走得实在太慢太慢了,她也便瑟瑟地走上前去,轻轻地抱起那只小虎崽,然后对着白虎傻笑。一副讨好的模样。白虎似乎明白了她的用意,感觉她没有一丁点恶意,就在前面带路了。一前一后,他们便朝着白虎山缓缓地走去了。
世界一片阳光,又一片和煦。
日中的时候,他们来到了葱白岭。白虎停住了,它放下了口里的孩子,示意她可以离开了。但是覃月格没有离开,她反倒走上前来,小跑着下山去了。她来到了迷魂坡,就像一只欢快的鸟儿,展开翅膀,想要飞翔。白虎也赶下山去,赶上前来,然后在前面继续为她带路。他们就朝着白虎山半山腰的那个洞穴爬去了。白虎一步三回头的,在前面等着她,望着她,十分地耐心。终于来到了洞口,白虎就停住了。它把小虎崽放了下地,又开始望着她。覃月格也把怀里的小虎崽放下了地,也开始望着它。白虎就走了过来,舔她的手。痒痒的。白虎舔了又舔,舔了又舔,似乎还嫌舔得不够。覃月格受宠若惊。但她依旧一脸的微笑,一脸的灿烂。哎呀,哎呀,她觉得自己就跟做梦似的,好舒服好舒服呀。她的泪水又情不自禁地涌了出来。
白虎似乎不忍心让她离去,又开始在前面带路,示意她跟着自己进洞去。可是覃月格却没有去,因为那里她去过,她太熟悉了,似乎除了浓浓的虎骚味外,什么也没有。一切都十分的简单。毕竟那是另一个世界,一个不属于人类的动物的世界。就这样,她便一步三回头地离开了,远去了。一路上,她都在轻轻地挥舞着手。远远地,她看见了白虎那留恋的目光,它似乎还在挽留她呢,可她毕竟是人类呵,她听不懂老虎的话,她不懂得老虎的语言,她不能留下来,她不能不回去。
但是覃月格也知道,他们已经是朋友——很好很好的朋友。
37.流浪
一只苍鹰俯瞰着杨再复远去。
出了里溪地界,他来到三河镇,他的肚子就不再痛了。这真是太神奇了。可是杨再复却不想就此甘心,他在三河镇休整了三天以后,便沿着另一条河流上溯而去。眼前依旧是青山,是峡谷,是村寨,是集市,是波涛,是雾海……他知道二千多年前,屈子沿河上溯时,也曾壮志未酬,慷慨悲歌,寻找岸芷汀兰,叩问黎民苍天,一路与鬼神对话。但是他却不知道,自己又该找谁去对话呢?当然,也只有古人与苍天了。于是他站在船头上,迎浪而立,放眼前方。眼前浮现的依旧是时空的隧道。那是一座历史的黑洞,但他走了进去。那个时候,这山是东汉的山,这水是东汉的水,这月亮是东汉的月亮,这太阳是东汉的太阳。那个时候,这里的首领叫相(向)单程。相单程不仅武艺精湛,善于骑射,心有韬略,正直勇敢,而且为民仗义,声名远播。那时候正值东汉光武时期,朝廷猥增贡赋,徭役失平,使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于是建武二十三年,相单程联合土民揭竿而起,声势浩大。东汉王朝遂派兵镇压,第一次发兵万余,乘船溯沅水而入武溪征讨,相单程则采取屯聚守险的战略,将敌人困滞于沅水一带,半途伏击,几仗下来,大败刘尚,全歼敌军,迫使东汉王朝将武陵郡移至临沅,亦即今之常德。次年七月,相单程又率部进攻临沅,声势浩大,锐不可挡。刘秀遂派两员大将,领兵万余前来进剿,企图一解临沅之危。只因马成连吃败战,几乎全军覆灭,又无功而返。朝廷震惊。于是建武二十五年春,朝廷又不得不把伏波将军马援推上前台。那时候马援已六十有二了,他深知厄运已经降临到了自己头上,便主动请缨,准备慷慨赴死!刘秀遂派马援率四万余众再次征讨,于是年农历三月进占了壶头。而相单程知己知彼,依然采取居高守隘的策略,将马援困滞于壶头一带。果不其然,马援引兵前来,因水急而船难于上行,于是首尾自不相顾,再次陷入绝境,再加上天气暑热,士卒不是得病就是疫死,连马援也病倒在军中了,那时候他仅凭一石洞以避暑热。这时候相单程同马援又打起了心理战,他命令士兵们开始升险鼓噪,以蛮歌动摇马援之军心。不久,马援病死于二酉山下。临死之前,他慷慨悲歌,遂写下了一首《武溪深行》的哀诗:
滔滔武溪一何深,
鸟飞不渡,
兽不敢临,
嗟哉武溪多毒淫。
恰这时,这支歌谣又唱响起来了。但却不是在东汉的天空唱响,而是在民国的天空唱响;不是在马援的口里唱响,而是在船夫的口里唱响。这时候船正好行到二酉山下,船夫们也便放开嗓门唱开了。哦哦,那不是唱,是吼。放声地吼。仿佛汹涌的峡谷波涛,跌宕起伏,回音不绝。杨再复不觉哀伤起来,因为他不知道,自己又会不会是那个壮志未酬而身先死的马援将军?有时候历史也会惊人地相似!
半途休息取水。杨再复便下了船。他不仅下了船,还上了二酉山,进了二酉山洞。那时候,面对那石崖和神灵,他不觉心生敬畏,于是赶紧上了几炷香烛。一阵祷告后,他才略微稍安。于是又下山,又上船。然而那首歌谣,却一直回荡在他的脑海之中,似乎一路总在提醒着他,不如归去,不如归去!可是他却反其道而行之,继而又上溯到了酉水岸边的会溪坪。他见到了一根高大的铜柱——溪州铜柱。此铜柱高约两米,八棱形,上面镌刻着楚王马希范和土王彭士愁于后晋天福四年秋爆发的溪州之战的经过和盟约,以此告诫双方子民要世代遵守,和平共处,不可违背。表面上看,溪州之战彭士愁因军事失利而被迫与楚签订盟约,最终臣服于楚,实际上在政治地位以及地域管辖上,他却取得了完全的胜利,从此奠定了彭氏在湘西绵延八百年不衰的基业。直到清初改土归流,这里又才有了流官。
这一天,杨再复试图找到彭氏的后裔,他试图揭开那一段尘封已久的历史。可是一打听,这里大多数人都姓彭,都说是土王的后裔或者嫡传。杨再复嘿嘿一笑,自觉贻笑大方。因为这一带,曾经有一个传说,传说土王白鼻子无道,享有初夜之权,如此一来,土王的后裔岂不是多了去了?这是再明白不过的事了,他居然还在求证,岂不可笑也哉?于是他只得继续上溯、前行,这就来到了千年古镇王村——土司王曾经居住过的地方。这是一个依山傍水而建的镇子,当年土王曾在这里设置官署。但这毕竟已是遥远的事了。可是他依旧不满足,他依旧沿溪而行,这就来到了猛洞河边的哈尼宫。一座隐藏在峡谷里的宫殿。这里两岸石壁,瘦骨嶙峋;峡中流水,幽清澄碧;一泓瀑布,自天而降。一打听,才知这宫殿原是土王麾下的“镇乱大将军”——科洞毛人为女儿哈尼所建造的。杨再复不觉大吃一惊,于是赶紧询问:
“船家,这里真的出过科洞毛人吗?”
那船家啊哈一声,笑道:“眼见为实,耳听为虚,这难道还会有假?你想要是没有科洞毛人,又哪里会有哈尼姑娘呢?要是没有哈尼姑娘,那毛人又怎会在此建造宫殿呢?”
杨再复不语,心想这哈尼姑娘要是与覃家峒的月格姑娘相比,哪一个又更漂亮一些呢?因为在这大半生里,他所见到的这世上最美的姑娘,就当数覃月格了!可惜!可惜!只是这个叫哈尼的美女,自己今生再也无缘相见了!
他继续沿溪而行。
这就来到了灵溪边上的石福城,当地人称之为“老司城”。这便是彭氏土王的故都了。可是一场改土归流,这里如今已经变得萧条不堪、冷落不堪了,往日的雄风早已随风而散,荡然无存。可杨再复依旧不肯停歇,也不知走了多远,忽然间,他又闻听得一片木鱼之声,仿佛天籁一般隐隐传来。啊,这里原来还有寺庙!还有道观!杨再复不禁摇头,暗自一喜,于是加快了步伐,脚步也轻快起来。
行不多远,杨再复猛一抬头,但见一流泉,穿石而出,叮咚而鸣。正好解渴。可是俯身一看,那石边竟镶嵌有字:洗心池!字涂了朱红,煞是醒目打眼。“洗心!洗心!”这不分明是有所指吗?他顿觉不爽,以为天道难测,天理不容,于是又继续前行。
前面是一石崖。抬头一望,但见两块巨石巍然屹立在猛洞河边,崖壁上又草书了四个大字:不二法门。杨再复又一怔,心想自己进还是不进呢?这难道也是自己该来的地方吗?他不觉犹豫起来、踌躇起来。
这时候,但见长空一鹰,“嘎——”地一声,惊得他心惊胆寒、毛骨悚然。可是他又心想,既来之则安之,这“不二法门”又有什么不可进的呢?于是他心一横,胆一壮,又一路看将下去。但见一墨绿石刻,深深地镶嵌在石壁上,苔痕斑驳,含义颇为深刻,他不禁念了起来:“到此人皆佛,同来我亦仙。”又不觉一愣怔,仿佛有一个声音正在天空对他说:“立地成佛,回头是岸!”
然而环顾四周,并无人语,这岂不怪哉?其实这是他的内心在说话,可是他却茫然而无知。于是他昂起头来,又径直走进了庙里。一地斑驳的阳光。
38.学艺
一路上,杨再复把自己想象成了天上那只翱翔的雄鹰,正俯瞰着大地,寻找着自己的猎物。
那时候他发现这个土司王曾经统治过的领地,如今以彭姓人为主,这里同样有端公梯玛,同样唱梯玛神歌,同样跳摆手舞、毛谷斯舞,同样祭祀他们的神——八部大王、彭公爵主、向老官人和田好汉。只是,这里与里溪不一样的是,除了摆手堂外,似乎还有寺庙和道观,尼姑与和尚,甚至还种植着一种叫罂粟的植物。而且他们还从这种植物中提取白色的汁液,熬制成鸦片烟土,然后吸食贩卖,或者换取大量的枪支弹药,保家护院,或与自己的仇家殊死搏斗。那个时候,整个酉溪几乎没有一天安宁过、消停过,到处都是绿林好汉,或占山为王,或各为其主。而闹过一阵红后,那些躲进城去的地主和乡绅,又从城里面回到了乡下,重新获取了土地的所有权、控制权,又开始对失去土地的百姓进行新一轮的疯狂镇压。血洗过的土地,于是催生出满山满岭的杜鹃,也使这个东洋人在那个开满鲜花的溪谷如痴如醉,流连忘返。
但是鲜花总归要凋零的。北风一来,从枝头一过,花瓣就飞落下来了,然后碾落成泥。
接着是白露,是霜降,是小雪,是大雪,是小寒,是大寒……数九寒天,这个年关就到了,这个年也就过了。可是,杨再复却是一个没有年过的人,他见毕兹卡人在热热闹闹地过年,就小心翼翼地询问:“你们为何要过赶年呢?”回答的口径几乎都是一致的:为了纪念抗倭的民族英雄!
他知道,在这个民族的记忆里,倭寇一点也不受欢迎,不受待见。
但这里却有一个好,那就是:这里大多数的人都能讲几句汉话,所以交流起来就不那么困难了。于是这一捱,冬天捱过去了,春天又捱到了。
于是万物复苏,满山满岭的花儿又次第开放。
但是杨再复一点也看不到山花的美丽,他似乎已经没有了人文的情怀与浪子的情愫……又是一个阳春三月,他想日本的樱花也该开放了吧?因为他太喜欢那花的色彩了:无论是染井吉野樱花的淡红,还是山樱和大岛樱花的洁白,还是江户彼岸樱的红紫,以及枝垂樱花的火红,他都无比地喜欢、热爱。那可是他们日本国的国花——国魂啊!而他依稀记得,每年的春天,三四月间,浪漫的樱花从日本列岛的南端向北方次第开放,恰好形成了一条由南向北推进的樱花线,而他的家乡就在广岛和长崎之间——待到樱花一开,那又是怎样的美丽、怎样的灿烂、怎样的浪漫呵!然而如今,他满眼里都是异国他乡的山花了,令他十分地孤寂、落寞、寂寥。然而,他似乎永远也忘却不了,那个老梯玛覃望岳强加给他的耻辱与屈辱——现在,他想加倍地将这一耻辱和屈辱还给那人,他觉得,如今似乎没有什么比这更当紧、更重要的了。
但这样的想法酉溪人却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