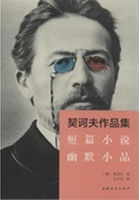但是一路的奔跑,让白虎的肚子一阵阵地发痛了。其实在此之前,它就知道自己快要分娩了,——顶多十天半个月。本来,它想等几天再去偷袭的,可见时机忽然降临,它便迫不及待地完成了这一惊险的壮举!它成功了,同时也付出了惨痛的代价。它快早产了!
那时候望着河对岸的人类和猎狗,白虎感到越来越茫然,越来越痛苦了。它不想就这么快地早产啊。它至少需要一个巢穴,挡风遮雨。所以,当人类的影子消失以后,它又沿来路返回来了。那时候白虎感到双腿铅沉似铁,走起路来摇摇晃晃、踉踉跄跄的,但它最终还是忍受着挺过来了。它想这点痛算得了什么?可等它一爬进洞子的时候,就忽地瘫软在地——它还未喘上一口气,肚子就开始阵痛了。
早产已经不可避免了。
而白虎等待着。它用舌头舔了舔小虎生,小虎生似乎还在安睡,还在梦中。但是白虎知道,这伢崽一点儿没事。那时候他的气息还在均匀地进出,他嘴里似乎还散发着乳香一样的奶味。白虎舔了舔。它舔了舔他的鼻子,还舔了舔他的嘴巴和眼睛,最后又舔了舔他紧握着的小拳头。那小拳头软软的,嫩嫩的,比鸡蛋青还软还嫩,就如琥珀一般透明。就在这时,白虎的生殖器开始膨胀了,又开始收缩了……这一系列的动作,在不断地重复着,交替着,一个胎儿就从子宫里滑落出来了。轻轻地滑落在地。白虎似乎没有感觉到一丁点儿痛苦。它毕竟不是第一次做母亲了。但是那一刻,它却不知那些被自己赶走的孩子的命运现在如何,心想它们或许还好好地活着吧,或许已经不在了,或许被自己的同类打败了,也或许被人类捕获了。因为猎人依旧是它们最强大的对手,最强大的敌人。它们似乎永远也改变不了这一悲剧命运!
但白虎还是立即收回了思绪。
一共滑下地三只。最后一只没有了呼吸,可白虎舔了又舔、舔了又舔,——它将这孩子的绒毛舔了个干干净净,可是,最终这孩子还是没能站起来,久久地躺在地上,一动不动……白虎就知道,它再也站不起来、活不过来了。
白虎没有眼泪,死亡对于它来说,其实并不可怕,而且在尚未意识到什么是死亡的时候就更不可怕。它想死亡也许是一种解脱,一种新生。但是那一刻,白虎知道自己还不能死,它是一个母亲,它还肩负着一个伟大的繁衍的使命!因为这个世界,不能少了它们这个物种啊!
这时候河雾升了起来,天也渐渐地明亮起来。白虎这才看清小虎生的脸蛋:一张圆圆的脸,一张虎脸。十分地生动可爱。正好,那刻小虎生也睡醒了,他似乎也感觉到饿了,他也便睁开了惺忪矇眬的眼。白虎就笑了,它觉得自己与他非常地有缘,一看见他似乎就看见了自己的孩子。这种感觉来得十分的真切,不容许任何人怀疑。
那是白虎最初的感觉,第六感。
而这个小虎生,他似乎也已经感知到这个世界了。不过,对于他来说,此时出现在他眼前的毕竟是一个陌生的世界,和一个陌生的人。哦不不,那不是人,是虎,一只白虎!白虎在想,在他眼里自己很可爱吗?它想小虎生也许还无法辨识出来吧。他还没有这个辨别能力。但他一定能够感知得到——我这个“人”,其实并不可怕、一点也不可怕。不然他一脸惊诧地望着我——他未来的母亲,又怎么会这么咯咯地笑呢?也许他真当我是他的母亲了呢。那时候小虎生把他的小手送进了嘴里,吸吮着,似乎觉得很甜很甜的,而且他的目光始终不曾离开白虎妈妈的脸和眼睛,——他真能辨识出我来吗?白虎在想,在反复地追问。但它搞不明白。它甚至还见小虎生用他的小手捋了一下自己的胡须。“噗——”,它发出了一声细微的声响。那是鼻音。但不是警告,它是在逗他玩儿呢。然而小虎生又哪里知道这些,他依旧捋着白虎的胡须,久久地不放。那感觉痒痒的、简直舒服极了,白虎就不再动了。它知道小虎生并不是恶意,也不是挑衅,而是一种小淘气。可是那几个刚会爬动的虎崽呢,它们又在哪里呢?哦哦,好像都在我的下腹拱动呢,都想吃奶了。一触就触到了。这是动物遗传的本领,天生的本领,不独它们有,任何动物都有。那时候白虎感到自己的奶头痒痒的,好像没有了汁液,没有了奶水。而虎崽们没有吸到奶,这时便不耐烦了,它们哼哼地叫起来,乱拱起来,将那几个奶头都拱到了,都拱红了,可依旧没有一滴奶水。它们就轻轻地叫唤起来、呻吟起来了。
其实白虎知道,这都是因为早产的缘故。
但它却再也无能为力了。这时候它的耳旁又响起了老梯玛覃望岳“摆郎”(夸儿女)的歌声。他把那个代表孩子的“襁褓”抱在了怀里,在骑凤仙子和驮龙仙师的帮助下,找到龙宫凤巢了,找到龙子凤崽了。他的神歌在赞:
科巴启业嘎麦日,(头大好当官,)
吉扒启业石堤踩,(脚大好踩田,)
借儿吉儿墨日里日,(脚长手长制天地,)
卵毕惹毕惹业岔业。(子孙万代都吉祥。)
紧接着白虎就看见老梯玛了,他从“渡男渡女桥”上求子回来了,他咿咿呀呀、不停地叫唤着,似乎也在体验临盆分娩时的痛苦和喜悦哩……他仿佛也快把孩子生下来了。但是过去人们在临盆分娩的时候,都是兴高采烈的、欢欢喜喜的,可如今谁也欢喜不起来、高兴不起来了。因为他们的孩子不见了,白虎也已经早产了。
那一刻,白虎实在是太虚弱太劳累了,它几乎没有一点动弹的力气了,甚至连去掩埋那个夭折的孩子的力气也没有了。它想如果人类这时候到来了,自己就只有等死的份了。但是,它坚信人类这时候不会到来,因为人类已经来过了,他们刚刚才扑了一个空,他们不会想到白虎还会返回来!但是那一刻,白虎感觉到,对自己构成最大威胁的其实不是人类而是饥饿——如果自己再不去寻找食物、再这么等待下去的话,那么这两只小虎崽,哦不,是三个小虎崽,还包括覃日格的孩子,那个小虎生,都将有可能饿死啊!可现在它却动弹不了了。它只得静静地躺着,闭目养神,养精蓄锐,直到小虎生也开始叫喊的时候,它又才想起该寻找食物去了。
哎哎,我的老天爷啊!我的腿咋这么沉呢?白虎再度茫然起来了……
7.喊魂
“儿呀!你回来呀你回来呀你快回来呀——!”
那是向日娜的呼喊声,她在喊她儿子的魂。可她儿子的魂她再也喊不回来了。
那时候望着老婆疯跑的背影,覃日格再也无可奈何、无计可施了。他也喊不回他老婆的魂了。他似乎比谁都更痛苦、更绝望。他只能在心底里对着苍天喊:“老天爷啊,你这是要惩罚我吗?那你来惩罚我好了!可你为何连我的老婆和孩子也不肯放过呀?我的老天爷啊,你难道也瞎了眼睛了吗?”
那时候老天爷也沉默了,也不肯再开口了,他还能怎么办呢?他阿巴又要他赶紧去求梯玛叔,——求梯玛叔为日娜再去做一堂法事,为她镇镇邪,喊喊魂,可他还有脸去吗?他心想,阿巴作为一乡之长、一族之长都不好意思去得,我又怎么好意思去呢?可阿巴的话就是圣旨呀,他又怎敢不去呢?而且他知道,日娜是因为丢了虎生备受刺激才发疯的,这是气疯。如今惟一能够解救的办法,也许就是尽快地将虎生找回来!这样她的病就不治而愈了。可如今,虎生是死是活都还不知道呢,日娜的病又怎么好得起来呢?
这一招不会灵的!覃日格这么想。所以他就不想再去请求老梯玛了。可他又不敢违抗阿巴的“圣旨”啊,他知道阿巴的脾气,向来都是一言九鼎、说一不二,十分地霸道。这时他的脑壳都快想破了,想炸了,也没想出一个好法子来。正好,那刻阿黑就在他身边,他又想踢阿黑一脚了,他心想,老子原本是那么地信任你,你狗日的怎么就放白虎进了院子呢?难道那只白虎真的是神吗?难道它真的会飞吗?老子不相信!但事实已经摆在他面前了,他儿子已经被白虎叼走了,他不相信也得相信了呵。可是那天,梯玛叔却当众说“日格啊,你的儿子没有事,他还好好地活着呢!”唉,他那不是屁话吗?他莫必真的能够下阴取魂、隔山买羊,看得见我的儿子如今还好好地活着吗?
只有天知道。
他觉得自己再没脸去了,即便梯玛叔的话是真的,他也不想再去求什么梯玛叔了。事实上不是他怕了白虎,而是他害怕人类再遭白虎之劫啊!这么想后,覃日格就带着阿黑心灰意冷、茫无目的地走开了。可是不待他们走上几步,阿黑就叫唤起来了。哦哦,哦哦,前面来了一个人:一个妇女,那妇女正抱着一个孩子一边走一边喂奶呢。其实那妇女不是别人,正是二屁的老婆——莲花。一个寨子上的人,谁又不认得呢。她不是也在坐月子才满月的吗?怎么就随便走动了?哦哦,他的心不觉猛然一动:我为何就不能把她的孩子当作自己的孩子呢?这样日娜不是就有救了么?
这么一想,覃日格就来了精神。他想阿巴是族长,如果叫阿巴出面一定比自己出面要好。他于是匆匆地赶回家,不想一进大门,一头就撞在了阿巴身上。
“请来了?”见儿子冒冒失失的,像丢了魂一样,覃望川就狠狠地瞪了儿子一眼。覃日格说:“我想了个好法子哩!”然后就将狸猫换太子的办法一点不落、一五一十地说了出来。他原以为这个办法很妙,阿巴一定会同意的,没承想阿巴忽地将脸一沉,劈头盖脑地就骂了起来:
“你那也叫主意?你儿子是儿子难道人家的儿子就不是儿子了?你晓得心痛人家难道就不晓得心痛了?”
覃日格哑口无言。但他知道阿巴是因为拉不下面皮,怕人家说长道短。所以他便犟犟地说:“不就借来一用么?”
“要是日娜认定那孩子就是她儿子,你又该怎么办?”覃望川鼻子一哼。“难道你还想把人家的孩子抢来不成?”
覃日格无言以对。
将儿子训斥了一通,覃望川屁癫癫地走开了。将儿子凉在了那里。可是覃日格却怎么也想不通了,他心想:好好好,你老架子大,你不去我去,这总成了吧?
这时太阳已经升高了,雾气开始消散。来到二屁家时,日光正好落在他家街沿上,随着他的脚步声在过道上轻轻跳荡。二屁和莲花正在吃早饭,见了覃大公子在门口一闪,立即赶了出来。才吃早饭?覃日格问了一声。是是!二屁回答。进屋请坐!莲花也说。
覃日格鼻子一哼,不屑一顾地进得屋来,便对二屁和莲花如此这般地说了一番。最后又补充说,我想试试看,看这个办法行也不行,到底能不能帮日娜把病治好!其实他嘴上这么说,心里却在想:哼,老子都已经开口了,你二屁难道还敢不答应不成?哼,老子就是想日你婆娘,就是叫你帮老子宽衣解带甚至倒夜壶甚至舔卵,只怕你狗日的也不敢怠慢。他量二屁这颗黄豆子,即使想榨也榨不出几滴黄水来,就更别屑说放什么响屁了。
“要得!要得!”二屁鸡啄米似的点着头,似乎想也没想就爽快地答应了。事实上他是连个响屁都不敢放的人,难道还敢说一个“不”字么?他知道自己的斤两。然而,二屁最害怕的其实不是这个,二屁最害怕的实际上还是覃大少爷的目光。那是一道淫光。那道淫光正不时地盯着他婆娘莲花的胸口看呢。那胸口里有什么呢?毋庸讳言,不就是两个葫芦般大的奶子么?如今大少爷看上了,他能不明白么?他当然明白的。可是他明白了又能怎样?他只得愣神装糊涂,假装不明白。他不想惹祸!除非他活腻了,不想再好好地活了。
事实上二屁回答得如此爽快,就连覃日格也没想到。他想二屁也许是看在老覃家的面子上,才让自己把他家孩子抱回家去的吧。可是一路上,他发现二屁和莲花依然不放心,都悄悄地、老远老远地跟着他呢,生怕有什么闪失!毕竟他老婆失了性,精神不正常!
果不其然,当覃日格兴高采烈地抱着孩子进屋时,向日娜只瞥了那孩子一眼,就把头偏过去了。仿佛视而不见。覃日格忙不迭地说:“日娜日娜,你看你看,我把我们的小虎生找回来了!你看你看!”
向日娜依旧不看。
覃日格愕然,心想她怎么就认得出这不是自己的儿子呢?
这时候,他故意将孩子的小鸡鸡亮出来,又让她瞧。可是向日娜瞧了一眼,却把她的嘴一呶,又自顾自地嘀咕开了。覃日格心想,她难道真的就没有一点指望、一点药救了么?于是又让她看。不承想她竟恼羞成怒,将那孩子忽地推了一把,就“鬼啊鬼”地叫喊起来了。把那孩子也吓哭了。二屁和莲花这就跑了进来,不由分说,一爪就将儿子抢走了。
覃日格绝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