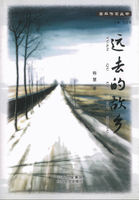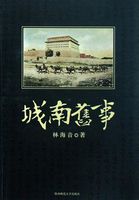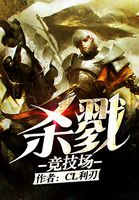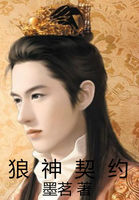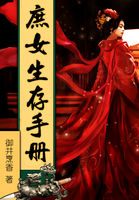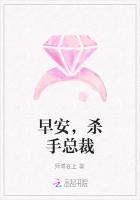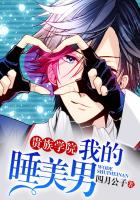艾云
二、肉身的限定
回忆起来,最早听到写作者猝死的消息,感到震惊的是王小波之死。
1997年春的一天,我们在聚会时,文能说,王小波在北京突发心脏病死了。文能当时是《花城》杂志社的名编,他和全国各地优秀的写作者都保持很密切的联系。
王小波?那时王小波还没那么有名,还没有后来所获的哀荣。但我们早就从文能那里知道了王小波。文能在刊物上发了王小波不少的散文随笔和小说,还准备为他出三部曲《黄金时代》《青铜时代》《白银时代》。文能说,不久,北京的王小波一定会成大气候。也因此,我们熟悉了王小波,他就像我们中间早已相识的一个朋友。
文能告诉我们说,王小波为了安静写作,住在北京郊外的一所房子。半夜突发心脏病去世。屋子里有空啤酒瓶,满缸烟蒂,还有正在写的文章。王小波死时才45岁。
我被王小波之死给震住。因为那时候我的心脏也不好,常觉心区憋闷,心悸,没力,头晕。到医院检查,让背个24小时监测心脏的仪器,一天一夜拿下来,医生看了,说是窦性心跳过缓。没什么治疗的办法,让我常服丹参片,如果再严重了,就在包里常备速效救心丹。
心脏病随时会要了人的命。这让我陷入恐惧中。
为王小波之死,我写下一篇文字《肉身的限定》。此文没发表过,此次收录这里:我所谈论的、感慨的问题拿到现在看也没有过时。
我写道:
仅仅是由于热爱精神生活,仅仅指望为世人献出一些自己在摸索沉思中的实话实说,不甘于让愚昧、谄媚成为流行,但他却死了。因写作而死。他什么都不想要,只想将真实和常识性意见表达,但上天却不见容于他。王小波之死,又一次证实这个时代无形中有冥冥的东西在钳制一种纯粹精神生命的生长。
他是累死的。那颗智慧的头颅在一刻不停地旋转,自己把自己捆绑在一架不歇的战车上,想下都下不来了。一个人在学会真实思想时,涌出的话语令上手的记叙追逮不及。却不知,肉身却在咔嚓嚓断裂之中,已到悬崖和深渊,但他却浑然不知。王小波他为什么不先生一场大病?那样,将有一种外力帮助他躺下,有一场缓冲,强迫他停下自己的所想,去试着过一下庸常的生活,可能那就躲过这场劫难了。但谁可以未卜先知呢?一个没有世俗立足之地的人,其实是自己抽走了脚下立存的土壤。他悬空了,只有永远地飞翔,停不下来。后来终于有一天,上帝怜悯他,把他召了去。我们对王小波,只能做如是想了。
一个思想的人死了。隔着冥河总在臆想和假设:如果王小波在生活形式上更讲求一些,更自我关爱,不那么敷衍自己,那么他是否就绕开了死神相约?在远郊独处的房间,是一摞书,一台电脑,一堆啤酒空瓶和一碟烟蒂。他为了拒绝俗世缠绕才选择独处。但日常里一个男人并不懂得如何料理自己。没有烟火燎灶,没有可口的饭菜,没有一定数量的肉类和蛋白质,我说出这些话显得是多么形而下。而身体的物质性是一个铁的事实。在短时间内喷涌出那么多念头,并且使之成型,这是如此耗神伤身的存在方式,却没有相应的营养补充。肉身之人,必得进补膳食,而非餐风啜露。却没有。按理,依王小波文字中表现出来的调皮诙谐的个性,他本不该是将自己耗到绝处的迂阔,他也会否定安渥优雅的生活方式,认为这样的话会影响切肤之痛的深刻表达。他虽是苦孩子出身,能受罪,但他又同时是见过洋世面的人,他该知道精致的生活并不能使精神下滑。但他一切都顾不上了,灵魂旋转得太快,他如果停下来悉心调养,那些喷涌的思想就会稍纵即逝。澎湃的思绪,却造成心悸,肉身太过有限,该停下来却没有打住,没有想到有一双黑手竟是那么快地扼住他生命的咽喉,他喘不过气来。在夜晚降临时痛苦地大吼,猝然被那黑口吞噬,再也没有回来。谁为灵魂担保,谁又为生命担保?物质的块层终于冰消雪融。又是一道电光闪过在刀刃。
多少人为之惋惜,却无奈肉身的限度。每每在想,这悲剧原本完全是可以避免的,可一切都悔之晚矣。在思考与写作的马拉松赛中,王小波将命运之绳撒手丢弃。谁知道他今后还会说出什么令人开悟启智的话呢?
又想到了北方。北方无论如何是听信和膜拜精神性事务的地方。如此理性透彻的王小波,一方面在对常识基地的杂冗进行着清理;另一方面却又是置常识经验于不顾。比如常识说,人要吃饭,有病要医。但他却是饥饱无定,有病不医。粗心的家人没有想到,有一巨大劫难即将降临。北方的家庭,多有热辣的情分,却鲜有具体的照料。他们没有把一些不祥的信号当回事。
看到《天涯》1997年第5期发的《王小波情书选》,他在20世纪70年代末期给李银河的那些情书。这个男人面对爱一点儿也不理性,他是那么疯狂地爱着,开篇便是“你好啊,李银河……”字里行间有类似一个孩子那般渴望爱的真挚深情,但在谈及人类处境和社会问题时他思想的聪睿智慧比比皆是。爱与恨在他身上都是表现得如此强烈,他容不得中庸之道。社会学博士李银河不是一个香鬓秀逸温柔驯顺的女子,而是与他有着共同的精神向度。他对女子的外在几乎不提任何的要求,他只要求一个对话者、交流者。她本该是加倍珍惜,可惜她太要求自己的独立了。她不知道这个如此懂她的男人有一天会累死。她如果知道,怎么也会守在他的身边。然而,她守在他的身边就能躲过这一大劫?天知道,大概每个人的命运都最终要由自己承担,最是相亲相爱的也无法替代。对于他的家人,又能说什么呢?只是再一次觉得可惜。王小波只是热爱写作,并没有招惹谁,却是猝然而逝,这令所有追求这世界彻底性而非通俗性的人心头发颤惊寒。
那颐养很好的人,却是无法展开思考。当我们肉身健壮时,语言隐匿;当我们肉身残破几近断裂时,那语言如陨石雨般纷纷砸在世界的深处,激起无穷回响。是神在嘲笑人类学会思考的能力吗?为什么不该中断处却是戛然而断再无法续接?一切又得从头开始。康德说这就是人的悲剧。人刚刚学会思考,生老病死就席卷而来。一切又得重新开始,一代又一代就是这样走过来的。肉身的有限,使得人类距离居住那个最终的宫殿遥遥无期。
那时我发感慨、写文章,还没有像现在这样江湖;那时文字里仍有年轻时节易于抒情和浪漫的腔调。但在字里行间,已透出我对身体细节的关注。我想说的是,王小波这个多子女家庭长大的孩子,从小不可能得到悉心的照料,况且他也有过1959年到1962年那三年低标准挨饿的经历,他成长时的身体没有足够的营养。长大以后,应该好好补虚了也没有。听文能说王小波高个,极瘦。个太高的男人,很容易心脏供血不足。如果懂中医,首先应该疏通脉络,补补脾胃和肾气。但是这些细节,没有几个男人上心。在北方,不仅男人,又有几个女人对此注意呢?北方是豪爽侠义的,同时又有些粗枝大叶。人们习惯于追求宏大主题,想大问题,想如何救国救民的大计划,想如何让受苦受难的别人挣扎出水深火热之中,这种强烈的忧患感,让他们显得面孔肃穆,气节风骨都令人格外敬重。但是,他们没学会照料自己。忘我、无私是好人的座右铭。
我在想,如果王小波懂得日常饮食调理,能好好吃饭,而不是靠酒烟提神写作,他兴许会躲过致命的一劫。如果他还能活,那颗天才的大脑、通透的心智,有启示意义的文字,还会给读者带来多少的裨益啊。
但是说什么都晚了。斯人已去,托体山阿。
五、谁在背叛遗嘱
通过研究生楼传达室的电话,我们约好了我去他处聊聊米兰·昆德拉。这一段,我在集中看昆德拉的书,《生活在别处》《生命不能承受之轻》《为了告别的聚会》《不朽》《玩笑》,以及新近出的思想随笔集《背叛的遗嘱》。
米兰·昆德拉是捷克作家。他生活在东欧社会主义阵营的国家,他经历的政治环境和意识形态影响,与我们中国很相近。他在文学作品中的虚构与现实、叙事与思考,都很对我们的胃口。那时,米兰·昆德拉在中国粉丝者众多。
这应该是1996年5月中旬的一天下午,约好了我去找余虹。半道上下了小雨,蒙蒙星星的。
爬上9楼,敲开他的门,我进去。此时我脸上的雨水和汗水搅在一起。我不大讲究,用袖子擦了一把脸,拢了拢头发。
余虹给我倒了一杯热水,里边放了一撮枸杞子。他的书桌前放着一个装有枸杞子的玻璃瓶。看来,他对自己的身体还是注意的。
我们一坐定,就开始聊米兰·昆德拉,重点是聊《背叛的遗嘱》。余虹不愧是余虹,他一开腔就抓住了方向,关于这本书,他说有必要引入“幽默”这个概念。
这个概念,过去是被我们悬置的,尽量不去碰它。比如1990年在河南平顶山开会,讨论的是“语言学转向”的概念,比如1992年湖南长沙,讨论的是“荒诞”的概念。“幽默”在相当长一段时间被我们认为不那么严肃和深刻。
那天下午,我们就这个概念聊得很深入。回去以后我追忆了笔记,这是我们共同的讨论,我没有写下谁说的,谁说的,只写下了最值得记叙的段落,现在翻看,仍然是概念条理都很清晰。
我的笔记写下我们所讨论的几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为什么会引入“幽默”这个概念。
以前的文学作品,基本上是道德判断在前,而叙事在后,叙事是以道德判断为前提而展开,如古典时期和浪漫时期的作家和作品。举例子来说,比如劳伦斯看起来很离经叛道,实际上他还是属于道德判断在先的作家。劳伦斯写性爱,首先把爱情放在前提,查泰来夫人和守林人是由于爱情而导致性爱。这样,作为爱情的性爱就被赋予了肯定性道德判断。再比如英雄,拜伦在前期以英雄崇拜为前提,这当然也是价值与道德判断。
而到了卡夫卡,则一切都有所改变。《城堡》中,K在未进入城堡时与酒店妇女有过一夜做爱。这仅仅是出于不可抑制的情欲,与爱情无关。在人的欲望冲荡中就那样做了,它取消了道德判断,悬置了意义,还原着人性真实。这人,既非英雄,也非卑劣的人,一句话,他只是个平平常常的人。
现代派的文学作品中所关注、着力描摹的全是些平平常常真实的人。这些人是没有深度的。作家所采取的也只是“幽默”的态度,既无法赞赏也无法抨击。幽默的态度是无奈之中一抹超然的微笑。但这种超然的微笑里边是否仍然含有道德判断的意义?
我们在讨论幽默中超然的微笑,依稀记得当时余虹脸上的表情一点儿也没笑容。因为我们直奔主题要谈问题,这不需要交际性的表情,不必强装出热情去应酬。这时的余虹因更深地进入到问题与思考,他的面孔非常冷峻。
我看到他脸颊瘦削,眼神疲惫。他早已谢顶,却有头屑落在黑色圆领衫上,密密一层。我当时心有一阵抽搐;这些,就像那蜕去的老皮,但是没有长出新质。这个男人,越发有学问有见识,但他是再也没有嬉戏和幽默的笑容了。
接着我们讨论的第二个问题是:取消了道德判断也就是取消了道德追问以后的文学是什么样的?
以幽默入文学的作品,还可以举出拉伯雷的《巨人传》。这部小说的幽默是带着反讽的意味。人不是无所不能的巨人,而是处处会露出破绽的可笑的人。西方这时期的作品,仍没有取消道德判断。
米兰·昆德拉的小说并没有完全取消道德判断,只不过他是把叙事放前把道德判断放后,而不是相反。他用更多的冷静,去打量活动于人生舞台上的男男女女林林总总。他引入时间,谈及性与革命。这两项,都是人超拔出平庸乏味日常生活的一些奇迹般行为方式。这种方式让人变得有了野性而不那么畏葸,有了正义感而不那么俗套。这使人有了一种新的可能。
我们继续聊着,显然是他讲得多,我在聆听。他有一刻停顿,拿给我一个小勺,说:“你把杯子里的枸杞子捞出来吃了吧,比光喝水还好。”我照做了。
我们都在喝水,歇一歇。讲话,尤其是讲这么劳心伤神的话,是很累人的。有道:日有千言,不损自残,讲话多了会伤气,伤元气。
有一阵我在想,余虹还懂得枸杞子泡水喝,他比我有养生意识呢!
事实上也是,余虹本人是个比较全面的人,他很懂生活,也很有美学鉴赏能力。他做得一手好菜,有一次我们几个朋友到他家里吃饭,他的糖醋鸡块好吃极了。我向他学了这道菜,至今我待客,这菜仍是我拿手的保留节目。
余虹不仅会写文章,他还会画画,懂封面设计,他也会挑衣服。有一次他陪我去广州环市东路的友谊商店去买衣服。他帮我参谋,挑了两件上衣,一件咖啡色亚麻面料的双排扣列宁装,一件是灰色丝光蝙蝠袖上衣。这两件衣服做工精良,样式至今也不过时。
现在我写这篇文章,我拿小勺捞着吃泡水枸杞子的情景,历历在目。当时,余虹已经知道吃些枸杞红枣之类的食补材料,这很好。可这仅仅是杯水车薪啊。他一直掉头发,不到40岁就开始谢顶,头皮屑多,这是他内里早就脾胃失调、肾气不够的原因。他的身体如果要调理,岂是食用枸杞红枣可以解决根本问题。那该是一项旷日持久的大工程。这工程需要很多步骤,要慢慢着手改变。
这步骤里边,首先是观念方面,要懂得没有身体,何谈精神。
其次是要认识身体,把身体当成一个微循环的小宇宙来辩证地看待。要改变滥用西药的愚钝观念,要懂得先通脉络然后温补。通了脉络以后,像余虹这样常吃枸杞就很好。如果人的脉络不通,吃什么都没用。不仅没用,还会堵在那里造成麻烦。
这些,不仅余虹想不到,我们当时谁也不会往身体、保健、养生这方面想。当时还年轻,以为身体有某种不适,扛过去就行了。还有就是对精神、灵魂过于迷恋,张口闭口都往这方面扯,让我们潜意识里觉得那么关心身体简直是庸俗。
这就是我们普遍的逻辑。余虹还不到40岁,就已经可以写出立论严密、思辨有力、文采斐然的理论文章了;他的讲课也给人以润物无声的甘霖。但这要耗他多少的精元之气和肝血。
同龄人中还有刘小枫,那也是一个早慧的天才和罕见的大家。刘小枫是四川人。四川是中国精神生活十分活跃、人才辈出的地方,学问、绘画、诗歌都有大家出现,学问中人如刘小枫、徐友渔、王岳川等人;绘画中人如罗立中、周春茅等人;诗歌中人又有欧阳江河、周伦佑、翟永明等人。余虹实际上父母都是四川人,他从小也出生在四川。
而湖北则是余虹下乡、升学、结婚生子、工作的地方。湖北是他的第二故乡。鄂人好生了得!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以至到90年代,这里都被称为“智力强力集团”。哲学思潮和美术思潮涌动,牵动着几乎是中国思想、艺术界的神经。笼统地说,这里边的李明华、张志扬、陈家琪、萌萌、邓晓芒、彭富春,以及尚阳、皮道坚、彭德等人,莫不为人所知。
余虹浸润着川人和鄂人坚定执着的精英文化立场,他希望通过语言,找到二度命名,而成为一个对人类有贡献的人。
他的立意高而洁。
稍稍喘息片刻,我们接着又谈到第三个问题:米兰·昆德拉笔下的性。
性这个问题,无论是作为叙事的材料,还是作为叙事者写作时的推动力,它本身都含有许多价值判断之外的东西,即它在善恶之彼岸。
所有的原创性写作,离不开生活本能和真相的东西,肉欲的性爱描写,无可回避。《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中昆德拉笔下的萨宾娜,是个需要在流浪中才能激发自身灵感的人。她不要一个名分的婚姻,却不拒绝性爱。这个女人是艺术的,她本人也是艺术家,她画画。她通过性爱的方式,让艺术的原创能力得以保有。性爱,是对一个艺术家的艺术创造力之推动。这正如西方浪漫主义时期对性爱本身的认识那样。比如施莱尔马赫这样说道:“人身上的一切精神性不都是从一种近乎本能的、模糊不清的内在冲动开始的吗?不都是逐渐通过自发行动和习惯,才发展成一种明确的意愿和意识,成为一种自身圆满的行为吗?”
西方的浪漫派时期推重内在的肉体冲动,认为这是人获得精神性的前提。浪漫派在18世纪末19世纪初的确创造了一个辉煌。尤其在德国。自此以后,直到20世纪以后都很难再出现这样一批杰出的思想家和作家。当然,他们那时推崇梦幻,理想主义里边掺和有游戏的成分。到了昆德拉的年代,他谈论性爱,把它放到了既是游戏又是严肃话题的位置。
所有原创性的作品都无法摆脱内在的冲动。这不仅仅是出于对内在原创性的认识,而是因此才可以催发原创性作品的出现。你的理性认知只能置后。而在此之前产生的创作冲动,先不必受理性的规范和制约。身体、欲望、性爱,这构成了原创性作品的重要方面。这也就是德国思想家施莱尔马赫所说的关于内在冲动导致精神性的意思。人在内在冲动过后,为了寻找心灵的解脱,为了给造次找一个充分理由律,人需要反躬自省,也需要寻找慰藉和超拔,这样,精神性的东西可能就被牵引出来了。
以上是我整理出的与余虹讨论的笔记。这基本上可以算是一篇比较像样的文章了。
可那时我们仍嫌不够,发誓说一定要语不惊人死不休。那时,我们恨不能将人类全部的思考都让自己承担下来,却不管不顾自己的肩膀原本是十分单薄和柔弱。
现在回忆起来,余虹侧重讲的情欲作为原创性的内在推动,是和自己曾经有过的情感经历关联的。但他不是现代性的,而是古典主义的情感模式。
比如他爱师妹,那爱如此纯洁晶莹。他不惜解除既有的婚姻,幻想与那个女子重缔一个家庭。他不要秩序之外的偷情。当他把师妹揽在怀里拥吻的那一刻,他看到那张年轻饱满的面孔,如飘荡在空中的青春灿烂的旗帜。拂动晶莹的肌肤如丝绸般划过,那细腻柔美,似乎让他的陈皮蜕落,长出新质。他看到蓝天之上,洁白的鸽子翩翩掠过。
他过于古典,并不知女生的心思。女生在他这里学习着情感,然后又走向另一个驿站。经历一路洗练,她才会找到最后的屋宇安身立命。而他以为这就是地老天荒了呢!
这中间是年龄造成了他们之间的错位。余虹认为已经做了的,就是无可更改了。他对于终极、永恒这些字眼看得太沉重了,他不喜欢某种瞬间,哪怕这瞬间极为震撼。他想要将瞬间变永恒。
聪明、正值豆蔻年华的师妹需要过程的演练。这个才华横溢、受苦受难的男人的确让她敬佩,可她并不想从此蜷缩在这个沉重的翅膀之下,去过保守主义的生活。师妹才是现代人呢!她早已知道,生活最终都是朴素的原色。跟着他,所有的日子已经确定,那就没有任何神秘与欣喜了。日子和所有人过的一样,都会味同嚼蜡。聪明的、年轻的姑娘会想,这个有才华有学问的男人,能带给她很多的幸福吗?未必。如今的甜言蜜语、海誓山盟都可能是囚禁自己的枷锁。当她知道他离婚的消息,就谜一般从他的生活中消失了。这就像昆德拉笔下的海伦娜,当她得知与她幽会的情人离了婚想要改变与她东躲西藏的生活,从而像正常夫妻一样长久厮守时,她神秘地消失了。她不想要这种囚禁,正如同不想要忠诚。
我看着一脸疲惫的余虹,感觉他还没有从上次情感的失意中解脱。现在他想用学问压住他对情感的记忆。
余虹用学问的方式在谈论性爱对艺术原创的催发,他越来越多的是从自己血肉丰沛的生命体验中,去抽象、概括出这些判词,以提醒别人写作时用。他自己却不要将初始性记忆变为写作的质料。他在永无止境的学问和追思中。
聊了一下午,我收获不少。傍晚时分,我起身告辞,要赶回家做晚饭。
出暨大校门,过天桥,对面有30路车,可以到我那时住的麓景路的家。
天不下雨了,还没有完全黑透。坐在公交车上,我的脑子奇异地清醒,那是被打开被唤醒的清醒。
我明白自己,对于抽象和命名,我自知不行。我没有如此深厚的哲学准备,也没有过人的理性归纳能力,我智力平平。但我会朝向精神生活靠拢,并努力学习如何进入。
原载2015年第5期《广州文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