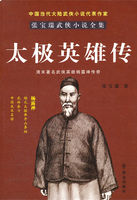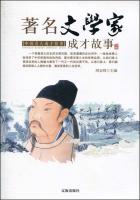突然雄河马从前方湖面冲出,喷出一股臭气。虽然远在箭的射程之外,但刺鼻的气味仍飘浮到我们头的上方。河马的后背突出在水面上,像一座花岗岩岛,在泻湖中闪闪发光。它呼啸着吸口气,转身又消失了。
“追上它!”塔努斯大喝。
“它在那儿。”我叫道,指着船那边。“正往回返呢。”
“好样的,老朋友,”塔努斯冲我笑。“我们会把你塑造成勇士。”这种想法太荒谬了,我是文书、哲人、艺术家。我的英勇行为就是我的思想。但我当时仍然感到一阵满足,我的表现一直受到塔努斯的赞扬。因为追逐河马,我一时兴奋,感觉不到恐惧了。
南部的船只也加入到追捕中。哈比神庙的祭司严格统计着泻湖中河马的数量,允许捕杀五十只迎接即将到来的奥西里斯节。这就是说,在神殿的泻湖中,女神还有近三百头牛。祭司认为这个数字最理想,既可以保持水道不被芦苇堵塞,还可以防止纸莎草滩侵犯可耕地,同时还能定期向神殿提供肉食。只有祭司们可以在奥西里斯节后十天还可以吃河马的肉。
所以捕猎就像某个错综复杂的舞蹈在水面展开。船队的各艘船互相交织、快速旋转,而狂怒的野兽在前面逃跑,跃入水中,喷气、咕噜着游出水面,然后再跃入水中。然而,追赶的船只逐渐逼近,它们无法在水下吸足气,不得不一次次跃入、呼气、再跃出,间隔时间越来越短。与此同时,每艘船上都发出艉楼铜锣的敲击声、桨手们兴奋的呐喊声和舵手们的激励声,一片疯狂的吼叫和混乱。受到这群嗜血成性的人们的感染,我也欢呼喊叫。
塔努斯把目光集中在了第一头也是最大的雄河马身上,忽略了射程内的雌河马和小河马。每次大河马露出水面,它们也跟着跳跃,逐渐靠近雄河马,毫不动摇。兴奋中,我钦佩塔努斯指挥荷鲁斯呼吸号的能力和手下船员对他手势的反应。在那时,他一直有能力让手下指挥的所有人发挥出最佳状态。然而,既没有财富,也没有某个了不起的庇护人支持他,他如何能迅速地晋升到现在的地位?尽管暗藏的敌意与陷害为他的成长设置了一道道障碍,但是他还是靠自己的功绩赢得了一切。
突然,雄河马在不到三十步远的地方冲出水面。阳光下,它闪闪发亮,像个怪物,又黑又吓人,云雾般的气流从鼻孔中喷出。它好像是来自阴间的怪物,刚吞食了众神的心脏。
塔努斯搭上箭,举起大弓,瞬间射出。莱妮塔闪闪发光,发出可怕的响声,旁人还未等看清,箭已飞出去。一支箭还在空中嘶嘶作响,另一支跟着飞出去,紧接着又飞出一支。弓绳像鲁特琴嗡嗡作响,箭一支一支飞出去,全部射入雄河马宽阔的后背。它惨叫一声,又跃入水中。
这些箭都是我为这次捕猎特别设计的。箭已不是带羽毛的飞箭,而是用猢狲木做的、类似渔夫浮网用的小浮漂。浮漂在箭杆尾部滑动,飞行时不易脱落;但是一旦野兽跳入水中、身上插着浮漂游动时,可以很容易把浮漂拔出来。箭柄上的细亚麻线把浮漂固定在青铜箭头,一旦浮漂脱离,线就会散开。现在,雄河马正在水下快速游动,三个小浮漂突然浮到水面,在河马旁漂动。为了便于识别我把浮漂漆成鲜艳的黄色,因此雄河马即使在泻湖的深水里,也一下就会被发现。
这样塔努斯就能提前知道雄河马的每一次疯狂冲跃,就能指挥荷鲁斯呼吸号掉转船头快速冲过去,也就能在河马浮出水面的瞬间,把箭射向水底下闪闪发光的黑色后背。现在雄河马身后拖着一个漂亮的黄色浮漂花环,周围的湖水因而泛起波纹,打旋,被血染红。它每次吼叫着来到水面,每次又被疯狂呼啸着的箭射中。尽管我此刻情绪高涨,但也不禁涌起一股同情。
我年轻的女主人没有这种同情心,她一直高度紧张,心里既害怕又觉得有趣,兴奋得不停惊叫。
雄河马再次在我们正前方出现,逐渐靠近荷鲁斯呼吸号。它的嘴张得很大,一眼可以看到喉咙——一个鲜红色的肉质隧道,完全可以轻松吞下一个人。看到它嘴里的一排牙齿,我的呼吸停止,浑身不寒而栗。下颚的牙齿就是巨大的象牙镰刀,用来收割粗糙、坚挺有力的纸莎草茎;上颚的牙齿就是发光的白色箭柄,有我手腕粗,足以剥去荷鲁斯呼吸号船身的木头,就像我咬玉米面饼那么容易。我最近检验过一具农妇的尸体。她在河岸上割纸莎草时,惊扰了一头刚生完小河马的雌河马。这个女人的死状就像是被最锋利的青铜剑齐整地切割成两半。
现在这个颚上长满发光牙齿的怪物被激怒了,正向我们袭来。我在艉楼,绝对远离它,但我也吓呆了,如同神殿里的雕塑,一声不响,一动不动。
塔努斯又射一箭,箭径直飞向张开的大口。然而这个大怪物本已痛苦至极,似乎没有注意到又飞来的箭。这一箭最终被证明是致命的。雄河马毫不迟疑,直冲荷鲁斯呼吸号而来。它受尽痛苦的折磨,临死时喉咙中发出令人恐惧的愤怒吼叫,动脉破裂,从张开的颚中喷射出一团团血,在阳光中变成红色的薄雾,既美丽又令人害怕。这头雄河马一头摔进了我们的船头。荷鲁斯呼吸号像狂奔的猿,正在水上破浪行进,但愤怒中的雄河马速度更快,再加上它的巨大块头,我们就像在石头岸上搁浅了。桨手们被甩得离开座位,趴在地上。我也向前扑去,撞到艉楼栏杆上,肺部用力一挤,犹如被坚硬石头击中,胸中疼痛难忍。
痛苦中,我关心的还是我的女主人。我痛得流出眼泪。透过泪水,我看见她由于惯性被抛向前。塔努斯伸出胳膊用力抓住她,但因为巨大的冲撞力,他也失去了平衡,左手握着的弓更让他无法用尽全力,只能片刻减弱她向前冲的力量,但她的身体仍在摇晃,抓住栏杆的双臂像风车般疯狂转动,后背向后突成拱形。
“塔努斯!”她尖叫,伸出一只手去抓他。他身手敏捷,恢复了平衡,尽力去抓住她的手。就在他们的手指相碰的一刹那,她的身体似乎被拽走,抛向一边。
从船尾所在的高处,我能随她一起掉下。她像猫一样在空中翻滚,白裙子向上飞扬,露出精致的大腿。我以为她似乎要永远坠落下去,开始痛苦地大哭,她也绝望地哭起来。
“我的孩子!”我叫道。“我的孩子!”我肯定她消失了。我熟悉的她的全部生活似乎在我眼前重现。我又一次看见那个牙牙学语的幼儿,听见她给我——她喜爱的“保姆”的婴儿般的爱抚;我看见她长成女人,记得她带给我的每个欢笑和心痛。在失去她的那一刻,我比以往十四年都更爱她了。她坠落在愤怒的雄河马宽阔、鲜血四溅的脊背上,四肢张开,就像某个色情宗教祭坛上的人祭品。雄河马四处转动,高高跃出水面,巨大变形的脑袋向后扭曲,竭力要咬到她。它疯狂乱咬,充血的眼睛闪着贪婪的光芒,下巴嘎嘎作响。
射中的两只箭在河马宽阔的背上突出,就像两只把手,洛斯特丽丝用尽全身力量紧紧抓住,然后四肢仰卧。她不叫了,用尽一切办法和力量稳稳躺在上面。那些弯曲的象牙般的牙齿互相碰击,就像对决武士的剑柄在空中交叉对峙。牙齿每咬一下,似乎离她越近,只差一手指的距离;而每一刻,我都想象她可爱的、像葡萄藤上生长出的嫩芽一样的肋骨被剥掉,想象她鲜红的、年轻的血液和雄河马头上伤口中流出的野蛮血液混到一起。
在船头,塔努斯很快意识到发生的一切。他的脸色看上去很可怕。弓对他已不再有用,他把弓扔向一边,抓住剑柄,猛地从鳄鱼皮鞘中抽出。青铜柄闪闪发光,和他的胳膊一样长,刃磨得很光,能削掉手背上的汗毛。
他跳上甲板边缘,掌握好平衡,看着水里严重受伤的雄河马在疯狂旋转。他猛地向外一跳,像俯冲的隼,双手同时握着剑尖,向下刺去。
他跳到雄河马的粗脖子上,骑上去,好像要骑着它进入地下。他身体的全部重量和那猛的一跳都不及他刺的那一剑。剑柄一半刺入河马头骨根部的脖颈。塔努斯像骑士一样坐在上面,用尽双臂和宽阔肩膀的力量,反复转动,把锋利的青铜剑深深刺入。剑一刺入,雄河马发疯了。这下,塔努斯的攻击就显得脆弱不堪了。河马巨大的身体几乎完全高耸出泻湖,左右摆头,在空中甩出大片水幕,落在船甲板上,像窗帘遮住了我眼前的景象,让我惊恐不已。
我看见他们俩在大怪兽的背上剧烈颠簸。洛斯特丽丝握着的一支箭柄咔嚓折断,整个人被抛出去。如果真是这样,她一定会遭到雄河马的凶猛攻击,被那些象牙利齿撕成血片。塔努斯左手向后伸去稳住她,而右手一直在把青铜柄深深刺入雄河马颈背。
河马无法袭击到他们,乱咬身体两侧,侧面的伤口越来越大,木船周围五十步范围的水域都被染成红色。洛斯特丽丝和塔努斯全身也被雄河马喷出的血染红,脸上像戴着怪异的红色面具,只有双眼苍白地怒视着。
剧烈的死亡之痛让雄河马撇开小船,越游越远。我是船上第一个恢复理智的人。我冲桨手们大叫:“追上他们!别让他们游远了!”桨手们跳到各自位置,驾驶荷鲁斯呼吸号追过去。
在那一刻,塔努斯的剑似乎找到了巨兽的脊柱关节,他下举刺入。雄河马巨大的身体僵直不动了,四肢僵硬地伸开,肚皮向上翻过来,扎入泻湖,驮着洛斯特丽丝和塔努斯向下沉去。
我抑制住绝望的恸哭,向脚下甲板上的桨手们怒吼,下令:“向后划!不要把他们撞翻!熟悉水性的,快去船头!”我被自己声音中的力量和显示出的权威吓了一跳。
木船前进的路受阻了。我还没来得及经过深思熟虑,一群勇士已涌向甲板。他们眼睁睁看着任何一位船长溺水,都很可能欢呼起来,但不会欢呼他们的塔努斯。
我脱掉衬衫,赤裸着。任何情况下——即使扬言要鞭抽一百下,我也不会这样做。只有一个人很久以前见识过政府行刑官给我留下的那些伤疤,那个人就是首先下令对我实施阉割的人。但是现在,我完全忘记了作为一个男人自己肉体上的残缺不全。
我的水性极强。虽然现在回想起来,当时的莽撞令我发抖,但是我真的相信我能从船舷跳下,游过血染的河水,去救我的女主人。然而,正当我站在船栏杆旁时,脚下的水分开,两个脑袋冒出来,浑身往下流着水,靠近得就像一对正交配的水獭。一个黑,一个金黄,但两个人都发出了一种声音,一种我听见过、却又是最不可能的声音——大笑。他们一边踉跄地向船边游来,一边尖叫,一边忘情地大笑。他们紧紧拥抱在一起。我确信他们真的有可能要把彼此溺死在水中。
面对这突如其来的变化,再想到自己即将采取的愚蠢举动,我所有的关心立刻转化成愤怒。就像找到丢失孩子的母亲,第一个本能就是痛打他一顿。我听见自己的声音不再像刚才那样深沉、充满权威,而是尖叫着在抱怨。十几只手主动伸出去把我的女主人和塔努斯从水中拉上来。他们一登上甲板,我用我一向的好口才痛斥她。
“你这个鲁莽、没约束的小野人!”我责骂她,“你这个不假思索、自私、无纪律的小野丫头!你向我保证过!你向女神的童真发过誓……”
她向我跑过来,双臂搂着我的脖子。“哦,泰塔!”她大喊,仍咯咯笑着。“你看见他吗?你看见塔努斯跳过去救我吗?这难道不是你说过的最伟大的事迹吗?就像你给我讲的那些最棒的故事中的英雄。”
我刚要做一个类似英雄般的手势,但没人理会,这又让我火上添油。与此同时,我突然发现洛斯特丽丝的裙子不见了,贴着我的身体凉冰冰、湿漉漉,完全赤裸着。她正把全埃及最匀称、最紧绷的两个屁股蛋裸露在全体船员粗鲁的视线中。
我抓过手边的盾,遮住我们两人的身体,同时大喊她的女奴给她再找条裙子。她们咯咯的笑声让我更加狂怒。我和洛斯特丽丝一穿好衣服,我就把矛头指向了塔努斯。
“你这个粗心的恶棍,我要向英特夫领主汇报!他会抽掉你后背的皮。”
“你不会这样做的。”塔努斯冲我笑,一只湿漉漉肌肉发达的胳膊搂着我的双肩,使劲拥抱我,致使我的双脚离地。“因为他会愉快地棒打你一顿。不管怎么说,老朋友,谢谢你的关心。”
他搂着我的肩膀,快速环顾四周,皱起眉头。荷鲁斯呼吸号已经远离了船队,但现在捕猎结束了。除了我们的船,其他船都装满了祭司准许的最高份额。
塔努斯摇摇头。“我们没有利用好我们的机会,对吗?”他咕哝着,命令一名船员向其他船只发出归队信号。
他挤出一丝笑容。“让我们一起喝一大杯。我们已等了一会儿,太口渴了。”他走向船头,女奴们正在那儿和洛斯特丽丝发牢骚。她们正在甲板上举行即兴野餐。开始我还一直很生气,因为不能加入其中,但为了维护我的尊严,我孤零零地待在船尾。
“哦,让他气一会儿。”我听见洛斯特丽丝一边小声对塔努斯说,一边给他的杯子倒满泡沫啤酒。“老朋友在吓自己,但是他一饿,一切就会过去的。他十分爱吃自己做的食物。”
她是不公正的典型,她就是我的女主人。我从不生气,我不是贪吃。我那时仅仅30岁,但是对于一个14岁的孩子来说,20岁以上就是老人。我承认,说到食物,我确实像美食家一样,有精细的味觉。她炫耀的无花果烤野鹅就是我最喜欢的一道菜,她非常了解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