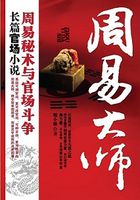直到爱妮丝离开伦敦时,我才又见到尤来亚·希普。我去票房向她告别,为她送行,他也在那儿,准备乘同一辆车回坎特伯雷去。我在爱妮丝面前努力和尤来亚维持友好关系,我想这努力理应不会白费。有很久,我都无法忘记分别时的情形。
在订约做实习生的那天,除了用夹心面包和葡萄酒在事务所招待那些文书们以及晚上一个人去看了戏,我没举行任何庆祝活动。订好约后,斯宾罗先生说,要不是他女儿就要从巴黎回来而家里的安排又有点混乱,他很愿意请我上他在诺伍德的家,庆祝我们的新关系。不过,他表示,女儿回家后,他希望能有机会邀请我。我向他表示了谢意,也由此知道了他是一个有女儿的鳏夫。
过了一个或两个星期,斯宾罗先生就提出了邀请,并说如果我肯赏光在星期六去他家并呆到星期一早上,他会很高兴。我说我很乐意,他就决定用他的四轮马车接送我。
斯宾罗先生的住宅有个漂亮的花园。虽然并非时值一年中赏玩花园的最佳季节,但我仍被那打理得十分美丽的花园迷住了。那儿有一片草地,有一丛丛的树,有我在昏暗中仍可辨出的观景小径,小径上有搭成拱型的棚架,棚架上有时令花草。
我们转进附近一间房,我听到斯宾罗先生介绍:“科波菲尔先生,小女朵拉,小女朵拉的密友。”一刹那间,我就神魂颠倒地爱上了朵拉·斯宾罗。“我,”一个熟悉的声音说道,“从前见过科波菲尔先生。”说话的不是朵拉,而是那个密友,默德斯通小姐!我不认为当时我很吃惊。在物质世界中,除了朵拉,一切可令人吃惊的事物都微不足道了。我向默德斯通小姐问好,并问候默德斯通先生。她答道:“舍弟很健康,谢谢你。”
斯宾罗先生对我说道:“小女不幸丧母,多亏了默德斯通小姐来做她的伙伴和保护人。”
当时,除了朵拉以外,对任何问题我都不会想了。我坐在火炉前,想着那迷人的、孩子气的、眼睛明亮的、可爱的朵拉。
除了朵拉,我不记得还有谁在那里了。除了朵拉,我不记得桌上有什么菜肴。我坐在她身旁,和她谈话。她的声音细声细气、悦耳动听,她的一切都是娇小的。越娇小越可爱,我这么认为。
那个夜里,我深深陶醉于幸福中了。当默德斯通小姐把朵拉带走时,她微笑了,向我伸出她那芬芳的手。我在一种如醉如痴的状态下入睡,又在一种脆弱迷恋的心境中起床。
这是个晴朗的早晨,时间尚早,我觉得我应该去那些拱形花棚下的小径上走走。我走了没多久,就在拐弯处碰见了朵拉,她带着一只被她称为“吉卜”的狗。
“你出来得这么早,斯宾罗小姐。”我说道。“在屋里那么无聊,”她回答道,“而默德斯通小姐又那么荒谬。她胡说什么要等天气干一点我才能出来。在星期天早上,我不练习音乐,我总得应该有点什么事干呀。所以我昨晚告诉爸爸,我非得出来。何况,这是一天中最亮的时候,你不这么认为吗?”
她把她那鬈发披了下来,我从没见过那样的鬈发呢!而那鬈发上的草帽和蓝缎带,如果我能把它们挂在我的卧室里,对我而言,那会是怎样的无价之宝呀!
“你刚从巴黎回来吗?”我说道。“是的。”她说道,“你去过巴黎吗?”“没有。”
“你和默德斯通小姐并不亲密,是吧?”朵拉说道。“不,”我答道,“一点也不亲密。”“她挺讨厌,”朵拉噘着嘴道,“我真想不通,爸爸选了这么一个让人讨厌的人陪伴我是为什么,是不是,吉卜?我们不会信任那种性格怪僻的人,我们喜欢信任谁就信任谁,我们要寻找自己的朋友,是不是,吉卜?”
默德斯通小姐找到了我们,然后,她挽起朵拉的胳臂,率领我们去吃早饭,我们就像是一支送葬的军人仪仗队。
由于茶是朵拉泡的,我不知道喝了多少杯。然后,我们就去教堂。那一天我们安安静静地度过了,我们散了一次步,4个人用了家庭晚餐。
第二天清早,我们就动身回去了,因为海军法庭正在审理一桩救援船只的案子。我一直盼着再度被邀请去斯宾罗家,可我不断失望,因为我再未受到这种邀请。
克鲁普太太是个有眼力的女人,在刚开始的阶段,她便觉察出来了。
“提起劲头来,先生,”克鲁普太太说道,“看到你这样子,我受不了呀,我自己也是个做母亲的呀。”我不知道说什么,就朝克鲁普太太笑笑。“要有希望,先生!”克鲁普太太鼓励道,“别失望,先生!如果她不对你微笑,天下女人还多的是。你可是一个让人喜欢的青年,你一定要明白你自己的价值,先生。”
说完这番话,克鲁普太太行个礼就告辞了。
第23旧友重逢
第二天,我想,该去看看特拉德尔了。他住在开姆顿区兽医学院附近一条小街上,那地方的房客主要是些男学生。我走到楼梯顶时特拉德尔已在楼梯口迎接我了。他见了我很高兴,极诚恳地欢迎我进他的卧室。卧室在房子的前部,虽然没多少家具却也十分整洁。在卧室的角落里,有件东西被一大块白布盖着,我猜不出那是什么。“特拉德尔,”我坐下后又握住他手说,“看到你我真高兴。”“我看到你也很高兴,科波菲尔。”他说,“在伊力巷相遇时,我看到你就开心得不得了,也相信你看到我就开心得不得了,所以我给你的是这个地址,而不是律师公寓的那个地址。”“哦,你有律师公寓吗?”我说道。
“嘿,我有一个房间加一条过道的四分之一,”特拉德尔答道,“有3个人和我合伙租了一套律师公寓。”
他一边这么解释,一边微笑,我觉着那微笑中包含了他旧日的质朴、善良、温顺,以及不幸。
“我通常不把这里的地址告诉别人,”特拉德尔说道,“并不是因为我有丝毫傲气,只是因为那些来见我的人不会愿意上这里来。对我自己而言,我尚在这世界上继续与困难抗争,如果我还装模作样,未免太可笑了。”
“你正在学法律,华特布鲁克先生告诉我的。”我说道。“嘿,是的,”特拉德尔搓着手,慢慢说道,“我正在学法律。”“特拉德尔,我坐在这里看你时,你知道我在想什么吗?”我问他道。“不知道。”他说道。
“你过去常穿的那身天蓝色的衣服。”“啊,当然!”特拉德尔笑着叫了起来,“紧包着腿和胳膊,是吧?”
“那时你是由一个叔叔抚养吗?”我问道。
“当然是的!”特拉德尔说道,“当时我有一个叔父,我离开学校后不久,他就死了。他以前是一个布商,曾立我为他的继承人。可我长大了,他又不喜欢我了。”
“特拉德尔,后来你怎么样了呢?”
特拉德尔说道:“我一直没学会任何技能,一开始我不知如何是好。不过,靠了一个人的帮助,我开始抄写法律文件,但那不够糊口。后来我开始为他们记叙案件,做摘要,以及诸如此类的事,所以我想学法律。我找到不少事干,也侥幸认得一位出版界人士,他给我些活干。而且,我订婚了。”
“她是位牧师的女儿,住在德文,是的!她是一个那么可爱的女孩!比我稍年长一点,却是最可爱的女孩!我相信,从订婚到结婚,我们还要等很长时间,不过我们的格言是:等待和希望!我们总这么说,我们时时这么说。她肯等我,科波菲尔,等到60岁,等到你说得出的任何年岁!”
特拉德尔得意地微微一笑,站了起来。
“不过,我们已向家庭生活迈出了第一步。不错,我们已迈出了第一步。我们应该一步一步地走,同时,”特拉德尔又坐回椅子上,“尽可能好地生活。我收入不多,可我开销也不多。我在楼下的那些人里搭伙,他们实在是些令人极满意的人。米考伯先生和太太都有很丰富的经验,是极好的伙伴。”
“我亲爱的特拉德尔!”我叫道,“你在说什么?”特拉德尔瞪着眼看我,好像想知道我在说什么。“米考伯先生和太太!”我说道,“我和他们很熟!”正好门上响起两记敲门声,在温泽巷的经验使我对这声音很熟悉,只有米考伯先生才那样敲门。特拉德尔打开门,于是,没有一点改变的米考伯先生带着上流人士和青年人的神气进屋来了。
“我请求你原谅,特拉德尔先生,”米考伯先生说道,“我不知道府上还有一位生客呢。”
米考伯先生向我微微鞠躬,拉起了他的硬领。到这时,米考伯先生虽与我四目相对,却一点也没认出我来。不过,看到我微笑,他更仔细地打量我,突然大叫道:“这可能吗?我有再看到科波菲尔的缘份吗?”
于是,他热情地握住我的手。
“唉呀,特拉德尔先生!”米考伯先生说道,“想不到你竟认识我年轻时的朋友,旧时代的伴侣!”特拉德尔正感到惊奇时,米考伯先生从栏杆上向米考伯太太叫道:“特拉德尔先生寓中有一位先生,你见了一定会高兴的,我的爱人!”
米考伯先生又马上转回来,和我握手。“我们的好朋友博士怎么样?”他说道,“坎特伯雷的各位都好吗?”“他们都好。”我说道。
“你将发现,科波菲尔,”米考伯先生说,“我们眼下过着一种可以说是退隐的生活。但你知道,在我的一生中,我已战胜了许多困难,越过了许多障碍。在我一生中某些阶段,我必须退后一步,以备作出飞跃,这事实是你十分熟悉的。眼下我有种种理由相信,不久就将产生一次有力的飞跃。”
我正表示我的欣慰时,米考伯太太进来了。与过去相比,她不那么衣冠整洁了,也许我不太习惯了才觉得如此吧。
“我亲爱的,”米考伯先生把太太领到我跟前说道,“这里有一位名叫科波菲尔的先生,他想和你叙旧呢。”
我们一共谈了半个小时。我问米考伯太太双生子的情况,她说他们“已成了大人”,我又问及米考伯少爷和小姐,她形容他们是“绝对的巨人”,不过当时没有带他们出来见我。
米考伯先生非常希望我能留下来吃晚饭,我推托说有另外的约会,米考伯太太立即如释重负。见此情形,无论他们怎么表示希望我放弃那个约会,无论他们怎样挽留,我都会谢绝的。
可是,我告诉特拉德尔和米考伯先生及太太,在我辞别之前,他们应该定下一个日子去我那里吃饭。由于事务之限,特拉德尔近日内不能去,可是我们终于订出了一个适合大家的日子,于是我便告辞了。